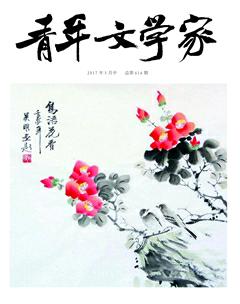“第三種人”的論爭以及《現代》的式微
摘 要:“第三種人”的論爭是左翼文學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論爭,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揚等左翼文學批評家都參與其中,但是這一論爭的主要陣地卻是《現代》雜志,梳理這一論爭的前后發展,會發現關于“第三種人”的論爭不僅改變了《現代》雜志的辦刊宗旨,而且成為了《現代》雜志興衰的轉折點。
關鍵詞:“第三種人”的論爭;《現代》雜志;施蟄存;杜衡
作者簡介:曹曉爽(1993.5-),女,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4-0-02
一、《現代》的初創與論爭的爆發
1932年,“一·二八”抗戰爆發,戴望舒、杜衡結束了水沫書店之后,彼此回到老家,兩個月內沒有聯系。這年3月,上海現代書局經理張靜廬致信施蟄存,希望其主辦一個刊物。次日,施蟄存趕到上海,與現代書局總經理洪雪帆、編輯部主任葉靈鳳商討創辦雜志的事宜。施蟄存因為“不是左翼作家,和國民黨也沒有關系,而且我有過辦文藝刊物的經驗”,最終成為刊物的編輯,一人單干,刊物定名《現代》。1932年5月1日,《現代》創刊,成為了因戰爭而百業凋敝的上海的唯一文藝刊物。施蟄存在創刊號上發表了《創刊宣言》,表達了《現代》“不黨、不群、不偏”的編輯宗旨。《現代》出版后,成為了“一·二八”后上海最先問世的大型刊物,初版三千冊五天脫銷,后加印三千冊。《現代》的銷量如此繁盛除了它出現的時機恰巧沒有與之相競爭的期刊雜志外,也與其“不黨、不群、不偏”的編輯宗旨有關。《現代》中出現的作家既有魯迅、茅盾、郭沫若、馮雪峰、錢杏邨、周揚、夏衍等革命作家;也有巴金、老舍、葉圣陶、郁達夫、李建吾、王統照、王魯彥等進步作家;此外,還有周作人、沈從文、胡秋原、李長之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以看出,施蟄存一直是堅持著自己的“中間路線”創辦原則的,因此當“第三種人”的論爭發生時,施蟄存始終保持緘默。
“第三種人”的論爭最初起源于1931年12月 25日,胡秋原在《文化評論》旬刊的發刊詞《真理之檄》中說道:“我們是自由的智識階級,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說明一切批評一切。我們沒有一定的黨見,如果有,那便是愛護真理的信心。”同期《文學評論》中他還發表了《阿狗的文藝論》:“藝術雖然不是‘至上,然而絕不是‘至下的東西。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按照胡秋原的回憶,他在這一時期,是“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不隸屬于任何黨派、堅持自由主義文化立場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隨后,譚四海發表《“自由智識階級”的“文化”理論》和《文藝新聞》社發表的《請脫棄“五四”的衣衫》抨擊“自由智識階級”是為虎作倀,1932年4月20日,胡秋原發表《是誰為虎作倀!》、《文化運動問題》、《勿侵略文藝》在《文化評論》第4期上,“不主張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1]。5月,瞿秋白在《文藝新聞》第56期上,發表《“自由人”的文化運動》,批評胡秋原是“‘五四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遺毒”[2]。
胡秋原隨后在《讀書雜志》第2卷第1期上發表了《錢杏邨文藝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批評了錢杏邨的“主觀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小兒病空談”。不久,馮雪峰化名“洛揚”在《文藝新聞》第58期上發表《“阿狗文藝”論者的丑臉譜》,批評胡秋原為了反普羅革命文學而攻擊錢杏邨。
在1932年7月1日,蘇汶在《現代》第1卷第3期上發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回應胡秋原在《讀書雜志》二卷一期上發表的《錢杏邨理論之清算》, 以及同時在《文藝新聞》第五十六號上發表了沒有署名的《自由人的文化運動》, 蘇汶第一次提出了“第三種人”的說法,自稱是“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人”之外的“第三種人”,也就是所謂的“作者之群”,在之后的的文章中蘇汶進一步解釋了“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容我給加上一個解釋吧,實在是指那種欲依了指導理論家們所規定的方針去做而不能的作者。”[3]隨后以《現代》雜志為主要陣地,展開了一場關于“第三種人”的論爭。
二、論爭的發展
1932年10月1日《現代》第1卷第6期上,發表了五篇文藝論辯的文章:蘇汶的《“第三種人”的出現》、瞿秋白化名“易嘉”的《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周揚化名“周起應”《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舒月的《從“第三種人”說到左聯》、蘇汶《答舒月先生》。
瞿秋白認為蘇汶和胡秋原都是持著“文藝自由論”,這是一種文學脫離無產階級,脫離廣大群眾的觀點,而蘇汶的超階級文藝觀更是受到了抨擊;周揚的文章運用了理論與實踐、文學與革命、文學宣傳作用與藝術價值的關系來回應蘇汶。蘇汶的《“第三種人”的出路》主要是答復瞿秋白的,并且做了總結式的陳述:“‘第三種人的唯一出路并不是為著美而出賣自己,而是,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不如努力去創造一些屬于將來的東西吧。”
1932年11月1日《現代》第2卷第1期上,同時發表了魯迅《論“第三種人”》和蘇汶《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的文章,兩篇文章針鋒相對。魯迅這篇文章主要闡述了兩個基本點:一是左翼作家需要同路人,二是“第三種人”根本做不成。蘇汶在《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中反對政治對文學的干涉,文學不能做某些人的喉舌,不然就會失去“做時代的監督的那種效能”。
之后,1932年11月,這場論爭發生了一個轉折,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以“歌特”的筆名在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第30期上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張聞天提出“使左翼文藝運動始終停留在狹窄的秘密范圍內的最大的障礙物時‘左的關門主義”,一是否認“第三種人”及其文學的存在,另一是“文藝只是某一階級‘煽動的工具、‘政治留聲機的理論。”對于“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不應排斥, 應該給他們以“自由”,從而實現“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4]張聞天的這篇文章其實給了“第三種人”一種較為中肯的評價,也適時地扭轉了這場爭論的重點。
胡秋原在《現代》第2卷第2期上發表了《浪費的論爭》,回應了之前瞿秋白、馮雪峰、周揚、舒月對其做的批評,胡秋原認為問題不是此時可以解決,遂不必做無益的論爭。在《現代》第2卷第3期上署名“洛揚”的《并非浪費的論爭》回應胡秋原的《浪費的論爭》,這篇文章是在張聞天的影響下,由馮雪峰、瞿秋白商定,最終由瞿秋白寫定的。而馮雪峰則化名“丹仁”單獨寫了《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理論》及《“第三種人”的問題》,這三篇文章對“第三種人”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而馮雪峰的《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理論》更是可以看成是一篇左翼批評家對這一場論爭的總結:“要反對那種以為現在沒有第三種人,‘第三種人就是反革命的見解。”
1933年4月,蘇汶帶有總結性質的《一九三二年的文藝論辯之清算》發表在《現代》第2卷第3期,蘇汶也代表“第三種人”對這一論爭進行了總結:“第一,文藝創作自由的原則是一般地被承認了”,“第二,左翼方面的狹窄的排斥異己的觀念是被糾正了”,“第三,武器文學的理論是被修正到更正確的方面了”。之后,蘇汶將此次論爭的文章編訂為《文藝自由論辯集》,現代書局1933年3月出版。論爭發展到此時,施蟄存始終保持沉默并已顯露不悅之情,希望可以趕緊撤換話題,所以用蘇汶的文章做一個結尾[5]。
三、《現代》的式微
《現代》第3卷第1期起,由施蟄存、杜衡共同編輯。杜衡加入編輯顯然預示著《現代》將要與“第三種人”產生瓜葛,由于此,許多作家已不熱心支持《現代》了。之后,由于施蟄存和魯迅之間有了《莊子》與《文選》的爭論,穆時英被國民黨收買去當圖書雜志審查委員,現代書局的資方內訌,最終施蟄存首先放棄編務,《現代》從而變為杜衡獨自主持。
而由于杜衡的加入,整個刊物的編輯宗旨也發生了改變,在《現代》第5卷第1期《社中座談》中的《本刊組織編委會之計劃》中提出:犧牲趣味而使雜志“更深刻化,更專門化”,這樣的改變顯然是與施蟄存的“輕文學”觀背道而馳的,所以施蟄存在放棄《現代》編務后,轉向編輯更加“輕巧”的《文藝風景》。以杜衡“第三種人”加入編輯為標志,《現代》在表面和事實上已經偏離了最初的創辦宗旨。
此時,《小說月報》解體后的文學研究會同人重整旗鼓出版的《文學》也對《現代》形成了沖擊,《文學》出版后經歷了同《現代》一般的搶購一空。而《文學》的主編魯迅與施蟄存因為《莊子》《文選》的事情交惡,后又因圖書審查事件誤會加深,因此,魯迅發表在《文學》上的文章漸漸減少,1933年11月,魯迅在《現代》上發表《海納與革命》后,停止為《現代》供稿,并奉勸《現代》“此后似亦不登我的文字為宜”[6]。此后,魯迅發表在《文學》上的作品亦有不少是針對《現代》的。
施蟄存曾分析道:“杜衡參加《現代》的編輯工作,恰恰表示《現代》已成為所謂‘第三種人的派性刊物……杜衡的參加編務,使有些作家不愿再為《現代》撰稿……從第四卷起,《現代》的銷路逐漸下降。”[7]第三種人的論爭以及杜衡加入《現代》的編輯使得《現代》被擱置在了左翼文學的對立面,正如施蟄存所說:“像《現代》這樣一個沒有政治傾向性的,不屬于左翼文學的刊物,也還是要在掙扎中求生存,而最后還是維持不下去”。[8]
注釋:
[1]胡秋原:《勿侵略文藝》,1932年4月20日,《文化評論》第4期。
[2]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運動》,1932年5月23日,《文藝新聞》第56號。
[3]蘇汶:《“第三種人”的出路——論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復易嘉先生》,載《現代》第1卷第6期, 1932年10月。
[4]歌特:《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斗爭》,1932年11月。
[5]“蘇汶先生送來《一九三二年的文藝論辯之清算》一文,讀后甚為快意。以一個雜志編者的立場來說,我覺得這個文藝自由論戰已到了可以相當的做個結束的時候。蘇汶先生的此文恰好使我能借此作一結束的宣告,遂為匯合洛揚,丹仁兩先生的文章一并發排。在以后的幾期《現代》中我希望能換些別的文藝問題來討論了。” 施蟄存:《重印全份<現代>引言》,《北山散文集》(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 2001年10月,第1614頁。
[6]孔另境:《現代作家書簡》,花城出版社,1982年2月,第176頁。
[7]施蟄存:《我和現代書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325頁。
[8]施蟄存:《重印全份<現代>引言》,《北山散文集》(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2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