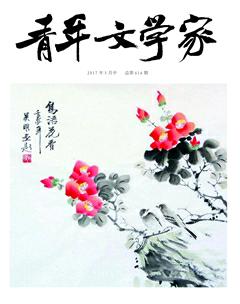從《正紅旗下》初探老舍民族觀
摘 要:“所謂民族觀,即對于民族和民族關系的整體認知。”[1]老舍作為少數民族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未完)中,直接或間接地透露著屬于他本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觀念。本文以《正紅旗下》為例,從當中的人物交往和傳統習俗著手,探索老舍民族觀的具體表現。
關鍵詞:正紅旗下;老舍;民族觀
作者簡介:李駿(1993-),女,中南民族大學碩士,研究方向:現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4-0-02
《正紅旗下》主要通過對“我”的降生以及“我”“洗三”宴時,族內各親友、不同民族的街坊鄰居前來道賀的場景進行描寫,繪就出一幅多民族和諧共處的美好畫卷。身為旗人的“我”們一家,突破了清朝政府對于不同民族分而治之的規定,毫無偏見地去跟漢族、回族等民族的民眾相濡以沫地交往和生活。因為在此時的滿族下層群眾心里,“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誰也擋不住人民互相友好”[2]。
雖然過去清廷曾嚴格規定旗人除了為皇家做事供職外,不得從事農商等活動。但到清末,民族隔閡在漸漸縮小,各民族的交往已呈不可抵擋之勢,這在老舍的小說《正紅旗下》中的人物交往和傳統習俗兩方面得以生動體現。
一、各族民眾的百態
在人物刻畫上,老舍顯示出其老道的寫作功力,一幅“各族民眾百態圖”躍然紙上,出場的大小角色都有著獨特的個性特征。其中頗具代表性的男性角色有:漢族商戶——便宜坊的王老掌柜;滿族青年——“我”的二哥福海。說到頗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便不得不提這兩位滿族婦女——“我”的姑姑和“我”大姐的婆婆。
(一)漢族商戶王老掌柜
王老掌柜是老舍回憶往事時不得不提的一個人,他是在京住了60年的膠東人。在王老掌柜起初對旗人的衣食住行以及說話的方式感到不習慣且有些反感。之后卻也漸漸入鄉隨俗,由惡到喜,比如養鳥、作揖請安和賒賬這些事。出乎意外的是,在“我”洗三那天,王老掌柜居然提著一對豬蹄子也來了。老舍也因此感言:“我一輩子忘不了那件事。并不是因為他是掌柜的,也不因為他送來一對豬蹄子。因為呀,他是漢人。”[3]在不斷的交往中,滿漢人民之間已悄然成為了朋友。例如王老掌柜就覺得:“清朝皇上對漢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兒既誰也離不開誰,便無妨做朋友。”[4]在后來受到倚仗牛牧師而跋扈賒賬的多大爺為難時,王老掌柜向身為滿族的二哥福海求助。福海也忙前忙后盡心盡力地想幫上他的忙。老舍如此敘述,體現出他所推崇的各民族互幫互助的和諧關系。
(二)滿族青年二哥福海
小說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來敘述“我”大舅的兒子——福海的故事,顯示出老舍對此人物頗為欣賞。福海無論是在禮儀舉止上還是為人處事上,都深受周圍人的愛戴。他不僅在朝廷任職,也是個“油漆匠”。從制度上來說,福海學油漆手藝是不符合佐領制度的,制度規定旗人不得擅自離京離旗,就連學手藝也會被旁人輕視。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之下,不從事一項副業,是很難過日子的。從小說中,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底層旗人們的生活雖然有著清廷每月的幾兩補助,可是已經不能滿足旗人的日常開銷,同時束縛著旗人的自由。
福海是一個“熟透了的旗人”,他“既沒有忘記二百多年來的騎馬射箭的鍛煉,又吸收了漢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5]他熱心幫助各族朋友,為搭救王掌柜的兒子王十成忙前忙后盡心盡力,最終兩人義結兄弟。面對旗人身份和兄弟義氣之間的矛盾心理,他最終選擇站在十成這一方。他對十成說:“我是旗兵不能自主!不過萬一有那么一天,兩軍陣前,你我走對了面,我決不會開槍打你!”[6]雖然面上因為旗兵這一身份不能明著支持義和團打洋鬼子,但在內心中他是十分佩服王十成的。雖未能信守對王老掌柜的許諾讓十成留京,卻也和上文提到的那樣,為幫王老掌柜解決多老大那件麻煩事而特意上門求助云亭、正翁和定大爺。
最后,就連定大爺這些上等旗人,也在暗中幫助王掌柜等漢族民眾排憂解難。老舍把身份地位不同、風俗習慣各異的各民族同胞放置在同一場景下生存,且相處還算融洽,間接也體現出作者內心對各民族和諧共處的認同和期待。
(三)回族商戶金四把
辦“滿月”酒時,金四把在定大爺走了許久后到來。老舍對于金四把的到來感到有些自豪,同時也覺得金四把的到來比定大爺更有意義。他特意在第六節篇末強調:“我至今還覺得怪得意的,是受到過回族朋友的慶祝的。”[7]在當時的環境中,回族受到滿族統治者的壓迫頗深,因此金四把叔叔的到來更是難能可貴。小說描繪到,金四把除了有時用幾個回民的特有名詞之外,說話和我們沒有隔閡。甚至連我們的特有名詞(如牛錄、甲喇、格格)他也能靈活準確地運用。除了嚴守教規不肯喝我們的茶用我們的杯子之外,其他并無大差異。我的母親并未因為金四把不喝我們的茶而覺得沒面子,反而十分尊重他的教規,提議“把有把兒的茶杯”為金四把專設專用。在《正紅旗下》中,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只要相互理解尊重,同樣可以相處很融洽,正如老舍在文中所說:“當彼此不相往來的時候,不同的規矩與習慣使彼此互相歧視。及至彼此成為朋友,嚴守教規反倒受到對方的稱贊。”[8]
(四)唯我獨尊的“我”的姑姑
“我”的姑姑比大姐的婆婆多一些風趣,但也總是擺出“大姑子”的身份使喚為母親。姑姑常常心安理得地使喚母親干各種雜事。姑母因為“滿人都尊敬姑奶奶” 而幫助在婆家經濟拮據的小姑奶奶,即“我”大姐,以壯自己的聲勢。“我”母親寧可自己吃苦吃虧也盡量把姑姑伺候舒服。因為姑母鬧起脾氣來“變化萬端”,“神鬼難測”。“我”得這位唯我獨尊的“姑姑”宛若家中的“老佛爺”,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行使著滿族觀念中“大姑子”的特權,可成為性格豪爽、直率的滿族婦女的一方面的縮影,同時也反襯出“我”母親的明事理、勤勞溫婉的優良品性。
(五)欺壓成性的“我”大姐的婆婆
老舍對于他大姐的婆婆是沒什么好感的,從多方面反映著如今已從高處跌入低谷的旗人,雖然生活已大不如前,仍擺著空架子靠賒賬維持看似光鮮的生活。在大姐婆婆的觀念里,不賒賬便枉為旗人。大姐的婆婆總是把大姐當女仆來使喚,趾高氣昂地吩咐、命令、下指示。這讓“我”的大姐生存壓力頗大,梳好的兩把頭好幾天不敢拆,天還沒亮就得起來包辦家里的全部家務,一旦起早了,便回到炕上穿著衣服打盹,不敢再躺下。在大姐婆家,大姐宛若免費勞動力,不僅沒有全家均享的“賒賬”的權利,還承擔著最終的家務重擔。
二、“講究”的旗人生活習俗
眾所周知,因入關之后身份尊貴,滿族人對于生活的藝術還是頗有講究的。老舍在《正紅旗下》中諷刺了這一“講究”的格調:“兩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埃,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么沉浮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里。”[9]在小說中,講究的兩位代表人物便是“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我”的大姐夫多甫甚至自豪地告訴“我”說:“咱們旗人,別的不行,要講吃喝玩樂,你記住吧,天下第一!”[10]足以見得,滿人對其生活趣味性是十分滿意的。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大姐的公公和丈夫父子倆認為把玩得細致、考究、入迷當作他們每天生活的意義。大姐的公公雖是個武官,卻“隨時都沉醉在小刺激和小趣味里”。他們以養鳥、養蟈蟈、養蛐蛐、聽曲兒、唱戲為樂。戲曲成為滿族人的生活必需品,他們不僅愛聽還喜歡自己粉墨登場。同時他們也創作大量的岔曲、快書、鼓詞等。大姐的丈夫,在玩膩了鷂子和胡伯喇之后,改養鴿子,體驗著“滿天飛元寶”的樂趣。
在“我”出生那日,兩父子在院子里縱情地放花炮玩,根本沒空搭理急忙跑來請救兵的“我”二姐,仿佛生孩子只是女人們的事情。身為女性的旗人等于包干了一切家庭瑣事。他們深受中國傳統祭祀禮儀影響,主張“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他們的長幼有序、婆媳尊卑觀念也異常明顯。同時,婦女們極講規矩。在家中練熟這種生活藝術后,在親友們小孩洗三、滿月、做壽、婚喪大典等場合得以實踐。“我”母親不能為了減少家中開支,就不去給親戚拜壽、吊喪或賀喜。不然就等于疏離親友,有失顏面。這些大大小小的規矩,給窮苦人家徒添很大的生活壓力,寧可縮衣減食也不敢壞了老祖宗留下來的規矩,不然就得受到周遭的譏諷和白眼。
老舍的民族意識和家國情懷在《正紅旗下》的細節描寫中比比皆是。他通過抒寫自身的生活經歷,為讀者展現一個民族友好和諧共處的意境。無論是筆下的人物還是文中的語言,都烙上了屬于老舍的滿族文化的影子。這也激勵著我們進行更加深刻地分析和研讀,以收獲對其民族觀更為全面的認識。
注釋:
[1]關記新:《老舍民族觀探賾》[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4期.
[2]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23頁.
[3]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23頁.
[4]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22頁.
[5]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02頁.
[6]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49頁.
[7]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41頁.
[8]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40頁.
[9]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91頁.
[10]老舍:《我這一輩子·正紅旗下高榮生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