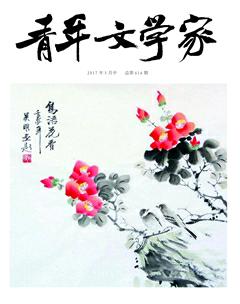《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紀、戴二人交游考
摘 要:紀、戴二人皆為清代之通儒,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稱紀氏大到經史子集、小到詞曲卜筮皆是通才,實力遠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贊紀氏為通儒;而戴氏在算術、考證等等方面亦有大成,王昶稱“余友休寧戴君”是“通天地人之儒也”。尤其是在紀氏在與名流雅士馳逐競游的時日里,二人的交游往來常常引發學術互動、軼事互寄等等。但二人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相關的記載文字卻少獲關注。在這些交游中,常常能看到二人學術觀或生活思想、倫理思想上的蛛絲馬跡。
二人之間的互動更能照見出彼此的觀點,而與之相比,一味地自我抒懷反倒是含蓄不明的。紀昀的學術、生活、倫理思想集中體現于《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而作為紀曉嵐人生軌跡中的知己好友,戴氏在這本書出現了多次,本文試作淺陋的梳理與總結。
關鍵詞:戴震;紀昀;交游;門戶
作者簡介:李翰廷(1993-),男,天津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4-0-02
一、戴、紀二人之論學術
戴、紀二人初識是在乾隆乙亥年夏天,按照紀氏的說法是“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紀氏還曾大贊戴氏深通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1]戴震確是在乾隆乙亥年進入北京的,后來得以與紀氏交游也可以說是塞翁失馬之功。在《戴震全書·第六冊》中由段玉裁撰、楊應芹訂補的《東原年譜訂補》中,找到這樣一段文字“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可以看到戴震是由于避難避禍才來到北京,且在之后有文字說明了該事件的來龍去脈。并在拜會了錢大昕之后,戴氏逐步結識王昶,而后紀氏等人逐步認識了戴氏其人。以下是在《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紀氏記載與戴氏相結交、交流的事例,因載于紀氏此書中,有的甚至是對話,可信程度最為確切。
在《灤陽消夏錄五》中曾記載了紀曉嵐與戴震的一段對話。紀曉嵐在這里保持著他欲引一論而極盡鋪墊的風格,以一句“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的出處問題開講,這一句詩使得朱青雷、高西園二人陷入苦思而不知出于何處。然而,柳樹之后有人說話稱此句出于劉希夷。二人尋聲找去竟發現只有一棵老柳樹,朱青雷不勝驚悚認為是白日見鬼,而高西園卻說應常見一見這樣的靈通之鬼。
緊接著才深入引出了類似的事例,紀氏將此事論與戴氏。戴氏則對紀氏說起了兩位書生討論春秋歷法出于何時的故事,同樣窗外有聲傳來:“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詞費也。”戴氏在這里引出了自己的觀點,不應一味的“曰若稽古”,在冥冥的客觀事實之中,眾多迂腐陳舊的儒生就是這樣被真相嘲笑的。
紀氏將這段放在了《灤陽消夏錄五》中,正說明了紀氏對戴氏這段話的高度認可。這段話也正好體現了紀曉嵐不拘泥于漢宋之爭,而出其“公理”的遠矚。
在錢穆先生的《錢賓四先生全集》中說:
“蓋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
然而,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戴氏也是尊古而不泥古的,在漢宋之爭中,紀昀始終保持著對二者的高度理性認識,呼吁著消除門戶之爭、兼采漢宋精華。在《總目·經部總敘》中,紀昀言:“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2]正是紀氏對漢宋之爭的高見。而戴氏也承認不能迂腐,在客觀事實面前依舊稽古,是非常可笑的。所謂二人皆通儒,所言非虛。“通”非僅在于廣博,也在于洞悉明理。
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第六卷中記載了紀氏回憶戴氏,關于學術的另一段話:
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3]
這本書即是戴氏的《考工記圖》,紀氏為之作序。紀氏與戴氏的交游痕跡也見于《閱微草堂筆記》之外,尚多見于《紀文達公遺集》《紀文達公全集》的詩文之中。
二、戴、紀二人之論鬼神與軼事
紀氏“尤深于易”,關鍵在于他明確地表達了“明人事”這一根本意義和目標。我們可以看到,其見識之深無論時代前后,紀氏的思想都是難能可貴的。同樣,他也不是簡單地以鬼寫鬼、以狐寫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他更是借“鬼神”以說人理,以“靈通”而達人情。
此種例子甚多,在這里僅就紀氏與戴氏相關的部分為例。
首先,紀昀記載了戴氏給他講的一個“歸隱之鬼”:
戴東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縣深山中,日薄暮,風雨欲來,見崖下有洞,投之暫避,聞洞內人語曰:此中有鬼,君勿入。問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請一見,曰:與君相見,則陰陽氣戰,君必寒熱小不安,不如君癎火自衛,遙作隔座談也。宋問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時為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取相軋,乃棄職歸田,歿而祈于閻羅,勿輪回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注陰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墓居群鬼之間,往來囂雜,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于此。雖凄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穽,則如生忉利天矣。寂歷空山,都忘甲子,與鬼相隔者,不知幾年,與人相隔者,更不知幾年。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跡,明朝當即移居。武陵漁人,勿再訪桃花源也。語訖,不復酬對,問其姓名,亦不答。宋攜有筆硯,因濡墨大書鬼隱兩字于洞口而歸。[4]
戴氏與紀氏的這段交流,頗有身處嘈市而心念野廬的“大隱”情懷。此鬼為人時不愿趨俗競利,死后發現鬼界互相傾軋亦復如是。他自己只得再次避居于山洞,可仍舊無法逃脫煩擾。最后,他將自己的洞看作是“不知秦漢魏晉”的桃花源,將宋姓書生看作是偶入武陵源的漁夫,希望真正得到寧靜。
這段戴氏給紀氏講的故事里,宋姓書生此事是否是戴氏的風聞,亦或是戴氏借鬼神抒懷而編出來的故事,其真切與否已不可考。但是,此故事依舊見于《閱微草堂筆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二人在精神上的高度契合。
還有,戴氏與紀氏、方可村聊天時,提到的關于倫常的論斷:
戴東原亦在座……未免縱欲忘患耳。東原喟然曰:縱欲忘患,獨此鬼也哉。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戴氏在與紀氏談天說地時的真實記載,而且是難得的一段你來我往的對話,我們看到的是朝野之外、門戶之外、拘泥之外的文人之間交往的真性情。
還有一則戴氏給紀氏所講的“狐貍驅鬼自傷”的故事,狐貍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是很重要的故事角色,經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主人公角色。尤以狐貍竊居或居住人室為多,像戴氏講的這則故事即是。這則故事里的狐貍原為善意,與主人相安如同鄰居,見屋中之鬼傷害主人和孩子,希望主人將其驅除。但是當主人燒符驅鬼引來天神天兵時,卻連它自己一同被趕走。后面是對這個故事的評論,“蓋不忍其憤,急于一逞,未有不兩敗俱傷者。觀于此狐,可為炯鑒。”還有,戴震為紀昀所講的畏鬼的故事,說戴震的“其族祖某”在偏僻小巷中居于廢棄的空院,夜晚遇鬼,而他毫不畏懼。戴震故事中的鬼也極盡幽默之能,多次引誘他說“怕”字。因他終不肯說“怕”字,鬼遂憤曰:“吾住此三十余年,從未見強項似汝者,如此蠢物,豈可與同居。”事后,有的人說他怕也是常情,而他卻說一旦松口就會失去“盛氣”,而有深知自己“道力”不深,所以不能為鬼所引誘。
這些故事揭示的是紀氏、戴氏之間的真切交流,是脫離于門戶、脫離于身份的真性情、真思想,是二人在談天說地時的暢快與舒朗。
三、結語
紀氏先寫“宦海浮沉頭欲白”,昔日與故友的笑語今日竟成真實,又接著說沒有人能夠像此公(東原)“癡”,讀及此處可以明顯的感到紀氏之可憐、可惜之感。戴震英才天縱卻科舉不順,因禍入京結交名士卻已是中年。“六經訓詁倩誰明,偶展遺書百感生。”紀氏在第二首開頭便問道六經訓詁誰人可向戴氏一樣通達洞悉,偶爾打開了戴氏的遺著不得不百感交集、涌入心頭。這句也道出了戴震在學術史上通“六經”、識“訓詁”方面的貢獻。最后,紀氏寫道,“揮塵清談王輔嗣,似聞頗薄鄭康成。”這兩句化用古人,將戴氏比作王弼,比作鄭玄。紀氏行文考究,為詩更見功力,化用的兩位古人一位是玄學、一位是漢學,而玄學又開宋學發端,可見紀昀對戴震在學術上的高度評價。
注釋:
[1]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版,第94頁。
[2]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版,第1頁。
[3]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版,第93頁。
[4]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六》,中華書局,2014年2月版,第3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