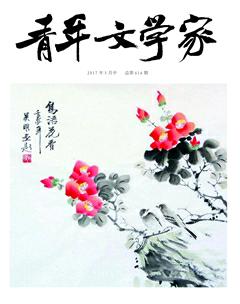《梧桐雨》《長生殿》結構助詞對比分析
摘 要:助詞作為漢語虛詞中的重要部分,用于表達動作的狀態情貌、顯示語氣、構成各種結構,是漢語表情達意的重要手段。“近代漢語助詞系統的出現和形成,也是近代漢語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1]因而值得我們的進一步刻畫和把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漢語助詞系統有不同的特點,本文力圖對元雜劇《梧桐雨》和清代戲劇《長生殿》文中出現的結構助詞做窮盡性的調查和描寫,將結果放入漢語史中進行考察分析。希望對元到清漢語結構助詞的特點與發展規律有所把握。
關鍵詞:梧桐雨;長生殿;結構助詞;漢語史
作者簡介:馬坤(1996-),女,漢族,河北張家口人,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漢語言(應用語言學方向)。
[中圖分類號]:H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4-0-02
第一個提出“助詞”的人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稱助詞為“助字”,并定義助詞為:“凡虛字用以結煞實字與句讀者,曰助字。”[2]筆者參考了《古代漢語綱要》中關于“助詞”的相關研究理論:助詞“是一種作為造成詞句的輔助材料的詞類,它是一種特殊的虛詞。”[3]筆者支持書中所說的“助詞”較之表語氣語音的語助詞更廣泛,詞素中的虛素和結構中的虛素也算作助詞。本文判別“結構助詞”所依據的定義與判定方法取自《古漢語知識辭典》對于結構助詞的解釋,即“用于句子中間表示結構關系的助詞。如‘之、‘是等。”[4]
本文語料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8年第一版)的徐朔方校注的《長生殿》和選自《元人雜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為底本。方法上,筆者首先利用antconc3.2.4w軟件對兩份語料分別進行助詞搜索、詞頻統計篩選出可能的句子,進而運用課上所學漢語史語法知識確認該詞的結構助詞用法,之后逐個對實例進行刻畫分析。最后將兩份語料的統計結果進行對比分析,并放入漢語史中進行考察。江藍生先生在給《東漢一隋常用詞演變研究》作的序中曾指出“漢語史研究有兩項基礎性的工作必須做。一是有計劃、有選擇地開展各代的專書研究,全面考察、描寫其中的語言現象。”[5]在以上學界研究理論的指導下,本文將聚焦《梧桐雨》、《長生殿》兩文的結構助詞進行對比,對于元代至清代的結構助詞發展脈絡進行斷代研究。
一、數量上看分化、合并與替代。
經計算機查找后筆者發現《梧桐雨》、《長生殿》中主要的結構助詞涉及到:的、地、之、得、個、價6個。在經過筆者人工篩排后,將名詞“地(di)”、動詞“得”名詞“價(jia)”、量詞“個”、句末語氣詞“的”排除。進而得到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兩部作品中所使用的主要結構助詞相同,詞語選擇變化不明顯,但使用的頻次有差別。通過觀察對比,這兩部作品中結構助詞使用最普遍的都是結構助詞“的”,可見在助詞系統整體調整的過程中“的”得到廣泛應用并逐漸取代了用法相似的“之”“地”,使得“之”比重明顯下降,“地”用法范圍逐漸被圈定。
此外,隨著“地”用法的逐漸減弱, 與其語法功能類似的“個”和“價”也開始走向衰落。但來自于“謂語+數詞+量詞+賓語/補語”的“個”進一步虛化,作助詞僅一種形式(“謂語+個+賓語/補語”)用例不斷增加,其余消失。正是“個”功能的擴展、虛化用法使得它免于消亡,反而使用增加。“價”幾乎不常見,表現出被完全替代的趨勢。
相比較古漢語結構助詞:“底”幾近消失,“之”仍保留且發揮作用,但由于其功能上的局限性,已經遠比不上“的”、“得”等新興助詞的發展。伴隨動詞“得”進一步虛化,引導狀態補語和可能補語功能固定,結構逐漸復雜趨向成熟,使用頻率上升明顯甚至和“之”相近。
筆者還注意到《長生殿》中出現的“之后”、“記得”、“驀地”、“特地”等一系列常見搭配有凝固的跡象,這些搭配和“之”字的衰落共同表現出漢語發展雙音化的特征。
總體而言,新興的助詞產生的速度和數量跟不上舊有助詞的消亡,造成助詞的總量從近代發展到現代越來越少的趨勢。數量的變化必將引起結構助詞功能的重新分配和擴大。那些古漢語里存在而近代漢語中不用的結構助詞必將由于它們的消亡發生功能的轉卸,它們所擔負的語法功能會由其他助詞來承擔。可見漢語助詞從產生之初發展到現代漢語的格局,經歷了整個助詞系統的自我調整。
二、助詞功能分化明確:由混用借用到分工固定
通過對兩文各結構助詞的功能分析,筆者認為從元到清初結構助詞已經表現出功能上的分化趨勢,甚至用例趨于固定。當然,《長生殿》仍是近代漢語助詞系統,因而結構助詞功能仍有部分交叉臨時混用現象,結構助詞系統也仍在向現代過渡。兩文中涉及的結構助詞主要功能如下:
(一)作為定語狀語標志和名詞短語標志,“的”使用情況逐漸復雜。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代詞、動賓短語、主謂短語后加“的”的短語結構在句中作主語、賓語、定語、狀語。《長生殿》中“的”可將形容詞、動詞、代詞等轉換成名詞短語這一助詞功能的凸顯,也意味著近代漢語“的”的用法趨近成熟。例:
哎呀,踏壞人了,老的啊,你在那里?《長生殿》
(二)“地”在“的”產生后部分用法被“的”替代,如
低低的叫聲玉環,太真妃笑時花近眼。
卻不道口是心苗,不住的頻頻叫。《梧桐雨》
但“地”沒有像“底”一樣消亡,而是保留了不少的用例,成為對立于“的”的又一結構助詞,其語法功能大多是與前面的詞語構成“地”字結構修飾謂詞性成分充當狀語,此用法更接近于現代漢語。
(三)在元到清這一階段中,結構助詞“得”有了迅猛發展。除了用例的顯著增加外還體現在:
1、在動詞后引導補語結構,既可以引導狀態補語也可以引導可能補語。
2、其動詞義進一步虛化,引導狀態補語時表達方式更為多樣。位置固定在動詞后,搭配功能上既能與詞(動詞、形容詞、名詞、副詞)也能與詞組(主謂、述賓、偏正),還能加更復雜結構(賓+補、比況短語、把字句)。
3、表示否定時還出現了一系列靈活的結構。
(四)結構助詞“之”用法過于單一,“定+之+中心語”最為常見,中心語必須出現還絕大多數為單音節。“之”陳舊的結構形式已經不能滿足漢語詞匯語法發展的要求。
謝主帥不殺之恩。 《梧桐雨》
分日月之光華,掌風雷之號令。 《長生殿》
(五)“個”的用法為“X+個+中心語”前面可加形容詞、代詞、動詞、時間名詞,在句中作主語、賓語、定語和狀語。這一用法明顯和“的”有重疊,因而可能被逐漸替代。《梧桐雨》部分例子中的“個”已明顯不再具備量詞“個”的實在意義,“個”已不再是對被修飾語進行數量限定。相反,它的出現賦予原有結構一些原不具有的語法意義,使原來的結構具有了“輕巧隨便”的非理性意義。因此在謂語和賓語/補語之間虛化的“個”在此后繼續保留,如:
我恰待行,打個囈掙。《梧桐雨》
請暫返香車,圖個睡飽。《長生殿》
(六)“價”作為用例最少的近代漢語結構助詞在元到清走向衰落。它既跟在副詞和時間名詞后,還跟在名量結構、動量結構、指代結構、動賓結構和連動結構的后作狀語。可見“價”的用法部分與“地”重合。隨著漢語語法的發展,“價”作為結構助詞的用法終將被“地”替代而逐漸消失。
一會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梧桐雨》
可見,從《梧桐雨》到《長生殿》,“個”、“地”、“得”混用為“的”用例減少,各個結構助詞用法分工比較明確。清代結構助詞系統在某些范圍內有了一個接近現代漢語的基本輪廓。
三、部分結構助詞詞義繼續虛化
《梧桐雨》中結構助詞不成熟、不固定、部分助詞詞性難以明確主要原因是存在詞義虛化不徹底。其中,“得”和“個”在元到清的詞義虛化過程也是他們結構助詞功能增長和轉變的重要原因。筆者簡要舉例分析:
丞相,不可殺此人,留他做個白衣將領。
我這一去,到的漁陽,練兵秣馬,別作個道理。《梧桐雨》
西宮因個甚,惱君懷?
生克擦直逼的個官家下殿走天南。《長生殿》
起初由于“一”作為數量義的原生性,一般都可以省略而不影響交際,“個”在表量的同時,逐漸衍生出表不定指的輔助功能。《梧桐雨》中“個”所修飾的都是一些名詞性詞組,《長生殿》就連謂詞性短語甚至小句也可以受“個”修飾,這種從具體到抽象,從體詞到謂詞的轉變是“個”虛化為助詞的表現。
恨不得手掌里奇擎著解語花,盡今生翠鸞同跨。
在上例中,“得”的“致使、得到”義逐漸弱化,“得”處于兩個謂詞性結構之間,前的動詞與后面的謂詞性成分之間的因果語義關系并沒有因“得”語法性質的轉變而發生變化。因而“得”的虛化自然而無明顯標志。上面最后一例《長生殿》中“動+得+主謂”的格式中,“得”字明顯失去了動詞的性質和功能(非連動),成為連接動詞和補語的成分,從而虛化成結構助詞。
綜上,元末到清初是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發展的重要時期,是近代漢語結構助詞系統向現代漢語結構助詞系統過渡的關鍵階段。《梧桐雨》和《長生殿》中結構助詞的特征都反映了元到清的近代漢語結構助詞發展總趨勢。它們繼承了古代漢語“之”和唐宋以來的新興的結構助詞,并且朝現代漢語的方向發展,表現為有些助詞分工不明確,功能重疊,有些助詞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用法。助詞之間功能的重疊以及助詞自身的興替也正反映出元末至清初的助詞系統仍處在自我調整的過程。
注釋:
[1]郭錫良 漢語史論集(增補本)[M].商務印書館,2005版.
[2]馬建忠 馬氏文通 商務印書館[M].1983 年,323 頁.
[3]周秉鈞 古代漢語綱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9版 394頁.
[4]馬文熙、張歸璧等編著 古漢語知識辭典[M].中華書局2004版.
[5]見汪維輝《隋一東漢常用詞演變研究》序,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
參考文獻:
[1]郭錫良.漢語史論集(增補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石毓智《漢語發展史上結構助詞的興替論“的”的語法化歷程》[J].中國社會科學1998(6).
[3]巢穎《<三遂平妖傳>助詞研究》[C].華東師范大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