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藝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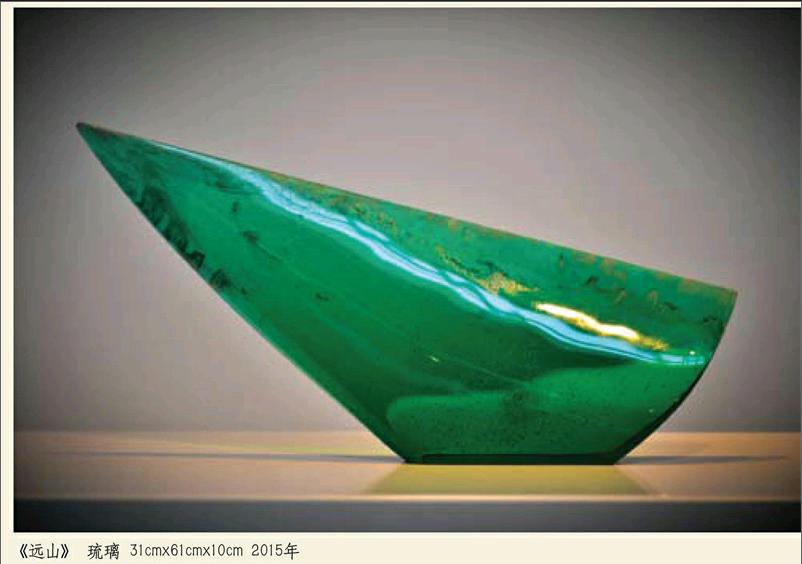
2016年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建院 60周年,雖然現在學校已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但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學術精神和傳統早已鐫刻在老中工幾代人的心中。從 1978年考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38年過去了,38年來我和學校一起成長前行。 回想學習美術的過程,從5歲到上中學之前,我一直住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宿舍兼工作區,那是個大院子,我們都叫它“大廟”。現在才知道是清代寧郡王府。童年很快樂,其中有個樂趣就是看話劇。因為排演廳就在院子里,平時的排練、彩排直至正式演出,經常看。許多時候,并不知道戲的內容,就是覺得好玩。日子久了,一些內容和場景,特別是多彩變換的天幕,也讓自己或激動、或興奮、或流淚,也會默默模仿戲中英雄的樣子。也許這就是潛移默化,是藝術的影響吧。隨著年齡增長,逐漸明白了戲中所表現的是與非、美好和丑惡,要做好事幫助別人。這種藝術的熏陶,潤物無聲,不知不覺深深鐫刻在我童年的記憶里,讓我對美有了理解和追求。現在我還記得一些戲的名字,《青年近衛軍》《羅密歐與朱麗葉》《雷鋒》《忠王李秀成》《費加羅的婚禮》《杜鵑山》等。兒童藝術劇院的戲更容易接受,《馬蘭花》《岳云》《以革命的名義》《箭桿河邊》等等。在我的童年記憶里,他們留給我許多美好和樂趣。那時,也經常看舞工隊繪景、制景,道具組作道具。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中上了小學,我在小學進了美術組,學畫畫、出板報。畫畫就是在這樣不知不覺中喜歡上的。中學時代以及工作后的業余美術實踐,加深了我對于繪畫的熱愛。“文革”后期,在文化宮的短期學習對我幫助很大,加之父親帶我去看北京畫院一些先生們繪畫,讓我從中獲益匪淺,以致堅定走上學藝之路。 1978年,我考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開始系統地學習美術,從理論到實踐補了很多的基礎知識。特別是辯證地認識藝術的能力,學會了思考和發現問題。譬如:老師在素描課講了“盡精微,致廣大”的觀察方法。在圖案課上知道了“以簡為繁,以素為炫”的裝飾真諦。工藝美院注重藝術風格研究的傳統,中西貫通的教學理念對我影響頗深。張仃老先生的“畢加索加城隍廟”文字雖簡潔,但揭示了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的辯證認識論,從哲學的層面認識藝術,這些經典的思想對于我如醍醐灌頂般的點撥,終生受益。老師是人生的引導者,我有幸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遇到許多好老師、學者、藝術家。記得一次國畫課,白雪石先生帶我們去十渡寫生,傍晚寫生結束,隨白先生回駐地的路上,饑腸轆轆,只顧趕路。突然,白先生坐在地上,打開畫夾鋪好紙,取出筆墨、調色盒,畫起寫意風景速寫。當時心里還抱怨,老爺子還不快走,但當我定下心來,往先生寫生方向看了一眼,我被震撼了。那夕陽染紅了層層疊疊的山巒,非常壯麗。在被美的景觀震撼后便是慚愧。先生那時已經年逾花甲,還保持著對自然之美如此的激情,對藝術的熱愛、對美的追求成就了“白家山水”甲天下的美譽。這件事過去三十多年了,但是一直在鞭策著我,每當在困難或者成績前,我想懈怠、想放棄、要自滿時,它會提醒、告誡我。在我三十多年的執教過程中,這件事也時時提示我,怎么當一名好老師。 1982年,留校之際正遇時代變革,美術界也迎來了空前的開放。各種思潮學說紛紛涌入,令人目不暇接,那個時期,我 對自己的要求是,以不變應萬變,即對藝術的真、善、美的基本認識和理念不變,時光荏苒,只是遺憾自己學習不力,進步 有限。有幸的是,能以青年教師的身份近距離感受前輩祝大年、梅劍鷹、白雪石等先生的風范,受益無限。 自2000年到現在,還來不及感嘆光陰似箭,十幾年就過去了,回想十幾年的苦苦求索,盡管充滿艱辛,在玻璃藝術教學、創作和理論的探索方面確也做了許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別在工藝美術系的教學,接觸到了全國工藝美術行業,見識到了多種藝術形式,以大美術的視角觀察,開闊了眼界。創作實踐上也跨越了“禁界”。金、木、水、火、土都是創作的媒材,精神更加放松和自覺。這些年不斷地在思考,感悟頗深。諸如,何為藝術、藝術表現的方法,不同學科如何交叉,科學與藝術的關系諸多問題常常縈繞心頭,存于腦海,自問自答,力求甚解。藝術學習是要花費巨大精力去實踐探索的,需要寬容、包容的胸懷,這不僅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精神。這些年從未敢懈怠,以“爐火正紅”為座右銘,鞭策、激勵自己努力,在藝術創作方面盡可能做到審美情理的通達,力求藝術形式的審美傳承,努力把握自己,堅守初衷,而不隨波逐流,在對傳統文化深入學習的基礎上,不斷探索,腳踏實地地進行藝術實踐。 每當憶及過往的支持與信任,心中充滿無限感激,師長、好友、親朋總是在關鍵的時刻給予巨大的精神支撐,令我堅定勇往直前。我由衷地感激、珍惜這寶貴厚重的情誼,更要加倍地努力。 王建中: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