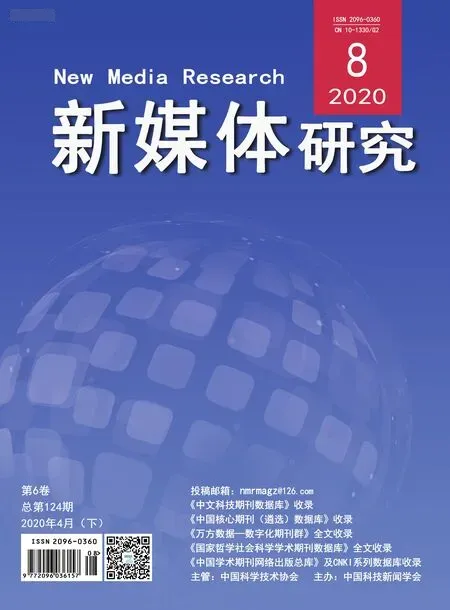吐槽彈幕與網絡節目的互動性探析
王海龍+景慶虹
摘 要 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的普及,網絡越來越成為人們觀看節目的重要途徑,吐槽彈幕作為網絡節目與觀眾互動的重要形式。通過分析當下深受青年網民喜愛的《吐槽大會》,研究吐槽彈幕的發送形式和文本類型以及網絡節目如何與觀眾實現互動,探析現在網絡節目利用彈幕開展互動的問題所在,并提出改進互動性的若干建議。
關鍵詞 吐槽彈幕;網絡節目;互動性;吐槽大會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7)08-0047-03
2017年開年之初,一檔由騰訊視頻和上海笑果文化傳媒公司打造的喜劇脫口秀《吐槽大會》爆紅網絡,10期創造13.8億點擊量的奇跡,因此被稱為最具有“網感”的節目。網絡節目的“網感”即強調節目與觀眾的心理互動,《吐槽大會》節目通過吐槽彈幕增強互動感和共享體驗,造就其成功的收視效果。自2014年提出推進“媒介融合”以來,實現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將傳統文化和新型的傳播方式相結合成為網絡節目制作、推廣的重要發力點。吐槽彈幕是網絡文化和青年亞文化融合后的新型技術表達方式,大大提升了網絡節目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性。國內最早提及是從技術角度介紹土豆網“豆泡”功能[1],此后有學者從文化角度研究彈幕網站[2],隨著吐槽彈幕與電影的結合,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吐槽彈幕與觀眾的互動性研究[3-4]。當前與彈幕吐槽傳播相關的研究前沿已經轉向互動性研究,而互動性研究中又以用戶間彈幕互動研究為主,彈幕與節目互動性研究缺少,本文結合《吐槽大會》的案例對吐槽彈幕與網絡節目的互動性做具體研究。
1 吐槽彈幕與網絡節目融合,締造青年網民的樂土
吐槽是源自日本的一種青年亞文化現象,是指用詼諧或者諷刺的語言表達對事物的看法,吐槽群體主要是偏愛漫畫(animation)、游戲(game)、動漫(comic)的御宅一族,因此在我國也稱之為ACG領域,吐槽群體源于“對二次元文化的認同[5]”而聚合,吐槽是由日本傳統藝術“漫才”發展而來,“漫才相當于中國的傳統相聲”[6],主要以“揭老底、抬杠”的形式表達情緒和觀點。而彈幕是一種技術手段,主要是指為用戶提供可編輯的文本框,用戶可以設置文本內容、字體、顏色、大小以及出現在屏幕中的位置,同時有些網站還支持將編輯的內容轉發到社交平臺。
吐槽彈幕初始用戶群體為ACG領域的“宅民”,這一群體追求獨立又害怕孤獨,吐槽彈幕迎合了有共同愛好者之間進行交流的需求。傳統的交流方式屬于觀后交流,不能滿足很多“宅民”一邊觀看一邊表達看法的沖動,吐槽彈幕則可以通過發送字條的形式實現這樣的需求。尤其在網絡電視和新興媒體興起后,原有的單向傳播方式被打破,加強情感溝通、實現互動對話成為網絡節目和視頻觀看者的迫切需求,由于吐槽彈幕能夠產生“圍觀式的觀感體驗[7]”,使得使用群體逐漸擴大,被更多的青年人接受。因彈幕制造的圍觀效應會產生組織歸屬感,讓更多的青年網民仿佛找到“知音”,例如《吐槽大會》中主持人張紹剛和策劃人李誕經常表示“你懂我”,這三個字道盡所有吐槽彈幕用戶的心聲。因此,吐槽彈幕與網絡節目的融合締造了青年網民的樂土。
2 從《吐槽大會》解析吐槽彈幕發布形式和文本類型
一些學者將吐槽彈幕營造的“青年網民的樂土”稱之為“狂化”“肆意情感宣泄”和“過度娛樂化”,但是筆者看來為一種現象做出定義要首先要對其內容和發布形式進行研究,才可以做出相對定論。
2.1 從吐槽彈幕的發布形式來看其存在三個方面的特點
2.1.1 發布時機碎片化和隨機化
碎片化和隨機化體現的是彈幕用戶使用時間和地點受約束程度低的特點。網絡節目中是否吐槽、吐槽什么內容都是隨機形成的,有時甚至不受節目本身的制約,可能源于發布者實際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心情狀態。這種隨時隨地能表達情緒的功能適應現代人的生活節奏。
2.1.2 網絡節目本身引導產生的彈幕吐槽,同時彈幕吐槽反饋節目本身
網絡節目本身具有自己的節目定位、文本設計和情節規劃,因此在腳本寫作和節目制作環節已經由策劃人埋伏很多的“槽點”,這些“梗”能夠有預期地引起觀眾吐槽。同時《吐槽大會》策劃者能通過對吐槽彈幕的閱讀發現有價值的信息,比如觀眾對節目的什么環節或者什么人偏愛,對節目的什么地方存在不滿,以及背后暗藏的改進建議。例如,觀眾偏愛池子的“知識點”和“有點狂”,節目組根據觀眾的喜好將這兩個點固化下來,成為觀眾期待的“包袱”;還有全場為了緩和節目沖突性,塑造了主持人張紹剛的“惡”形象,有意識地分化觀眾吐槽對象,觀眾也在彈幕中給予回應,“懟”主持成為節目的亮點。在大數據技術廣泛引用的今天,吐槽彈幕作為海量數據來源,能夠為分析節目制作和推廣提供可參考的數據支撐。
2.1.3 吐槽群體的“自嗨”
吐槽人群往往有自己特定的語言或者表達方式,網絡節目中主持人和嘉賓也經常涉及這方面的用語,例如BGM在網絡語言中是背景音樂(background music)的意思,又是在吐槽彈幕中可能代表人物的“悲慘命運”或者搞笑結局(引申自電影《夏洛特煩惱》的背景音樂《一剪梅》),或彈幕用戶提出一個與節目相關或無關的問題,其他的用戶會做出相應的回答。
2.2 從吐槽彈幕發布的文本內容來看,也主要集中在四種類型
2.2.1 幽默搞笑類
一方面幽默可以說是吐槽彈幕的先天基因,另一方面通過詼諧的語言可以很容易引起其他用戶的共鳴。比如節目中形容某嘉賓發際線比較靠后時說“頭發給眉毛讓路了”,形容染發的策劃人是“后殺馬特時代的先鋒”等。
2.2.2 謾罵嘲諷類
謾罵嘲諷的內容是吐槽彈幕的消極內容,引發原因常來自節目以外,可能因為對某些節目嘉賓存在不好的印象或者當時的心情煩躁需要發泄途徑。其表現形式有對網絡節目的侮辱,也有對里面嘉賓的挖苦,或者挑釁其他觀看視頻的用戶。例如將韓國明星宋仲基寫作“送終雞”,嘲諷客串主持人王自健和嘉賓曹云金等。
2.2.3 意見建議類
意見建議類的吐槽對網絡節目來說最具有價值,通常會直接關系到節目的制作和嘉賓選擇。在《吐槽大會》的往期節目中,節目組經常爆料策劃人李誕團隊為了收集反饋信息,常常把一期彈幕看許多次。比如有的網友建議“正式節目開始前的花絮應做成高清”“讓蘇醒常駐”“不要老看提詞器,脫口秀不是背書”等等,對節目視頻效果,嘉賓任選以及表現力等環節都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2.2.4 無意義表達
無意義的表達存在兩種狀況,一是觀眾本身處于一種無聊的狀態,二是覺得某段節目很無聊,偶爾會發現吐槽彈幕中飄過“aaaaaa”“滴滴滴滴”等字眼和一些圖形。
3 吐槽彈幕與網絡節目的互動效果及問題
吐槽彈幕與現代青年網絡生活的互相適應促使其成為流行的青年人交流方式,正在重新定義“觀劇模式[8]”和塑造新的觀看習慣。從《吐槽大會》欄目的本質上看是一檔脫口秀節目,結合本檔節目可以發現,吐槽彈幕對網絡節目的影響主要存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網絡節目制作起到指引作用。通過對吐槽彈幕發布形式的研究發現,吐槽彈幕與網絡節目直接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一方面,吐槽彈幕產生源于節目腳本寫作時候的“槽點”設計;另一方面,通過研究吐槽彈幕提供的意見和建議可以改進節目制作。
第二,營造觀看氛圍,塑造新的觀看習慣。“互聯網+”時代,電視節目制作逐漸引進微信紅包,“搖一搖”和二維碼等技術,但是從真正互動性交流的角度來講,這幾種互動性遠不如吐槽彈幕。首先,現有這些創新的互動方式使用起來較為麻煩,繁瑣的操作過程或者附加的廣告推廣等極容易引發用戶反感。其次,節目組提供的概率渺茫的獎金獎品,對于觀眾吸引力并不大,搖紅包看看電視遇冷就是最好的說明。再者,觀眾在看節目時更渴望的是心理層次的追求,社會屬性的需求遠遠大于物質刺激。吐槽彈幕便捷編輯和即時分享,能夠說實現用戶群體的社交需求。
第三,促進裂變傳播,助力網絡節目推廣。吐槽彈幕發布形式特點之一就是吐槽群體的“自嗨”,所謂“自嗨”是指吐槽人群可以利用彈幕進行交流分享感受,并在這些話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形成新的話題,實現二次傳播直至N次傳播的裂變式傳遞,這種特點對于節目宣傳推廣起到巨大的作用。通過互聯網可以發現,觀眾對某些明星“陳年舊事”的挖掘以及觀眾對當年事件的追憶幫助節目做了宣傳。
雖然從節目點擊量和收視率等數據分析節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吐槽彈幕與網絡節目互動性方面《吐槽大會》仍存在一些問題。《吐槽大會》每期都會請到一位(或組合)有“爭議”的明星,這位明星曾經有過引起大眾感興趣的話題。從十期的節目來看,其選取的明星確實有可談之處,但是出于對明星形象的維護以及節目與明星之間的協議,吐槽的點主要是三種類型:一是明星已經被公眾所知的錯誤或者窘境;二是公眾未知的“趣事”,凸顯明星的性格特征的正面事情;三是根據觀眾彈幕反應出來的偏好,臆造一些話題引發吐槽。這些槽點和段子明顯讓人感覺沖突性不足,尤其是對于一些重量級嘉賓幾乎是以變相捧夸為主,讓觀眾感覺不過癮、沒力度,因此也就降低彈幕發送頻率。吐槽是一種隨機性的行為,節目程式化的操作方式使得許多觀眾認為該節目是在變相為明星做公關。節目策劃者組織一些人以朋友身份進行吐槽,由嘉賓到主咖(主嘉賓)輪流吐槽次序固定不變,吐槽的類型固定在公眾既知、無關緊要、臆造話題和變相吹捧四類,讓觀眾難以感受到節目設計上的精巧和變化,容易產生厭倦乏味,使得節目成長為品牌欄目的可能性較低。
4 網絡節目利用吐槽增強互動性建議
通過對《吐槽大會》以及其他一些利用吐槽彈幕的網絡節目的觀察,可以發現吐槽彈幕雖然成為網絡節目的“寵兒”,但是對于彈幕的回應性、彈幕用戶關系維護以及彈幕本身的規制問題仍需要進一步研究改進。
4.1 應在節目制作環節增強對吐槽彈幕的回應
現有的網絡節目沒有對吐槽彈幕做出有效回應,節目環節設置上或者現場舞臺背景方面沒有嵌入吐槽彈幕。但這并不表明很多節目沒有意識到吐槽彈幕的價值,恰恰相反,網絡節目的策劃團隊會拿出巨大的精力去瀏覽。難以形成回應性的原因主要是節目錄制和播放相分離的制作機制,錄制、播出和吐槽不能實現同步。這種問題可以通過設計節目預覽機制以及回應板塊加以解決。預覽機制就是將吐槽和節目預告相結合,通過發布預覽提前收錄一批關于即將邀請的嘉賓團的吐槽;回應板塊是主持人或者嘉賓對往期經典吐槽以及預覽機制中收集的吐槽加以點評、回復。這樣可以密切網絡節目與觀眾的聯系,使觀眾的存在感得以體現,同時提升節目的互動趣味。
4.2 利用新媒體建立網絡節目對應的討論社區
吐槽彈幕可以稱之為新媒體技術與網絡節目結合的產物,因此可以利用新媒體的功能提高節目互動性。利用微信公眾號、貼吧、微博等新媒體社交平臺建立節目互動圈,實現吐槽由視頻向社區的轉移,雙管齊下增加觀眾黏度。
4.3 把握吐槽自由與文明的平衡,完善吐槽彈幕規制
吐槽彈幕傳遞的內容不全是積極的,在吐槽彈幕中經常會發現消極負面的言論,破壞網絡文明和節目觀賞氛圍,因此應該加強對彈幕內容的技術規制。但是從吐槽機制產生來看,吐槽是隨性的、激發性的行為,如果規制力度把握不當則會扼殺這種互動形式。吐槽彈幕發送前,完善實名認證,一些網絡節目彈幕發言不需要登錄,隨著社交軟件實名制的普及,通過社交軟件登錄發送彈幕必須作為一種強制性要求;吐槽彈幕發送后,引入關鍵字限制技術,將涉黃、涉恐等敏感字眼自動刪除。
5 結束語
綜上所述,媒介融合時代促進互聯網、新媒體與網絡節目相融合,已經成為未來網絡節目發展的重要走向。利用吐槽彈幕技術增強網絡節目與觀眾互動性,既是促進節目制作水平和推廣能力提升的渠道,又是提升網絡用戶觀看效果凝聚青年群體的重要手段。新時期,加強規制吐槽彈幕在網絡節目中的使用方式研究,將為吐槽彈幕服務于網絡節目和網民群體提供健康的環境。
參考文獻
[1]趙天新.土豆網彈幕產品“豆泡”視頻分享融合SNS元素受捧[N].通信信息報,2012-8-29(B13).
[2]陳一,曹圣琪,王彤.透視彈幕網站與彈幕族:一個青年亞文化的視角[J].青年探索,2013(6):19-24.
[3]張釵.彈幕視頻的互動現狀及發展策略[J].青年記者,2015(5):65-66.
[4]宗申.“彈幕”功能及互動模式研究[D].天津:天津師范大學,2016.
[5]張聰,陳穎,程遠涉.論彈幕在電視媒體中的應用——基于對彈幕受眾的實證研究[J].中國電視,2016(10):71-75.
[6]吳君.抵抗與表演:“吐槽文化”的傳播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5.
[7]江含雪.傳播學視域中的彈幕視頻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4.
[8]曾一果.新觀眾的誕生——試析媒介融合環境下觀劇模式的變化[J].中國電視,2015(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