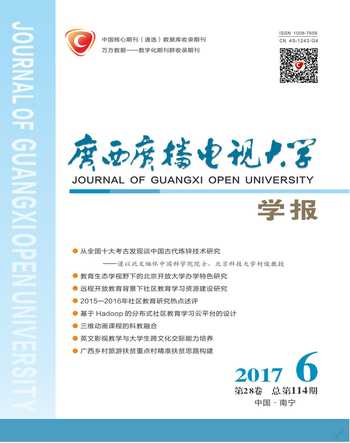論李綱《和陶詩》“出世”與“入世”的思想
[摘 要]李綱于貶謫之地創作大量“和陶詩”,表達了自己的“出世”之意與隱逸之志。然而在客觀時局、人生經歷與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和陶詩”中流露出濃濃的“入世”思想:憂心時局,關心民瘼;貶謫之痛,壯志難酬;思親念友;退而在野,樂遂其志。李綱“和陶”實質是為尋求心靈慰藉,“出世”之念實際上是平息“入世”之痛的手段,“出世”為虛,“入世”才為實,詩人最終人生指向仍為“入世”。
[關鍵詞]李綱;和陶詩;出世;入世;思想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656(2017)06-0087-05
梁代鐘嶸《詩品》贊陶淵明乃“隱逸詩人之宗”[1]與昭明太子蕭統《文選》收錄陶詩七題八首且對其進行高度評價,陶詩逐漸被文人接受,并將其作為學習對象。唐代崔顥、韋應物、白居易、宋代梅堯臣等,皆偶作學陶、效陶、擬陶之作,但這并非真正“和陶詩”。“和陶詩”不是亦步亦趨的模擬之作,而是后人因慕其人格、好其詩歌,取陶詩文題,或應其旨意,或取其韻腳,融化己意,進行藝術再創造而成的自覺之作。因此蘇軾109首和陶詩才為肇始,我們可以從東坡先生《追和陶淵明詩引》中得知:“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于東坡”[2]。自蘇軾開創之后,“和陶”之風綿延不絕,好比“汩汩小溪,奔騰不息,終竟匯成蔚然大觀的江河之勢”[3],而李綱則為眾多溪流中的一支。
李綱,字伯紀、天紀,號梁溪先生,宋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因人生經歷的相似性與對陶淵明人品詩品的追慕,李綱于謫居之地創作了85首“和陶詩”,其間縈繞著詩人濃濃“出世”之意。可“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為社稷生命安危”[4]P1797的李綱,面對山河破碎、生靈涂炭的動蕩時局,不可能隱逸塵外而對此置若罔聞。因此雖遭貶謫,李綱終不失拳拳愛國之心與盡忠報國之志,從而“和陶詩”中存有大量“入世”思想。現筆者通過仔細研讀李綱“和陶詩”試圖探討詩人“出世”與“入世”矛盾心態,并挖掘二重思想的真正旨歸。
一、李綱“和陶詩”中的“出世”思想
李綱“和陶詩”皆作于貶謫閑居之時,寄寓了詩人“娛意泉石,忘懷世味”的隱逸之心與“出世”之意。李綱生于宋神宗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卒于宋高宗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此階段乃宋朝最為黑暗動蕩的時期:金人渝盟,大肆南下;統治集團昏庸無度,驕奢逸樂,橫征暴斂;洪澇旱災,接連不斷生靈涂炭;山河破碎,宋朝呈現江山即倒之勢。艱危之際,李綱“知天下有安危,而不知其自身有禍福”[4]P1775,許身為國,奏疏列論,主戰反和,數進忠言良策,渴望恢復中華,拯民于水火,做了許多利國利民之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京師大水,朝中卻無敢言其災異者,而李綱披肝瀝膽,呈《論水災事乞對奏狀》《論水便宜六事奏狀》二書,分析水患之由,提供治水之法;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敗盟,攻打京城開封,李綱刺臂血上書,促成內禪,徽宗傳位于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李綱以文臣領武將令,率領開封軍民浴血奮戰,取得“東京保衛戰”的勝利;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南宋王朝建立,李綱任宰相之職,對外主戰,積極收復失地,對內整飭綱紀,加強政治軍事經濟改革與建設,造就“建炎中興”局面。可是,李綱的盡忠職守、主戰反和、耿直敢言不為昏君賊臣所容,以致遭受罷黜貶謫,漂泊羈旅于沙陽、寧江以及鄂州、澧州等地。李綱精忠為國,卻逢昏君小人而屢遭貶謫,人生的起浮潮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詩人的隱逸之心。
李綱“出世”之意除客觀時代因素與個人遭際影響外,還受主觀佛道二教信仰的隱性化推動。李綱乃忠實佛教信徒,張培峰先生曾言及:“李綱對佛教研究之深,信仰之堅,是不下于宋代任何一個信佛士大夫的”[5]。他認為自己“前身真是老浮屠”[4]P302,對佛教存有莫名親切感,“每見招提心即喜”[4]P302,因此自幼習讀佛經典籍,打坐參禪,交游僧人。同時李綱生長于多僧人、佛寺的福建邵武,加之父親李夔好佛,常與僧人探討佛法,使得李綱從小便有接觸高僧佛法的機會。李綱也喜道教,少時便習道教典籍:“少年學神仙,日誦《瓊笈經》”[4]134,難免會受道教思想影響。李綱少習佛道,佛家言“靈明空寂、寂滅無為”的“出世”思想與道家言“自然無為、親近自然”的“隱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其遁世修隱思想無意識化。
主客觀因素促成了李綱的出世之心,加強了李綱的隱逸之志,李綱創作“和陶詩”直接動機因素便在于此。在和陶詩中,李綱道其隱逸之心、山林之樂乃天性使然:我本田野人”,“是心本純白”,加之有感于人生短暫,而希望自己“勿使吾心違”,因而渴望盡早隱居山林田園而忘塵世:“我欲隱山下,誅茅占其前”“不如早抽身,卜此山林居”“採芝白云中,愿學園與綺”。伯紀于《和陶淵明〈歸園田〉六首并序》[4]P131-P133《和淵明〈歸園田居〉六首》[4]276-P278中勾勒了自己向往的隱居生活:他并未擇其所貶之地沙陽、寧江、湖外而隱遁,他所向往的隱居之地乃家鄉邵武故居,故居落于梁溪旁,山環水繞,風景絕佳,乃桃源仙境,于此,詩人可游山玩水,覽風景名勝;可“手植松千株”,于蒼翠間開草屋八九間;可建書室以“著書聊寄懷”“膝橫五弦琴”“試鼓南風曲”“開懷酒一壺”“寓意棋一局”;可結蓮社侶,與僧人習佛參禪;可引梁溪水,灌萬頃田,獲累累碩果;可設酒殺雞,宴請鄉鄰友人,“神游八極表,心跡兩超然”,忘懷世味,寧靜閑適,和樂融融的家鄉梁溪隱居生活乃伯紀之“素志”,其言有:“常謂享此樂,可以終華年”。但是梁溪之隱終究是夢,由于伯紀“誤學霸王略”奔走于官場,而“為世網所嬰”,以致“擾擾不得閑”“未遂脫塵鞅”;而今又羈旅于外,漂泊猶未歸;且連年兵叛盜起,景物佳處鞠為灰燼,隱居梁溪之夢破碎。
但是伯紀隱逸之志是堅定的,如他所言:“立志既爾爾,豈復中道回”[4]P133。既然無法身隱于梁溪,那就于貶謫之地做到“心隱”。因感自身“獨酌誰與共,獨歌誰與疇”,無志同道合之朋儔,伯紀追慕古人,視其為知心之人,而又尤其欽慕陶淵明,“我讀古人書,獨與淵明親”。《次韻淵明九日閑居》道:“緬懷陶淵明,雅志與我俱。還看枕間屏,乃是歸來圖。古人不予欺,歲暮將何如”[4]P267,雖然淵明骨已朽,與李綱時隔千載,但他將其視為摯友,也把自己看成淵明的知心人。此外,疏廣、賀知章、梁鴻、管寧等皆受其愛慕。可見,通過追慕古代隱士,學其安平樂道之志,而達到“心隱”。其次,飲酒也為“心隱”之妙法。《次韻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并序》[4]P132-P135稱飲酒可忘萬物,解萬憂:因累于“世網”而“慘淡終年悲”,可“得酒可歡喜,醉鄉真可依”;可寬羈旅之情,“既醉謝羈束,不知冠屢偏”;可澆壯志未酬之悲,“獨酌一杯酒,不知窮與通”;可得人事之純真,“舉世人事偽,惟酒存天真”;可避亂世,歸太平,“笑指黃金罍,是中可逃秦,糠秕鑄堯舜,萬世同塵埃”。通過飲酒,伯紀于醉鄉之中,無拘無束,沉醉于山林桃源之樂。最后,于佛道二教中求“心隱”。謫居沙陽、寧江、湖外等地時,李綱雖仕途低迷,但有更多時間精力習佛悟道。他于《次韻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并序》(其十八)道:“人因謫而窮,我因謫而得。博考圣賢書,獨立愈不惑”[4]P134,可見,此時李綱能用心佛學,博覽佛家典籍,打坐參禪,同時常拜訪高僧(丹霞宗本禪師、惠深),參禪問道,也可與傾心于佛學的士人、朋友(陳淵、鄧肅、羅疇、李光等)探討佛學旨要。日復一日,李綱佛教思想逐漸成熟定型。貶謫期間,李綱除習佛外,還修“神仙之術”與“煉丹之術”。《次韻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并序》(其十七)載有:“交梨與火棗,丹鼎期必成。呼吸存夜氣,宴坐至五更。豈知糟麴中,醉鄉即黃庭。玉池灩生肥,天鼔常自鳴。酩酊欲仙去,超然離世情”[4]P134,詩人可以通過冥坐、煉丹來消遣塵世之煩憂。因此,李綱參禪悟道,修心養性,使心脫離塵世,而達到寧靜自然,實現“心隱”。
綜上所述,面對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宋王朝,李綱不失拳拳愛國之心,關心社稷蒼生,察政治得失而建言獻策,主戰反和而馳騁疆場,居宰相之位而勤政治國。可君王昏庸小人離間,使他飽受貶謫之苦,這將加重伯紀隱逸之心。可因累于世網、連年兵火、漂泊羈旅,李綱梁溪隱居之夢破滅,但他并未放棄隱逸之志,于追慕古人、飲酒、參禪悟道中尋求“心隱”。由此可見李綱“和陶詩”中“出世”心態是強烈的。
二、李綱“和陶詩”中的“入世”思想
儒釋道三教皆注重個人內心的熔鑄,但之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處理上,儒家主張“入世”,“正己,修身”是為“治國,平天下”;而佛道主張疏離(即為“出世”),打坐參禪、采藥煉丹是為明心見性、遁世修隱。李綱雖然好佛道,但是儒家思想乃為其主導思想,并最終決定其出處進退。因此,李綱“和陶詩”中雖傾注自己的“出世”之意;但詩歌中也處處彰顯著自己的“入世”思想。
李綱儒家思想的形成與強化受其家庭影響。“其先系出有唐”[4]P1695,曾祖父、祖父品行操守皆高,為鄉閭所宗;父親李夔“以進士起家,時為名卿”[4]P1695,學識淵博,忠君愛民,為官清廉,仕途暢達,被追封衛國公;母親吳氏,溫柔賢淑,相夫教子。由此皇室淵源、祖先品行的典范、父親的榜樣力量、母親的教育有方皆作為外因促使李綱自幼便受儒學熏陶。在李綱儒家思想的形成與強化過程中,外因固然重要,但自身內因才起決定性作用。李綱于《擬騷并序》中道:“長游學于四方兮,爰觀光與國賓。服詩禮之嚴訓兮,傳忠孝之家聲。攬百氏之所傳兮,味《六經》之純精”[4]P8,可知他幼年便游學四方,熟讀儒家典籍,確立“安宗社,保生民”的儒家人生觀。李綱崇儒且好佛道,主張三教合一,但以儒家作為主導思想,他在《三教論》中指出:“從儒。彼道、釋之教,可以為輔,而不可以為主;可以取其心,而不可溺其跡”[4]P1361。面對風雨飄搖的時代局面,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李綱不可能隱遁世外,“坐視世界的衰落而無動于衷,無論在平時或是亂世,都不能忘情怎樣變道為有道”[6]。因此,即便被貶湖外,伯紀仍未辭官歸隱,而是在謫居之地,勤政愛民,治地有方,等待著朝廷的征召。由此可見,無論是讀書求學,還是在朝為官,還是被貶湖外,李綱的“入世”思想始終伴隨,如林則徐題福州小西湖李忠定公祠:“進退一身關社稷,英靈千古鎮湖山”。這就決定李綱“和陶詩”中“入世”心態是顯而易見的。
李綱將“憂心時局,關心民瘼”之心寄寓于“和陶詩”中。伯紀憂心異族入侵,主戰反和,力主收復失地,如《和淵明擬古九首》(其五)所言:
立國有常理,恩威撫要荒。胡為決藩籬,坐使寇及堂。憑高寓遠目,中原氣蒼茫。昔時冠蓋地,今日爭戰場。玉輦幸朔漠,金椀出北邙。腐儒獻竒策,碧衣坐稱昂。儻無濟時略,何以綏四方。蒼生未蘇息,慨嘆情內傷。[4]P278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逾盟,大肆南下,宋欽宗慌亂出逃。李綱力勸欽宗留守京城,并主戰反和。他發揮濟世才略,親自督戰,團結百姓,取得東京保衛戰的勝利,而“綏四方”。可是后因主和派的干擾、李綱的貶謫,金人囂張氣息復燃,戰火連年,“蒼生未蘇息”。憂國憂民,慨然神傷,由此可見伯紀“入世”之心。除此之外,伯紀還于“和陶詩”中揭露因統治者的驕奢逸樂、橫征暴斂,而導致“貧者無置錐,富者連阡陌”的局面。而嚴重的貧富懸殊、賦稅徭役導致農民起義不斷,《和淵明〈游斜川〉》言有:“盜賊紛滿眼,事故端百憂”[4]P281,《和淵明〈擬古九首〉》(其四)道:“一隅豈易保,巨盜連荊舒”“江邊畏群盜,歲暮當何如”[4]P278,詩人在此出于忠君以及階級局限性將農民呼為盜賊,這或許帶有輕視反抗之意,但是明確起義緣由(官逼民反)之后,莫不同情百姓悲慘遭遇:“世態互陵滅,冰炭方凝焦”。伯紀在“和陶詩”中還揭露了官場的黑暗,黨爭不斷,小人當道,忠臣蒙難,如《和淵明〈擬古九首〉》(其三)中所言:“階禍初甚微,智者能要終”,“時平足諛佞,世亂多奸雄”[4]P278。面對紛亂世態,伯紀理想的社會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因此取陶詩韻腳作《桃花源并序》,表達對“無賦稅徭役、兵連禍結,百姓躬耕自樂,純樸自然,閑適寧靜,和樂融融”生活狀態的追求。除此之外,伯紀于《和〈勸農〉篇》[4]P280-P281中表達了自己的農本思想:鼓勵百姓勤勞躬耕,目的在于國家富強、社會安定。
伯紀關心社稷蒼生,希望為拯民于水火而獻一份力,可屢遭貶謫,因此“和陶詩”中可見其“貶謫之痛、壯志難酬”的悲傷情緒,這也是“入世”心態的折射。如《次韻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并序》(其十九):
結發觀國光,壯年躋膴仕。懷恩重泰山,欲報輕小巳。幸立不諱朝,緘默誠可恥。晨趨玉陛前,暮謫閩山里。飄零若萍梗,此志誰復紀。行藏豈異途,川流與淵止。不如飲美酒,世態何足恃。[4]P134
其間,詩人言及自身意氣風發,渴望建功立業,為報君恩,而盡忠職守,為國為民。可世事難料,“晨趨玉陛前,暮謫閩山里”。自己不在君側而漂泊江湖,感慨生不逢時,壯志難酬,所謂“嗟我方遠謫,慷慨念平生”“羈縶因羅網,慘澹終年悲”。又如《和淵明〈貧士〉詩七首》(其二、其四):
淒涼寓僧舍,寂寞坐松軒。雖辭萬鐘祿,尚未自灌園。仲尼猶在陳,我廚晨有煙。藜羮得一飽,滴露味自研。寒窗寫《周易》,更詠五千言。儒生真可笑,餓隠稱其賢。[4]P266
骯臟老張鎬,寂寞窮黔婁。古人日已遠,此意誰復酬。墨翟突不黔,仲尼轍環周。豈為一身計,實懷四海憂。沮溺但躬耕,吾豈斯人儔。有酒且徑歸,無酒不必求。[4]P267
前一首詩歌,伯紀主張隱逸,但反對“餓隱”。雖辭萬鐘祿,但未躬耕田園,詩人尚能“藜羮得一飽,滴露味自研”,可見在一定程度上他接受朝廷的俸祿與友人的接濟。因此伯紀并未完全否定功名富貴,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視其為自己隱逸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后一首更為直接表達自己的“入世”之心:戰國之黔婁、唐代之張鎬相隔久遠,當今有誰效其歸隱,何況墨翟突然放棄百姓身份而為官,仲尼驅車周游列國,因此伯紀“懷四海之憂”,不愿與沮溺為友而躬耕于田,愿安社稷、保生民。
伯紀向往梁溪隱居,除前文所言的主客觀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親念友,這也是“入世”之心的顯現。詩人于《和淵明〈貧士〉詩七首》序言中提及詩歌創作意圖:“次其韻,將錄寄梁溪諸弟,以發數千里一笑”[4]P266,《其一》之言“迂疏得遠謫,漂泊將何依?區區一寸心,未報三春暉”[4]P266,弟兄親人皆居梁溪,而自身離群,棄家遠征,未能孝敬長輩、幫助兄弟,照顧妻子兒女,自責愧疚,急切想要歸家。當他得到來自梁溪家書時,知家人之境況,倍感欣慰,如《和淵明〈答龐參軍〉》[4]P283所言:“剝啄叩門,梁溪有書。發函讀之,遠懷以娛”,“左圖右書,中心好之”,“三復佳句,實慰所思”,“無遐邇心,好音數聞”。儒家將三綱五常,除君臣之道外,父子、夫婦、兄弟、友人皆為受儒家重視,因此李綱于“和陶詩”中所言之“思親念友”之情乃其儒家思想的外化,也為“入世”之心。此外,伯紀在“和陶詩”中表明自身雖遭貶謫,但“節義”不衰,“惟余節義士,可向編簡求”,“歲寒時艱,節義彌敦”。李綱一直倡導:“古之君子,進而在朝,則樂行其道;退而在野,則樂遂其志”[4]P1285,這與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7]相應,既然報國無門,那么應完善自身品德,將自己鍛造成節義之士。因此伯紀強調修身養性、重節義出自其儒家思想,也為“入世”之心。
三、小結
基于儒釋道三教思想的合一,李綱一方面行儒家“正己,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入世”道路,一方面追求率性而為、空寂無為、淡泊寧靜之“出世”人生。黑暗動蕩的世態與屢遭貶謫的人生經歷,一方面加重了伯紀的隱逸之心,但另一方面也感慨壯志未酬、報國之心未遂。由此“和陶詩”中“出世”、“入世”二重心態并存。但是于由“出世”“入世”所構建的天平上,兩者砝碼不可能對等。因為雖然李綱倡導三教合一,但這一思想提出的動機處于為政治國,且儒家思想居首位,即“治之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釋之教存而弗論,以助教化”[4]P1561,所以“安宗社,保生民”乃伯紀主導人生觀。因此,伯紀雖屢遭貶謫,但始終忠誠為國,重國家百姓之安危,而輕個人傷痛。“入世”之心強于“出世”之念。
李綱不可能忘懷社會、政治、蒼生,“和陶詩”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李綱無奈的憤懣之語與心靈良方,李綱追慕古人、飲酒、習佛問道無外乎是為尋求心靈安慰。因此,伯紀“出世”之念乃平息其“入世”期間所遭受的憤懣悲傷心態的手段而已,詩人最終人生指向仍為“入世”,“出世”為虛,“入世”才為實。
李綱和陶并非真正出于“出世”之心,這將導致李綱不能得陶詩“真淳”,但就“和陶”文學創作本身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對于李剛個人而言,有利于詩歌藝術的成熟多樣化與人格的完善,俗話說:“唱和相長”,李綱追和陶詩,通過體味陶詩聲調,揣摩作品意境,學習作品章法結構、語言詞匯,從而提高自身詩藝,加深詩歌意蘊,豐富詩歌風格。對于陶淵明接受史而言,陶淵明其人其詩受士人標舉而逐漸成為一種文化符號,這是東晉至唐宋文人共同努力的結果,而李綱在陶淵明文化符號的解讀與傳播中也盡了一份力。對于“和陶詩”創作本身而言,次韻和陶而寓己意始于蘇軾,此后蘇門弟子與其他文人翕然從之,推動了新的詩歌體裁“和陶詩“的創作,因此作為其中一員的李綱的“和陶詩”對于南宋、金、元、明、清“文人創作“和陶詩”或多或少有影響。
[參考文獻]
[1](梁)鐘嶸著,陳延杰注.詩品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58.
[2](宋)蘇軾.東坡全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0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440.
[3](元)郝經.陵川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9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61.
[4](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M].長沙:岳麓書社,2004.
[5]張培峰.宋代士大夫佛學與文學[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205.
[6]余時英.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15.
[7](漢)應邵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123.
[作者簡介]王倩,女,西南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元明清)。
[責任編輯 孔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