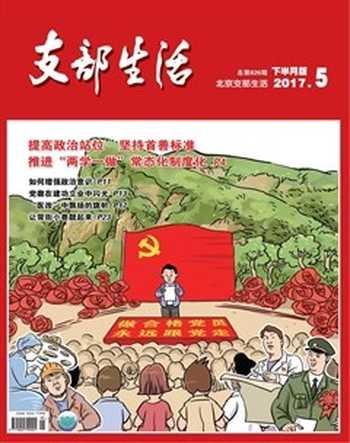“醫改”中飄揚的旗幟
陳寧 方園 柴衛紅



4月8日零時,北京3600余家醫院燈火通明。
“倒計時,3、2、1……電子病歷系統、門診住院收費系統、各橋接系統同時切換,各醫療信息系統運轉正常!”
作為全國醫療核心資源的聚集地,北京醫藥分開綜合改革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落地1個月時間里,全面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取消掛號費,設立醫事服務費,全面取消藥品加成,實施陽光采購,推促分級診療制度形成……北京衛生計生系統各級黨組織正帶領廣大醫務工作者走出依靠優質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的醫療新格局。
“備戰這場‘大考,緊緊依靠的是黨組織”
4月8日零時,第一張印有醫事服務費的就診憑條,清晰記錄著幾項收費項目的調整。對于北京市3600余家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來說,這背后是一場涉及將醫事服務費、435項醫療服務項目以及上千種藥價等準確導入醫療機構信息系統、一次又一次的測試信息系統和準備應急預案的“大考”。
為了這一天,在得到醫改通知之初,西苑醫院黨委就在第一時間成立了黨員攻堅小組,搭建新的醫療機構信息系統。
作為黨員攻堅小組成員,西苑醫院計算機信息中心黨支部的黨員張曉峰和同事們已經足足忙碌了3個多月。
調試、切換,準備應急預案,有時1個患者就有幾十個信息點需要調整,累了,就在會議室里打個盹兒;工作得太晚,就找張行軍床湊合一宿。
“這么多天不回家,愛人沒意見?”
“咳!她也在醫院加班。每天干得比我還‘苦。”
張曉峰的愛人李丹是醫院信息統計科主任,也是黨員攻堅小組的成員。醫院結束一天運營時,是李丹最忙碌的時候——“會不會給患者增加經濟負擔”“按新系統測算醫保基金能承受嗎”“醫院是否保持良性運營”,經她統計分析的各類信息,每天會按時發送到黨委書記劉婕和各科室黨支部書記、主任的手機上,供黨委班子研判。
與新系統“磨合”的3個月里,李丹幾乎天天加班,沒有請過一次假。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她硬是背著公婆給8個月大的兒子斷了奶,托付給家里的保姆照顧。系統平穩運行后,李丹抹起了眼淚——回趟家,8個月的兒子已經不認識自己了。但看到信息系統平穩過渡、沒有給一個患者帶來不便,李丹卻又說:“這就值得!”
黨員主動承擔起最繁重、最困難的工作,西苑醫院并非特例。“備戰這場‘大考,緊緊依靠的是黨組織。”北京市衛生計生委黨委書記、主任方來英說。醫改中,3600余家醫院幾乎都成立了 “黨員志愿者服務隊”“黨員攻堅小組”“黨員突擊隊”,通過充分引導黨員發揮模范作用,加班加點地完成政策培訓、系統調試、一線出診等準備工作,保證了醫改有序地開展。
信息系統準備就緒后,另一項考驗隨之而來。系統零時切換,最先面臨考驗的,是門診量巨大的夜間急診。對于一些供需矛盾突出的大型三甲醫院,形勢尤其嚴峻。為此,多家醫院黨委號召臨床一線的黨員醫生利用休息時間幫助急診醫生“消化”非急癥病人。
經過連續加班,北京兒童醫院內科門診黨支部書記郭琰因為炎癥導致了突發性耳聾。下班輸完液后,他轉身又回到了醫院內科門診部。“你怎么還不回去休息?咱們科所有黨員都到齊了,醫生已經是平時出診的兩倍了!”一名同事勸他靜養,盡早恢復聽力。
“正是工作壓力大的時候,我這個支部書記怎么能缺勤。”郭琰不由分說,進了門診室。他換了座位,用聽力較好的一側挨近患兒和家長,身體微微前傾,振作精神問診。焦急的家長帶著孩子來了又走,卻沒有一個看出郭琰的異樣。
凌晨12點半,郭琰和同事們送走了最后一個小患者,為急診留出了緩沖時間,保證了醫改平穩運行。第二天早晨8點,他又準時出現在了病房巡檢,開始了工作。
“讓醫生手中這支筆,寫下的都是患者利益”
“喲!掛號費漲了這么多?”
“咱們現在叫醫事服務費了,這總花銷漲沒漲,您看看我算的這筆賬?”62歲的王貴琴是北京世紀壇醫院離退休黨支部“守護天使”黨員志愿者團隊的一員。醫改以來,她每周都要抽出2天時間,在北京世紀壇醫院門診樓解釋、疏導:“我有高血壓,是個20多年的‘老病號。3月和4月同樣在這兒開了利血平等6種藥,一共便宜了117.16元,再加上醫事服務費,比之前還便宜了點兒!”
醫改前,和很多黨員志愿者一樣,王阿姨接受了市衛生計生委黨委、院黨委和離退休黨支部的3輪醫改培訓,醫改政策早已爛熟于心。她攥著手中的收費單據,一遍遍地給患者講政策,說得頭頭是道。
“這支黨員志愿者團隊,既是醫護工作者又是慢病患者,由他們向患者解釋政策更有說服力。”北京世紀壇醫院黨委書記李天佑談及成立志愿者團隊的初衷,這樣說道。現在,“守護天使”的黨員志愿者們每天活躍在北京世紀壇醫院的門診樓、放射科、中醫理療室等醫改政策變化較大的科室,引導患者就醫、為他們解釋醫改政策。
“以藥補醫”的舊機制下,醫院的1/3收入都來自藥品收入。醫院只有多賣藥、賣貴藥、多做檢查、多用耗材才能多掙錢,病人多有不滿。但假如患者一天繳1000元的住院費,其實只有7元屬于醫護團隊。提高醫事服務費后,雖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醫務工作者的價值,但有人不無顧慮:部分患者醫療支出增加,是否會引發新的醫患矛盾?
北京市衛生計生委黨委給出了清晰答案:“我們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讓醫生手里這支筆,寫下的都代表著患者利益。”方來英書記說,降低藥品、檢查費用,提高醫務項目價格,“這就好比一個人健身,雖然短時間內體重沒改變,但是脂肪在降低、肌肉增多了,肌體變得更健康了。”
從“以藥補醫”轉向“依靠優質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的運行機制,新醫改為提升醫療服務騰挪出了空間。北京市衛生計生委走得更遠一步,各醫院成立藥事管理委員會,全面考核醫生處方的合理性,讓醫生填寫每張處方單都慎之又慎,進一步優化醫療服務。
“解困局,疏解勢在必行”
北京雖然醫療資源密集,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想順利掛上三甲醫院的專家號,絕非易事。
然而,在北京“看病難”現象也是相對的:二級醫院和社區醫院環境不差、技術設備也齊全,卻門可羅雀,乏人問津。為什么會有如此大反差?一名患者回答得非常直接:“同樣的掛號費,我肯定到三甲來看!”
“鯀治水無功而返,失于堵;禹治水遺澤千年,成于疏。”解困局,疏解勢在必行。
北京醫改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積極引導分級診療機制:4類慢病,可在社區醫院開具最長2個月的長處方;同三甲醫院普通門診個人支付10元醫事服務費相比,社區醫院個人僅需支付1元,60歲以上的北京醫保患者則連這1元也免去了。
“增”與“減”之間,直接影響了患者的就診去向。一個月以來,西城區德勝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日均門診量已達到了900人次。
患者雖被“疏解”來,但社區醫院能否留得住,看得好?西城區德勝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韓琤琤對此很有信心。
她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3家“緊密型醫聯體”單位的支持:“我們現在與人民醫院、北大醫院和二龍路醫院,都成為緊密型醫聯體,將醫療機構的發展和利益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韓琤琤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這就好比兩家醫院,一個班子。”
為了扶助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生的成長,北京二龍路醫院黨委還作出規定,選拔出2名主任醫師,每月對德勝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100份電子處方進行點評,點評的質量由黨委直接考核,并與醫生的晉升、績效考核密切掛鉤。
軟約束變成了硬要求,“緊密型醫聯體”開始發揮應有的效能。
“今天來找高大夫,繼續開點藥。”作為“緊密型醫聯體”的一名受益者,50歲的施阿姨來到德勝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醫時,打開了“話匣子”。“年初,我就發現看東西老‘重影兒,去三甲醫院眼科排了老長的隊,不到3分鐘就讓出來了。”醫生診斷為老視,需要配老花鏡;但驗光師卻告訴她,眼睛肯定沒問題。幾經周折,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施阿姨最后來到了家附近的德勝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全科醫生高鳳娟仔細詢問了她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當得知施阿姨的父親是糖尿病患者時,立即對她進行空腹血糖檢查。結果大吃一驚,施阿姨是一個伴有嚴重并發癥的糖尿病患者。
高鳳娟立即聯系“緊密型醫聯體”單位——北京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知名內分泌專家董愛梅,董主任給予了明確治療方案。同時,高鳳娟又通過雙向轉診平臺,把施阿姨轉到北大醫院眼科,并做出了“考慮糖尿病神經病變”的指向性診斷。“第二天,我就拿著轉診單找到了北大醫院的眼科專家對癥治療,一個月就好了。”施阿姨說。
“緊密型醫聯體”的集中優勢資源,讓“施阿姨們”不僅得到了正確診治,更大大提高了就醫效率。高鳳娟坦言,自己也是獲益者:有了醫院黨委的制度約束,自己作為一名全科醫生,可以對接知名三甲醫院幾個優勢科室主任醫師的直接“點撥”,她感覺自己的業務水平在加速進步。通過搭建“緊密型醫聯體”,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診斷水平有了明顯提升,患者就真正“留”在了基層社區醫院。
西苑醫院知名心血管專家徐浩有了接診的新體會——“含金量”提高了:“現在每天就診量減少1/5,減少的都是拿藥的病人。候診的人少了,我能給病人講解得再細一點,等候的病人也能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