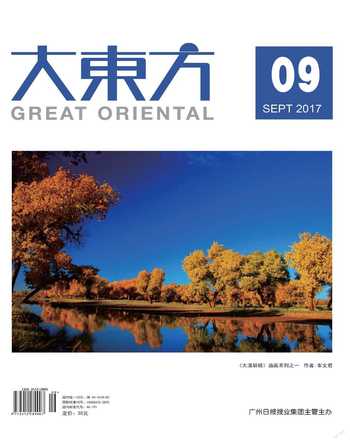淺談新聞敲詐的法律規制
黃毓智
摘要:新聞敲詐是指真假記者以媒體曝光威脅、要挾當事人,從而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實施新聞敲詐情節嚴重則構成犯罪:假記者實施新聞敲詐構成敲詐勒索罪;“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職業記者利用其職務便利進行新聞敲詐,應以受賄罪論處。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有償新聞”或“有償不聞”,不僅有損媒體的公信力,更嚴重踐踏了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精神和道德底線。對于新聞敲詐行為既要依法懲治,也要不斷完善新聞管理體制機制,從根本上防止其發生和蔓延。
關鍵詞:21世紀網敲詐案,新聞敲詐,法律規制,刑法
一、什么是新聞敲詐
(1)21世紀網敲詐案
2014年9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偵破一起特大新聞敲詐案件,涉案的21世紀網主編和相關管理、采編、經營人員及上海潤言、深圳鑫麒麟兩家公關公司負責人等8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涉及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的數十家企業。該網利用“買斷負面消息”,大搞有償新聞、有償不聞,甚至以輿論監督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據專案組初步核查,2010年至今,21世紀網平均每年與100多家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簽訂“廣告合同”,累計收取費用數億元。[1]
實際上,惡意利用IPO報道換取商業利益的做法,不只21世紀網一家在用。媒體以負面報道相要挾與上市公司尋求“合作”的模式,越來越多媒體爭相效仿、直接復制。上市公司、財經公關公司與財經媒體之間通過廣告合同等“合法”形式進行交易,掩蓋了其違法犯罪的事實,逾越新聞職業道德的基本底線,嚴重損害了財經媒體的公信力。
(2)“新聞敲詐”概念
所謂新聞敲詐,是傳媒或新聞從業人員以不利于報道對象的新聞稿件(包括編發內參等)相威脅,強行向被報道對象索要錢財或其他好處的行為。[2]出于個人私欲,一些道德觀念不強的記者利用手中的批評監督權利,被動收受“封口費”而“有償不聞”,或者尋找借口敲詐勒索利害關系人,索取不正當錢財。這種以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的行為,不但違背新聞職業道德,而且輕者違法,重則犯罪。
在行政規章、行業規范中同樣存在與新聞敲詐有關的規定,如《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第四條明確規定:堅決反對和抵制各種有償新聞和有償不聞行為,不利用職業之便謀取不正當利益,不以任何名義索取、接受采訪報道對象或利害關系人的財物或其他利益。[3]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冒充記者身份的“假記者”。這些假記者招搖撞騙,肆意敲詐,然而被敲詐者自身多有問題而不敢舉報,假記者“現形”被抓的情況往往出于偶然。行政規章、行業規范明顯無法對他們予以制裁,只有以法律為依據,予以刑罰,才能有效遏制此類現象。
(3)新聞敲詐的危害
①引發公眾質疑,媒體公信力下降
21世紀網新聞敲詐案的發生,其后果不僅僅是對本身造成了負面影響,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惡性的連鎖反應:由事件本身波及了整個新聞界,受眾由此對整個新聞行業產生了信任危機。可以預見,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公信力一旦受損,將不利于行業的長遠發展。況且近年來如2002年山西繁峙礦難“封口費事件”等一些案件已嚴重敗壞了媒體的信譽。
②使原本經營困難的傳統媒體“雪上加霜”
媒體的社會認可度和信任度直接關系著發行量和視聽率,進而影響廣告收益。當“社會公器”成為利益工具,還有多少媒體和新聞值得信賴?如果照這樣惡性循環下去,勢必會使本就盈利困難的傳統媒體“雪上加霜”。21世紀網與21世紀報系緊密相關,但新聞敲詐事件造成公信力的下降,此前其紙媒的一些忠實讀者可能不會再忠誠于它,原本被視為21世紀報系轉型希望之一的21世紀網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③對新聞人才隊伍的建設產生不良示范效應
“新聞敲詐”的敗露說明一部分新聞從業者存在職業素養低、法制觀念淡薄,往往對《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口頭上喊得熱烈,心里卻以一種不屑的姿態對待。長此以往,勢必降低新聞從業者的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道德水準,進而影響到整個新聞人才隊伍的梯隊建設。
二、新聞敲詐與其法律規制
(1)“敲詐”與“受賄”及其區分
我國現行《刑法》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從該條規定可知,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有三項:
①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②行為人實施了以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勒索財物的行為;
③敲詐勒索的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實施敲詐。
如果是一般社會人員冒充記者對利害關系人進行敲詐,這種行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威脅或者要挾對方就范而強行索取公私財物,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應以敲詐勒索罪論處。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利用或者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軍人、新聞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詐勒索”,按敲詐金額不同,可以分別認定為《刑法》第274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可以看出在我國的法律規定中,對于假記者實施新聞敲詐構成敲詐勒索罪是沒有異議的。而職業記者的新聞敲詐行為屬于何種犯罪,檢察機關、法院的認識并不一致,甚至出現過犯罪行為類似而定罪不同的情況。
2007年9月20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對涉嫌敲詐勒索國內某知名電視購物公司的原某財經報記者X以及作為事件“中間人”的某廣告公司的M進行宣判,兩被告犯敲詐勒索罪,各判處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此案兩被告M和X為報社同事,案發時X系某財經報社的記者,M系某廣告公司職員。2006年7月,被告X在某報上對某公司進行了負面且有部分虛假內容的報到。該公司企劃部總經理經朋友介紹聯系上被告M,M向其表示只要花錢就能解決問題。M與X聯系后決定由M出面敲詐該公司錢財,以X還將繼續進行負面報道相要挾,向該公司索要人民幣40萬元。該廣告公司在雙方交涉期間已向公安機關報案,同年7月底,雙方最后一次交易時,兩被告被當場抓獲。[4]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最終定性“敲詐勒索罪”,而在另一類似案件中,法院定性卻存在較大爭議。2006年9月,某報原浙江記者站站長、新聞中心主任MH利用其記者身份,以發表批評報道、曝光相要挾等手段向多家企業索要數額不等的錢款,被杭州市上城區檢察院以受賄罪和強迫交易罪提起公訴。杭州市上城區法院認為MH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一審判決后,公訴機關以一審判決定性不當、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提出抗訴。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被告MH身為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依照《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因此,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二年。[5]
到底是敲詐勒索還是受賄,同樣的犯罪事實,適用不同的罪名,刑期長短可能差別很大。2013年以來判決的幾起典型新聞敲詐案件,不同地方法院對涉案記者的定罪也不一樣:《今日早報》記者金侃群、《都市快報》記者朱衛、《杭州日報》記者楊劍被定為受賄罪,《西部時報》記者馬玉華和田華、《證券時報》記者羅平華則被定為敲詐勒索罪。[《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8起典型新聞敲詐案件》,新華網2014年3月31日,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31/c_126336305.htm。]
敲詐勒索和索賄行為都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但是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犯罪,在我國《刑法》中,敲詐勒索罪的類罪名為“侵犯財產罪”,受賄罪的類罪名則是“貪污賄賂罪”。兩者的區別主要有三個方面:
①犯罪主體不同。受賄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為特殊主體。我國《刑法》第385 條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敲詐勒索罪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即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就可以構成。
②犯罪手段不同。 受賄罪是利用職務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敲詐勒索罪是以威脅、要挾等手段強行索取他人財物。行為人是否利用職務便利是二罪的本質區別。
③侵害的客體不同。 受賄罪侵害的客體主要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敲詐勒索罪侵害的客體則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
那么,職業記者實施新聞敲詐構成犯罪,究竟屬于“敲詐勒索罪”還是“受賄罪”?
這首先要看職業記者是否符合受賄罪的犯罪主體資格。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受賄罪的犯罪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即“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不過第9條又規定: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我國的新聞單位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機關,但考慮到我國黨政管辦媒體這一獨特的新聞體制,職業記者肯應該“以國家工作人員論”,也符合受賄罪的犯罪主體資格。
其次,職業記者進行新聞敲詐,當然是利用了采訪報道新聞的職務便利,即使不存在為他人謀取利益之情事,也照樣構成受賄罪。因為通過新聞敲詐的方式索取公私財物,屬于索賄型受賄,而“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是索賄型受賄罪成立的必備條件。
第三,職業記者進行新聞敲詐,侵害的是我國新聞傳播的正常秩序和新聞媒體的公信力,比一般的敲詐勒索行為情節更為嚴重,社會危害性更大。按照刑法“想象競合犯”理論,對此科以更重的“受賄罪”而不是“敲詐勒索罪”,也是加大對這種犯罪行為的懲治力度。因此,持有記者證的職業記者,不管是新聞單位在編記者或是正式聘用的非在編記者,只要實施新聞敲詐構成犯罪,一般應以受賄罪論處。
至于新聞單位臨時雇傭的沒有記者證的工作人員進行新聞敲詐構成犯罪,可以按《刑法》第163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量刑。2008年10月發生的真假記者在山西霍寶干河煤礦排隊領“封口費”事件,涉案的《中國鄉鎮企業》雜志社工作人員張向東等就被法院判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而假冒《法制日報》記者的劉小兵則被判為敲詐勒索罪。
(2)職業道德與法律法規,自律與他律
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法規同時調整新聞傳播活動的重要途徑,考慮新聞敲詐的法律規制時,同樣不能忽視職業道德在該問題上的重要影響力。新聞傳播業之所以成為一種職業并為社會所尊崇,是因為該行業根據職業特性約定俗成地形成、制定了一套道德原則,作為行業成員規范自己職業行為的準繩。《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的第一條,要求我們的新聞從業者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可以說,獻身公共利益,是全球新聞傳播業的至高道德準則,聯合國新聞自由小組委員會1954年通過的《國際新聞道德信條》(草案)即規定:“職業行為的崇高標準,是要求獻身于公共利益。謀求個人便利及爭取任何有違大眾福利的私利,不論所持何種理由,均與這種職業行為不相符合。”
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在整治“新聞敲詐”中必不可少。畢竟,新聞自律較之他律,效率較高而成本較低。近年來,新聞敲詐案件頻發,對其的處理消耗了大量的司法及執法資源。然而,如果媒體從業者在工作中嚴格自律,遵循職業道德規范,這種情況本能避免。另一方面,職業道德水準的提升,對于法律法規得到尊重和維護,也有著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三、結語
本文在法律風險上注重分析了新聞敲詐刑法罪名的構成,其實,新聞敲詐的法律責任不僅僅包括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同樣是新聞敲詐必須承擔的。在民事責任方面,新聞敲詐可能導致民事侵權行為的發生,侵犯當事人隱私權、名譽權等。隨著新聞行業協會的監督管理功能增強,行政責任的承擔也將更加得到落實。我們需要認識到,新聞敲詐事件的有效整治并非刑罰打擊獨立就可實現的工程,而需要堅持多樣整治措施并舉。
新聞敲詐是媒介權力異化的結果,權力異化來自多重因素:權力本身的腐蝕性,監督機制的缺失或“漏監”,“空監”地帶的存在以及監督規范的滯后等等。凡此種種,均有可能生成所謂的灰色地帶,使身在其中的媒體人和管理者從喪失警覺、模糊身份、淡化法制觀念開始,到渾水摸魚、濫用權力,及至以身試法,欲罷不能。深刻剖析21世紀報系新聞操作失范的成因及后果,探尋相應的防范舉措,吸取其慘痛的教訓,有助于新聞工作者更加自覺地堅守職業道德倫理、嚴守法律底線,使我國媒體更加健康、有序地發展。
參考文獻:
[1]許一力. 21世紀網敲詐案暴露財經公關潛規則[J]. IT時代周刊, 2014 (18).
[2]鄧濤, 肖峰. 新聞法學視閾下的“新聞敲詐”[J]. 現代視聽, 2013, (7).
[3]陳建云. 新聞敲詐,該當何罪?[J]. 新聞記者, 2014, (7).
[4]陳春彥. 從“封口費”說起:談媒體傳播法律風險規避與采編技巧[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2009.
[5]張立. 打擊新聞敲詐是為實現自我凈化——“新聞敲詐的法律責任”研討會綜述[J]. 青年記者, 2014, (34).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