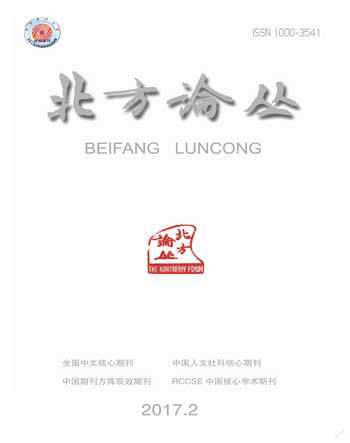二十世紀“龍學”的經典之作
戚良德
[摘要]詹锳先生是20世紀“龍學”史上的大家,他以《文心雕龍義證》一書集成了《文心雕龍》的校注成果,不僅成為大陸第一個《文心雕龍》的會注集成本,而且至今亦無出其右者。這部皇皇巨著廣征博引,嚴謹細密,以集解匯注的形式探求《文心雕龍》的本義,以證得對《文心雕龍》原文的確解,從而完成了一部既有會注與集成之功,又具個人理論色彩的“龍學”巨著,成為中國大陸20世紀“龍學”的標志性成果之一,亦成為百年“龍學”史上的經典之作。
[關鍵詞]詹锳;龍學;《文心雕龍義證》
[中圖分類號]I206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7)02-0044-06
Abstract: Zhan Ying, a master in the history of 20th-century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epitomizedfruitful recensionsand commentariesin his book, Wenxin Diaolong Yizheng, which wa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corpus of Wenxin Diaolongs commentaries. This magnum opus quoted copiously from many sources and developed rigorous logic to explore the true nature and exact understanding of Wenxin Diaolong by gathering various commentaries, thusmaking a great book on Wenxin Diaolong with not only gathered commentaries but alsounique personal theory. It is a landmark in 20th-century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and even a classic work in the one hundred yearshistory of Wenxin Diaolong study.
Key words:Zhan Ying;study of Wenxin Diaolong;Wenxin Diaolong Yizheng
《文心雕龍》是一部只有三萬七千多字的書,但研究它的專著中,卻不乏大部頭的作品。在20世紀的“龍學”史上,有兩部規模較大的著作,一是我國臺灣地區李曰剛先生《文心雕龍斠詮》(1982年),180余萬字;二是詹锳先生《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34萬余字。這兩部著作分別成為海峽兩岸二十世紀“龍學”的標志性成果之一。尤其是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證》一書,被收入影響極大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之中,一直被作為“龍學”和中國古典文論的重要參考書目,可以說已成為具有集成性的“龍學”經典。這部皇皇巨著廣征博引,嚴謹細密,做到了“把《文心雕龍》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處和典故,都詳細研究,以探索其中句義的來源”[1](p.3)。正如詹福瑞先生所說:“這部書,既反映了詹先生幾十年研究《文心雕龍》的創獲,又可以看出自古及今歷代研究《文心雕龍》的成果,是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之后,又一部全面而謹嚴的證義為主,兼有匯注、集解性質的本子。”[2](p.126)
一、版本與匯校
《文心雕龍義證》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其集成性,并首先表現在版本搜羅和匯校之功上。翻開《文心雕龍義證》,開篇的《序例》之后緊接著就是《〈文心雕龍〉版本敘錄》。詹先生說:“《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最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可是由于古本失傳,需要我們對現存的各種版本進行細致的校勘和研究,糾正其中的許多錯簡,才能使我們對《文心雕龍》中講的問題,得到比較正確的理解。”[1](p.9)正是這種強烈的版本意識,促使詹先生多年來跑遍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濟南等地,搜羅《文心雕龍》的各種版本,從而為《文心雕龍義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詹先生之前,于版本校勘方面用力頗深、成果顯著的學者主要是王利器和楊明照兩位先生,其代表作分別是《文心雕龍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和《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詹先生于“楊王二家所校各本”“大都進行復核,寫成《文心雕龍版本敘錄》”[1](p.4),顯然具有集成、補正之功。詹先生所錄從最早的刻本即元至正本到近代發現的敦煌殘卷中的唐寫本,共32種。他對這32種《文心雕龍》的不同版本都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他還特別強調“眼見為實”,所錄入的版本除了乾隆四年(1739年)刊李安民批點本《文心雕龍》和顧千里、黃丕烈合校本《文心雕龍》未見外,其它版本皆為自己親眼所見。詹先生著重介紹的版本主要有:元至正本,明徐火勃校汪一元私淑軒刻本,明曹學佺批梅慶生第六次校訂本,明謝恒抄、馮舒校本。在王利器和楊明照先生的著述中,這幾個版本或信息不夠詳細,或付之闕如。
也正是有此強大的版本學基礎,《文心雕龍義證》一書基本網羅了眾家的校勘成果。比對各家所校異同,指出其中校勘錯誤,提出修訂意見和說明,詹先生盡展自己的匯校之功。如《文心雕龍·宗經》篇有“義既挻乎性情”一句,其中“挻”字,各種版本不一,歷來注家亦爭論不斷,詹先生引用了多家校勘成果予以對比說明:
《校證》:“‘挻原作‘極。唐寫本及銅活字本《御覽》作‘挺,宋本《御覽》、明鈔本《御覽》作‘埏。按‘挺‘ 埏俱‘挻形近之誤,《老子》十一章:‘挻埴以為器。‘挻與‘匠義正相比,今改。”橋川時雄:“極字不通。挺、極形似之誤。挻字始然反。《老子》:‘埏埴以為器。《釋文》引《聲類》云:‘柔也。河上公注云:‘和也。”斯波六郎同意趙萬里《校記》之說,謂應作“埏”,是“作陶器的模型”。又說:“此字又可作動詞用,如《老子》第十一章‘埏埴以為器,《荀子·性惡》篇‘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齊策》三‘埏子以為人等。”潘重規《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埏蓋‘挻之偽。《說文》:‘挻,長也。《字林》同。《聲類》云:‘柔也。(據《釋文》引)《老子》:‘挻埴以為器。字或誤作‘埏。朱駿聲曰:‘柔,今字作揉,猶煣也。凡柔和之物,引之使長,搏之使短,可析可合,可方可圓,謂之挻。陶人為坯,其一端也。”[1](p.61)
一字之校,詹先生慎重引用了王利器、橋川時雄、斯波六郎、趙萬里、潘重規等五家校語,最后才按曰:“‘挻通‘埏,此處猶言陶冶。”[1](p.62)于此,不論我們是否同意詹先生的結論,對這個字的來龍去脈總是了然于心了。
詹先生不僅充分羅列并運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而且進一步補證前人。如《才略》篇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庾筆奏,世執剛中;并楨干之實才”等句,其中“楨干”二字頗有異文。詹先生先引述《文心雕龍校證》:“‘楨,馮本、汪本、兩京本、王惟儉本、《詩紀》《六朝詩乘》作‘杶。”再引《文心雕龍校注》:“‘楨,黃校云:‘汪作杶。按元本、弘治本、活字本、張本、兩京本、胡本、訓故本、四庫本亦并作‘杶;《詩紀別集》引同。皆非也。《程器》篇贊:‘貞干誰則?‘貞為‘楨之借字,可證。”然后舉出兩條新的佐證:“《書·費誓》:‘峙乃楨榦。‘榦亦作‘干。‘楨干,支柱,骨干。亦作貞干。《論衡·語增》:‘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干也。”[1](p.1818)顯然,詹先生補充的兩條證據極有說服力,不僅佐證了楊先生所謂“并作‘杶……皆非也”的結論,而且進一步證明無論作“楨干”還是“貞干”,皆有所據,則連“借字”之說亦可不必了。
補證之不足,詹先生還會對先賢的校勘意見予以商兌或指正,例如,《神思》篇有“物以貌求,心以理應”之句,對于這個“應”字,其校曰:
“應”字,元刻本、弘治本、佘本、王惟儉本、兩京遺編本均作“勝”,那樣和末句“垂帷制勝”的“勝”字重復。張之象本、梅本并作“應”,今從之。這兩句說:所求于事物的是它的外部形象,而內心通過理性思維形成感應。《校注》《校證》均謂“應”字當作“勝”,解說迂曲,今所不取。[1](p.1008)
可以說,詹先生的選擇是較為合理的,多數《文心雕龍》研究者也早已認可《神思》篇的這兩句名言。不過這里有一個小問題,《文心雕龍義證》的讀者多未細察,我們既然說到了,當為詹先生一辯。查楊明照先生《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其明確表示各本“并作‘勝,與下‘垂帷制勝句復,非是”,而認為:“文津本剜改為‘媵,是也。爾雅釋言:‘媵,送也。‘心以理媵,與上句‘物以貌求,文正相應。‘媵與‘勝形近,易誤。章句篇‘追媵前句之旨,元本等亦誤‘媵為‘勝,與此同。附會篇:‘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是舍人屢用‘媵字也。”[3](p.234)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龍校證》亦云:“案‘勝疑‘媵誤,《章句》篇:‘追媵前句之旨。‘媵即原誤作‘勝。《附會》篇:‘媵句憔悴。”[4](p.190)
顯然楊、王二位先生均以“勝”為“媵”字之誤,則詹先生所謂:“《校注》《校證》均謂‘應字當作‘勝,解說迂曲”云云,似乎是誤解了兩位先生,但以詹先生之嚴謹,這樣低級的錯誤自不應有,則其必事出有因。細思之下,筆者覺得上述詹先生所言,原本應是“《校注》《校證》均謂‘應字當作‘媵”,這才是楊、王二書的實際,詹先生不會不察;只是《文心雕龍義證》一書乃繁體字版,排版過程中把詹先生原稿的“媵”字誤為繁體的“勝”字,后未能校出而已。詹先生所謂“解說迂曲,今所不取”者,所指正是楊、王二位先生論證“應”當為“媵”之語。若果真如此,這可真是一個小小的歷史玩笑,楊、王二位先生均力證《文心雕龍》各版本誤“媵”為“勝”,但詹先生不以為然,而其《文心雕龍義證》卻正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自然,詹先生于此可能一直未有察覺作為“龍學”經典著作,《文心雕龍義證》一書多有重印,筆者所見1989年初版本和1994年初版二印本的《神思》校語,均誤“媵”為“勝”,希望出版社再印時改正這一關鍵性的小錯誤。,更不意味著這就足以證明楊、王二位先生所謂“應”當為“媵”之說。但這不經意的一字之錯,可能傷及三位“龍學”大家,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版本的校勘實在是《文心雕龍》乃至古代文化研究的根本和基礎,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者,斯其謂乎?
二、會注與集解
《文心雕龍義證》一書的主體部分無疑是對《文心雕龍》文本的會注和集解。詹先生明確指出:
本書帶有會注性質。《文心雕龍》最早的宋辛處信注已經失傳。王應麟《玉海》《困學紀聞》中所引《文心雕龍》原文附有注解。雖然這些注解非常簡略,本書也予以引錄,以征見宋人舊注的面貌。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大多采錄明梅慶生《文心雕龍音注》(簡稱“梅注”)、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簡稱“訓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較難得,王惟儉《訓故》尤為罕見。茲為保存舊注,凡是梅本和《訓故》征引無誤的注解,大都照錄明人舊注,只有黃本新加的注才稱“黃注”。[1](p.5)
可見,詹先生的“會注”,首先是匯集宋明以來至清代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舊注成果。這些成果從數量上看并不算多,但卻代表了數百年《文心雕龍》研究的成就。詹先生以此為基礎,顯然是非常正確的。他又說:“全書以論證原著本義為主,也具有集解的性質,意在兼采眾家之長,而不是突出個人的一得之見,使讀者手此一編,可以看出歷代對《文心雕龍》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當代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有哪些創獲。”[1](p.7)如此明確的思路和目標,使得詹先生的《文心雕龍義證》成為大陸第一個《文心雕龍》的會注集成本,至今亦無出其右者。
既為“會注”,當然是要匯聚各家的成果,但卻并非簡單地羅列在一起,而是仍然面臨一個選擇的問題。而選擇不僅要具備犀利獨到的眼光,更要有盡可能廣泛的范圍,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聞見廣博。因此,真正做好古籍的會注集成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對“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而言,其難度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比興》開篇有云:“《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1](p.1333)其中“風通而賦同”一語,向為理解的難點,其“會注”就顯得格外必要了。正因如此,詹锳先生不惜筆墨,對這五個字進行徹底索解[1](pp.1335-1336)。劉勰的五個字,詹先生用了一千余字來注解,規模不可謂不大,但從其引錄可見,涉及“龍學”八家成果而已,真要做到囊括無遺,篇幅肯定還要成倍擴大,但那顯然是不可取的。這里便見出了詹先生的“會注”之功。他特地分段標注,正顯其用心所在。第一段是王利器、黃侃、范文瀾和楊明照四家之說,“龍學”大家的校注成果我們看到了;第二段是李曰剛之說,代表我國臺灣地區“龍學”的基本觀點;第三段和第四段都是郭紹虞先生的見解,卻不是有關《文心雕龍》的注釋,而是來自郭先生的兩篇文章,這便充分顯示出詹先生獨特的眼光和取材;第五段和第六段是郭晉稀和牟世金先生的見解,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大陸最有影響的“龍學”觀點。如此,我們不能不說,詹先生的“會注”決非不加選擇的簡單羅列,而是頗為用心的集其大成。
其實,上述這種“會注”固然見出功力,選擇固然需要眼光和視野,但還不能完全代表“集解”之功。在筆者看來,上述“會注”還只是匯合別人的見解,盡管這種匯合有著充分的取舍,體現了選擇者一定的學養,但其中所“會”,畢竟都與所“注”的內容密切相關,因而范圍畢竟還是有限的。而真正的“集解”,固然首先要集中別人的見解,但更要在此基礎上,提出集解者自己的意見,至少也要顯示某種傾向性,則集中哪些見解,其選擇性就主觀得多了,其范圍也就大得多了,從而對集解者的學術水平也就要求更高了。如《原道》開篇有云:“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1](p.2)其中“文之為德也大矣”一句,歷來為解釋重點和難點,各家說法不一,但詹先生卻沒有采用“會注”的方式,沒有引用任何一家對這句話的注釋,而是引用了《論語》《中庸》《四書集注》《周易正義》等語來進行釋義,其云:
《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朱注:“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此處句法略同,而德字取義有別。《易·乾·文言》正義引莊氏曰:“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德即宋儒“體用”之謂,“文之為德”,即文之體與用,用今日的話說,就是文之功能、意義。重在“文”而不重在“德”。由于“文”之體與用大可以配天地,所以連接下文“與天地并生”。[1](p.2)
顯然,這些引文都不是對《原道》開篇這句話的直接注釋,是否引證,引證哪些,完全取決于注釋者的判斷和選擇,而這又都成為其對劉勰原文進行闡釋的基礎和根據。這里便更充分地體現出詹先生的學養和功力了。之所以要引用《論語》和《中庸》的話,是因為劉勰的句式與它們相同,但詹先生隨后指出:“而德字取義有別”,至于何處“有別”,則再引《周易正義》之語,然后作出判斷;這一判斷雖以之為據,但重在解釋劉勰,因而有很大的跳躍和跨度,不僅解釋了什么是“文之為德”,而且還對下文“與天地并生”的邏輯予以點出。如此“集解”,既體現了“無征不信”的原則,又充分表現了詹先生對《文心雕龍》的理解,因而使得《文心雕龍義證》一書不只是簡單的“會注”之作,而是成為“以論證原著本義為主”的理論著述。
在廣泛征引各種元典和經典解釋《文心雕龍》的同時,詹先生還充分利用劉勰自己的說法證明劉勰,所謂“參照本書各篇,展轉互證”[1](p.3),也就是利用可靠的“內證”,對《文心雕龍》進行闡釋。如《章表》篇“贊曰”有“肅恭節文”一語,詹先生就利用《文心雕龍》中的多篇來進行互證:
《樂府》篇:“辭繁難節。”《誄碑》篇:“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書記》:“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镕裁》篇:“然后舒華布實,獻替節文。”《附會》篇:“夫能縣識湊理,然后節文自會。”《斟詮》:“節文,謂禮節文飾也。《禮記·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管子·心術上》:‘禮者因人之情,像義之理,而為節文者也。”[1](p.850)
這樣的互證,有些可能一望而知,有些則出于研究者自己的判斷,完全取決于對《文心雕龍》一書的整體把握和融會貫通程度。在計算機和信息技術普及的今天,我們或許覺得這不算難事,但在詹锳先生作《文心雕龍義證》的時候,能夠如此信手拈來,沒有遺漏,卻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當然,這段注釋還不僅僅是“互證”,而是在集中了劉勰的相關說法之后,又引用了李曰剛先生的注釋,予以進一步的說明。這里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詹先生除了引錄,沒有多余的話,那表示他同意李先生的概括,即“節文,謂禮節文飾也”,可見《文心雕龍義證》雖皇皇巨著,長逾130萬言,但詹先生仍是惜墨如金的。二是李先生的注釋主要是引經據典,詹先生予以全部引錄,這既是以經典證劉勰,又不埋沒李先生發掘之功。這樣的集解方式,詹先生在該書中多有運用,其良苦用心,我們不得不察;其良好學風,值得我們學習。其《序例》有云:“當代著述,筆者認為可資發明《文心》含義者,多徑錄原文,注明出處。各家所引古書資料,本書注明轉引。有時筆者原稿已有引文,而他人已先我發表,也說明已見某書,以免‘干沒之嫌。”[1](p.6)這正是“雖杼軸于予懷,怵佗人之我先。茍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5](p.145),其謙謙儒風,令人景仰。
作為一部會注和集解之作,取材廣博是自不待言的。根據詹锳先生所列“主要引用書目”,《文心雕龍義證》一書參考到的經傳子史和漢晉以來的文論約70種,具體到每一篇的校注集解,自然還有大量沒有列入這個書目的書籍或篇目。至于為研究者們所習見的資料,該書更是詳加搜羅,片善不遺。由“主要引用書目”可知,詹先生共參考了中外現當代“龍學”著述九十多部,相關著述二十多部,甚至還有一些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尤可稱道者,詹先生不僅大量參考了近代的各種資料,而且有些資料極為難得,像聽課筆記,詹先生亦注意搜羅,甚至還對某些信息缺失的筆記進行考訂而加以利用。如《文心雕龍義證》之“引用書名簡稱”的最后一條是“朱逷先等筆記”,詹先生說:“朱逷先、沈兼士等聽講《文心雕龍》筆記原稿,只有前十八篇。朱、沈皆章太炎弟子,疑為章太炎所講。”[1](p.38)詹先生多處引用了這個“疑似”的課堂筆記。此懸案后經周興陸先生采用紙張鑒別的手段,證實了詹先生猜測的正確性[6]。作為首位大膽提出此朱、沈二人《文心雕龍》課堂筆記乃章太炎在日本“國會講演會”之演講記錄的學者,詹先生對“龍學”史和章氏文學理論的研究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此外,對于20世紀80年代的《文心雕龍》研究來說,我國大陸之外的“龍學”成果并不如今日這般容易檢索和得到。《文心雕龍義證》的集大成還表現在它不僅匯集了常見的我國大陸學者的成果,而且搜羅了許多我國臺灣地區、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海外學者的成果。我國臺灣地區的潘重規、李曰剛、張立齋、王金凌、黃春貴等人的觀點,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饒宗頤、石壘等人的主張,以及日本的戶田浩曉、興膳宏、目加田誠、斯波六郎等人的見解,我們都可見到,甚至在“主要引用書目”中還列舉有“匈牙利英文書目”,這在當時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三、釋義與評說
《文心雕龍義證》給人的突出印象是其集成性,但卻決非一部資料性的工具書,而是具有重要的個人見解和理論色彩的專著。盡管詹先生說這部書“具有集解的性質,意在兼采眾家之長,而不是突出個人的一得之見”,但它又是“以論證原著本義為主”[1](p.7)的一部著作,因而與一般的會注集解之作是頗為不同的。對此,詹福瑞先生曾經明確指出過。他說:“這部書雖有集解性質,然其主旨則是論證原著的本義。故書中對《文心雕龍》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處和典故,都詳細研究,悉心探索其中句義的來源,以求得對本義的正確理解。”[7](p.310)筆者以為,福瑞先生的這一說法是深得詹锳先生之“用心”的。
從著述形式上說,《文心雕龍義證》當然是一部以校勘與注釋為基礎的著作,但《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思精”的理論之作。詹先生既以“義證”為目的,則最終能否得“證”其“義”,僅僅靠網羅眾家之見,顯然是難以完成的。實際上,我們上面已經看到,從“會注”到“集解”,詹先生在一步步完成“義證”的目標,這是明確而堅定的。《文心雕龍·論說》有云:“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1](p.701)劉勰認為,注釋類的文字,可以看成是分散之論;其雖摻雜于文中而與論文有別,但匯總起來仍是完整之論。可以說,《文心雕龍義證》一書正是很好地實踐了劉勰的主張。這當然得益于詹先生自身良好的理論素養及其對《文心雕龍》的精心研究。其以《劉勰與〈文心雕龍〉》《〈文心雕龍〉的風格學》等理論專著作基礎,《文心雕龍義證》對劉勰文論思想的闡釋,雖然字數不多且分散為論,卻往往具有點睛的性質,與前兩部著作可謂異曲同工。
如所周知,詹先生建構了《文心雕龍》的風格學理論體系,他甚至將整部《文心雕龍》都看作是風格學的論著,《文心雕龍義證》一書也明顯貫穿了這一觀點。在《序例》中,詹先生就指出:“筆者希望能比較實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龍》原書的本來面目,發現其中有哪些理論是古今中外很少觸及的東西;例如劉勰的風格學,就是具有民族特點的文藝理論,對于促進文學創作的百花齊放,克服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會起一定的作用。這樣來研究《文心雕龍》,可以幫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以指導今日的寫作和文學創作,并作為當代文學評論的借鑒。”[1](pp.7-8)正因如此,在很多篇目中,詹先生都會把自己的風格學思想熔入其中進行解說。除此之外,無論《文心雕龍》的創作論、批評論、修辭學以及文學史論等,詹先生都在引經據典的同時,不忘對其進行理論的闡發或評點,自然也常有遠見卓識。如《神思》篇“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二句,詹先生一句注曰:“這句照唐宋散文的寫法是‘思理之為妙也,意指‘形象構思的妙處是。”另一句注曰:“即物我交融,也就是人的精神和外物互相滲透。”[1](p.977)這種著眼文論的釋義不但是明顯可見的,而且順便指出以駢體論文的《文心雕龍》與唐代散文之句法的不同,其點睛之妙,可謂無愧“雕龍”之稱。又如該篇“窺意象而運斤”句,詹先生注曰:“‘意象,謂意想中之形象……在西方心理學中,意象指所知覺的事物在腦中所印的影子;例如看見一匹馬,腦中就有一個馬的形象,這就是馬的意象。其所以譯為‘意象,是因為和王弼的解釋類似……這句是說:有獨到見地的作者,能夠根據心意中的形象來抒寫。”[1](pp.983-984)這里的注釋不僅同樣從文論的角度入手,既著重闡釋“意象”一詞,又不忘整句話的意蘊,而且詹先生充分發揮熟悉心理學之長,把古今中外熔為一爐,把自然與人文予以貫通,亦可謂“深得文理”了。
當然,作為一部“會注”和“集解”之作,詹锳先生既然明確宣稱“無征不信”,則其理論闡釋亦自然不會架空立說,而是充分引證各種資料,從大量相關的論說中提煉自己的觀點,陳說自己的看法。我們以《風骨》篇的“題解”為例,來看一下詹先生是如何把大量的資料與自己的陳說相結合的。僅晉代至中唐時期有關“風骨”的資料,詹先生便列舉了《世說·賞譽》篇、《世說·容止》篇、《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宋書·武帝紀》《南史·宋武帝紀》《南史·蔡樽傳》《北史·梁彥光傳》《新唐書·趙彥昭傳》、高適《答侯少府》、謝赫《古畫品錄》、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后畫錄》、齊王僧虔《能書錄》《法書要錄》、梁武帝《書評》、梁袁昂《書評》、唐李嗣真《書品后》、唐張懷瓘《書議》及《書斷》、唐竇泉《述書賦》《魏書·祖瑩傳》、楊炯《王勃集序》、盧照鄰《南陽公集序》、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盧藏用《陳氏別傳》《大唐新語》、殷璠《河岳英靈集序》,以及《河岳英靈集》劉昚虛小序、陶翰小序、高適小序、岑參小序、崔顥小序、薛據小序、王昌齡小序,乃至日本近藤元粹輯評本《王孟詩集》詩話部分等。而對于近人和當代學者的成果,詹先生先后引用了梅慶生引楊慎之注解、曹學佺之批語、馬茂元《論風骨》、寇效信《論風骨》、劉禹昌《文心雕龍選譯·風骨》、劉大杰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關于“風骨”的論述以及錢鐘書《管錐編》、宗白華《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等論著中的有關論述。可以看出,關于“風骨”的資料,尤其是劉勰時代前后的資料,近乎一網打盡了;在20個世紀80年代,能做到如此琳瑯滿目而洋洋大觀,僅翻檢之勞亦是可想而知的。
面對如此豐富的資料,詹先生又是如何評說的呢?在引證謝赫《古畫品錄》之“六法”后,詹先生說:“氣韻生動是其它各種要素的復合。創作能達到氣韻生動的首要條件是筆致。骨法用筆就是筆致,就是所謂骨鯁有力。”[1](pp.1041-1042)短短的幾句話,由“氣韻生動”而到“骨鯁有力”,也就很自然地把畫論引入了文論,把《古畫品錄》與《風骨》篇聯系在了一起。在列舉了中唐以前的相關資料后,詹先生總結說:“從上引資料,可以看出‘風骨一詞在人物品評,畫論、書評以及詩文評論中都是經常出現,而且它的含義是一致的。”[1](p.1045)這一總結與對“氣韻生動”的解說遙相呼應,進一步說明不僅繪畫與文章的“風骨”是一致的,而且與人物品評、書法也是一致的,從而六朝乃至唐代的“風骨”論就是一脈相承的了。如此,劉勰的“風骨”論便有了廣闊的文學藝術理論背景,而劉勰之后的“風骨”論也不再是無源之水,則《風骨》篇這一空前的美學范疇專論在中國美學史上的意義,也就不言而自明了。與資料引證之繁富相比,詹先生的幾句評說可謂簡潔之至,但又不能不說,其視野開闊而要言不煩,對理解眾說紛紜的“風骨”論具有重要的幫助。至于在引證曹學佺對《風骨》篇的批語后,詹先生說:“曹學佺的意思是說,氣屬于風的一個方面,而在‘風骨二者之中,風又居于主導的方面。黃叔琳在《風骨》篇論氣的一段加頂批說:‘氣即風骨之本。紀昀又反駁黃氏評語說:‘氣即風骨,更無本末,此評未是。這樣一來,反而把問題弄混了。”[1](p.1046)這是引證之后的評說,評說之中復有引證,看上去有些纏夾,但這里詹先生之所以不惜筆墨,蓋以涉及有關《風骨》篇的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風骨”和“氣”是什么關系?由此可見,《文心雕龍》的“會注”和“集解”,若非對“龍學”的歷史和現實了如指掌,是難以做到有的放矢的,而進一步的釋義和評說,也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綜上所述,《文心雕龍義證》是一部既有會注與集成之功,又具個人理論色彩的質地優良之作;在20世紀“龍學”史上,是不可多得的。
[參考文獻]
[1]詹锳.文心雕龍義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詹福瑞.詹锳先生的治學道路與學術風格[J].陰山學刊,1992(3)
[3]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張少康.文賦集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6]周興陸.章太炎講演《文心雕龍》[N].中華讀書報,2003-01-22.
[7]詹福瑞.學者簡介·詹锳[C]//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
(作者系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責任編輯連秀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