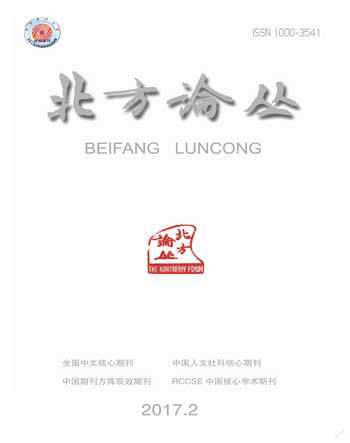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早中期家庭意識形態探析
傅燕暉
[摘要]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早中期(1837—1870年)的家庭意識形態話語是規范與約束當時女性尤其是中產階級女性行為的主導力量,亦深刻影響了這一時期乃至后世的文學作品對女性形象的再現。追本溯源,此意識形態與19世紀初英國中產階級的形成與崛起息息相關,構建了中產階級的“家庭理想”與中產階級女性的“家庭天使”意象,是中產階級對嚴肅道德生活追求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此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日后又將為英國中產階級女性所用,推動著她們積極改變自身命運。
[關鍵詞]維多利亞時代;家庭意識形態;“家庭天使”;中產階級
[中圖分類號]K5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7)02-0102-08
Abstract: Victorian domestic ideology is the omniscient ideology that regulates women, especially middle-class womens behavior. And it has a profound effect up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nd modern literary works. Encompassing both the domestic ideal and “the Angel in the House” ideal, this ideology comes into being almost concomitantly with the formation of middle-class in Victorian England and becomes part of Victorian middle-classs serious pursuit of a moral life. Yet the discordance between the ideology and societal realities eventually compels Victorian middle-class women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ake changes in the 1860s.
Key words:Victorian domestic;family ideology;“the Angel in the House”;middle-class
維多利亞時代早中期(1837—1870年)的英國,“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家庭理想”(the domestic ideal)話語興盛至極,這在當時為女性所做的行為指南書或文學作品等清晰可見,其強勢的影響甚至延續到了20世紀初。也因此,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指出,她的女性同胞們在進入寫作領域時,須先拔除一個“幻象”,即“家庭天使”,她溫順、純潔,不可表達出自己的真實情感,受到很多禁忌的限制;“家庭天使”的“幻象”束縛著女作家的表達,令她們只做規矩順從的女人,強迫她們展現出符合女性規范的形象,所以,女作家須先將其“扼殺”,才能真正寫作 [1](p.279)。 伍爾夫所處的20世紀初尚且如此,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作家更是深受此“幻象”的羈絆。因此,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維多利亞性”(Victorianness)之一即是再現女性的“家庭天使”形象[2](pp.2-3)。在刻畫女性形象時,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們或是亦步亦趨,或是離經叛道,但終歸都避繞不開“家庭天使”意象的糾纏。
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意識形態(domestic ideology)與維多利亞社會現實之間的鴻溝,是這一時代的一大焦點。維多利亞時代小說中的“寫實性”面臨的其一問題即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天使”理想與女性在社會中的現實處境矛盾重重,作家對這種緊張關系的意識決定了他們展現出怎樣的女性形象[3](p.53)。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男作家多因兩性差異,無從窺探女性的真實內心,也因其對女性充滿期待,其筆下的理想女性常與“家庭天使”的意象亦步亦趨。經典女作家筆下的女性雖也深受“家庭天使”原型的影響,但還是較為貼近社會現實,她們在女性人物身上寄托了改變女性命運的期望。凡此種種,不能不讓人好奇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意識形態究竟為何物。追根究底,維多利亞時代家庭意識形態的緣起,與英國中產階級的興起休戚相關,它的成形,也承載著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嚴肅的道德追求所向。這是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女性最具統治效力的意識形態,引導但同時也牢固束縛著這一群體女性的行為舉止及思想等等。這亦是維多利亞時代中后期中產階級女性開始著力改變自身命運的出發點。
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道德追求
知名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Laurence Stone)在《一個開放的精英體系》中寫道,1660—1800年間,英國社會出現了“中間階層”(middling sort),人數眾多,充滿“活力”,盛載“財富”,這是這一時期英國最重要的社會特征[4](p. 408)。斯通所指的“中間階層”此時是介于貴族和下層勞動者之間,主要包括從事貿易和專門職業(profession)的兩大類人群,而到了19世紀初期,中間階層的人群大量擴展,并且逐漸用“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稱謂自身。不過,這不僅僅是稱謂的變化。此前的中間階層尚未孕育出特定的階級自覺意識。但是,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在一系列事件尤其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反谷物運動的推動下,此階層的人逐漸認識到自己和這個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分享共同的利益,與另一群體的利益則明顯對立。在“階級”實體形成的過程中,人們越發能感知到社會中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沖突劇烈化,“階級”一詞也漸漸取代“階層”等詞匯來稱謂這些人群。“階級”在19世紀的語境中充滿“社會沖突”與“敵意”的色彩[5](p. 26)。這些沖突和敵意不斷得以化解,又不斷重獲新生。中產階級在利益沖突的推動中生成,成長為維多利亞社會舉足輕重的一股力量。
英國的中產階級主要起家于工商業,廣泛容納了相當多的人群。收入來源是劃分階級的主要標準,據此可劃分出貴族(地租,rent)、中產階級(利潤,profit)及工人(工資,wage)三大階級[6](pp.36-40)事實上,維多利亞人還采用其他標準為當時的社會人群歸類命名。同樣是三層式架構,托馬斯·卡萊爾以是否“工作”(work)來劃分,分別是“工人、工作的雇主和不工作的雇主”(Workers, Master Workers and Master Unworkers)。FD毛利斯的劃分法是“貴族、商業階級和工人階級”(the aristocracy, the commercial classes and the working classes)。馬修·阿諾德將維多利亞人分類為,野蠻人、貴族(Barbarians, the aristocracy),非利士人、資產階級(Philistines, the bourgeoisie)和大眾、工人(Populace, the workers)。除了上述三層式的社會等級分類法之外,還有兩分法。例如,馬克思按照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把當時的英國社會歸納為兩大敵對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科貝特(Cobbett)認為,維多利亞社會是由“主人和奴隸”組成;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在《西比爾》(Sybil, or the Two Nations)中則歸納出“富人和窮人”兩類人。但是,歷史學家貝德瑞達(Bedarida)指出,馬克思雖然這樣劃分社會人群,他卻注意到統治階級中其實存在著貴族與資產階級兩大陣營,而且在《資本論》未寫完的最后一章中,馬克思的生產過程理論也是以租金、利潤、勞力為基礎的,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對維多利亞社會等級的建構其實也是三層式的,包括地主、資本家、工薪者。馬克思的這一概念,其實源自亞當·斯密等人根據生產收入類型來定義社會結構的思想。貝德瑞達認為,在眾多對維多利亞社會等級的三層式建構中,似乎更為普遍的分類法是,社會底層是普通大眾(popular classes),或稱下層或工人階級(the lower or working classes),中層是資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最上層則是貴族或稱上層階級(the upper classes)。這種三層式的社會等級結構根源于人們的思維習慣中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參閱Francois Bedarida,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51-1990, trans., ASForster and Geoffrey Hodgkin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pp36-40。。18世紀后期開始,英國城市中的工商業者,抓住工業革命的契機,迅速累積財富,中間階層的隊伍擴大。到了19世紀中期,中產階級日漸成為英國社會的中堅力量。不過,雖然統稱中產階級,其內部又不乏差異。中產階級內部按財富多少又可細分為上、中及下層中產階級。上層中產階級主要包括大金融家、銀行家、大商人、工業家,以及部分高級職員,年收入在800英鎊以上[6](pp. 48-53),過著同貴族水準較為接近或更為優渥的生活。中層中產階級年收入一般在300—800英鎊之間,包括一般雇主、律師、文人等,生活節制有度,安逸舒適。下層中產階級則主要由小商販、小店主、推銷員等組成,年收入在100—300英鎊之間。中下層中產階級人數占中產階級的多數。值得注意的是,middle class漢譯“中產階級”“中產”,在中文語境中可能讓人產生聯想,認為這一階級的收入在英國社會中處于中等水平。當然,這也符合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實際狀況。不過,英國上層中產階級(尤其是大金融家、大工業家等)或甚至是中層中產階級其實可能比部分貴族更為富有。但是,他們依然位列中產階級,因為middle class這一概念在英國更多指向的是其社會地位,而非其收入水平。
中產階級內部雖然存在職業類別、收入水平等差異,他們卻擁戴共同的價值體系,以“工作倫理”(work ethic)為其核心理念。凝聚階級的因素之一在于,一個階級必須形成與其敵對階級相對立的本階級理想。在這一方面,塑造各階級理想的功勞主要應歸功于中產階級職業人群中的思想家。這些人從理論上將各階級的理想“道德化”,將各階級自身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升華為道德層面的追求,并催促其努力達成目標 [5](p.261)。他們塑造出的中產階級男性理想形象以工業家為原型:富于進取,奮斗不息,勤于自助,節制有度。中產階級的核心理念是“工作的福音”(the gospel of work)。事實上,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英國社會即已認識到“工作”的重要性。不過,視“工作”為“福音”卻是始于維多利亞時代。在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等人努力下,這一理念深入人心。維多利亞人賦予了“工作”多層面的意義。在世俗層面上,工作是工業社會新興中產階級賴以生存的源泉,是工業社會物質進步的根本途徑;在清教傳統濃厚的中產階級中,工作還被看作是在完成上帝賦予的使命,是高貴的行為[7](pp.242-262)。因此,“工作倫理”也成為中產階級批判貴族的懶散與腐朽的利器。他們同時還把矛頭指向工人階級,通過宣揚“工作倫理”來展示自身的道德優越性。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將“工作倫理”推崇到了極致境地。
中產階級踐行“工作倫理”來贏取經濟實力,在維多利亞社會的經濟生活中日益占據主導地位。但是,他們還須確立自身的社會地位,這主要通過模仿貴族的文雅生活方式(gentility)來達成 [4](pp.397-426)。在模仿之中,兩大階級的紐帶又得以聯結。貴族的文雅之風,主要先由上層中產階級習得后傳播至整個中產階級。這些人尤其是上層中產階級中的新富(大工業家、銀行家等)的影響至關重要,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即是中產階級的理想。中產階級理想的生活圖景中有著大房子、仆人、雅致的馬車、精致大方的晚宴,以及供養在家的貴婦人等等。有學者將這種生活方式稱為“全套的文雅生活”(paraphernalia of gentility)[8](p.87)。乍看之下,仿佛與貴族生活相去不遠,實則不然。對于貴族而言,盡顯慷慨奢華是他們的責任,但中產階級卻是不同,他們必須在追逐文雅生活的同時保持節制的習慣,因為他們的收入不如土地貴族的穩定。貴族的奢華生活顯然讓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望塵莫及,但他們按著自己的收入水平也能過上體面的生活,也學著在體面的家宅里供養著閑散的妻女,外出時有馬車接送,在家有傭人在旁服侍,一應俱全。雖然中產階級與貴族在經濟利益上互為對立,對文雅生活的追求又轉而成為聯結二者的紐帶。這兩大階級間有著“同質”(homogeneity)的文化和行為舉止方式 [4](p.423)。
中產階級構筑與貴族的紐帶不僅在于前者跟風后者的生活方式,還在于中產階級逐漸選擇“紳士”作為自身認同的對象。爭取成為紳士既能提升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金錢泥沼中摸爬滾打的中產階級追求道德生活的體現。雖然紳士也位列貴族,但他們不屬于公侯伯子男爵這類有頭銜貴族。中產階級只須擁有一定地產即有望成為鄉紳。“紳士”吸引中產階級之處還在于,他們擁有社會地位,具有土地貴族的名望,可為與“貿易”有關聯的中產階級去除“貿易”的不良名譽。“紳士”有著社會地位的內涵,又不是個相當民主的概念,于是成為中產階級男士潛心模仿的典范。紳士風度的精髓在于文雅的行為舉止與高尚道德之間存有某種聯系。道德(morals)與行為禮儀(manners)互為貫通,文雅的舉手投足映透出美德的光芒。在此意義上,以紳士規范為標準來約束自身,亦能成就中產階級男性的道德追求。不過,中產階級并不單純被貴族的“紳士”概念同化,而是依靠本階級的重要社會力量,改造了“紳士”的概念。
中產階級選擇貴族作為仿效的對象,在沖突與調和中構建自身的社會地位,追求道德生活。在兩套價值體系的沖突中,最難以消融的是中產階級的“工作倫理”與早期以貴族為主要構成人群的紳士的基本特征之間的矛盾。化解沖突的過程催生了新型的中產階級職業理想。貴族紳士的根本特征是不事體力勞動,有賴地產過日。這顯然與依靠工作起家的中產階級的根本理念不相融合。19世紀五六十年代,中產階級發起的政治運動,要求英國政府部門改革政府對文職人員的招聘方式,要求政府重新審視公學教育體制等等,推動了“紳士”的重新定義。在這股東風之下,大約開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公學改革,強調以“職業精神”(professionalism)為根本,注重培養學生的誠摯品性(moral earnestness)、公共服務精神(public service)、公允無私(disinterestedness)等品質。進入公學的中產階級后代在畢業后大多避離父輩的工商職業,轉而成為專門的職業人員,組成了新一代的職業人員精英團體。到了19世紀最后25年間,維多利亞社會似乎已形成某種共識,認為不論父輩從事何種工作,接受公學通才教育的學生都掌握了“文雅”的門道,具備了“紳士”的資格。職業精神與公共服務精神的突顯,也使得“紳士”概念與“工作倫理”的沖突得以緩解。在此意義上,19世紀英國社會產生的是新興的“紳士化、職業化、官僚化”的資產階級,不是恩格斯所說的“資產階級貴族”(bourgeois aristocracy),而是“貴族式的資產階級”(aristocratic bourgeoisie)[4](p.411)。
英國中產階級在這一時期心態復雜。他們將自己視作工業文明的主要貢獻者,對自身所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但同時也意識到工業發展、利潤追逐等引發的社會問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19世紀40年代英國中產階級的“社會性特征”——節制、嚴肅、節儉、工作等成為當時社會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但后來在對待弱者的態度等問題上這一“社會性特征”又融入了“公共服務”的重要理想 [9](p.80)。 在同一意義上,歷史學家亞撒·布里格斯(Asa Briggs)也認為,所謂的“維多利亞主義”(Victorianism)包含四個主要構成因素,即“工作的福音、認真的品格、體面、自助”[10](p.450)。這些都是源自中產階級的價值理念,他們代表著進取、勤儉、競爭、自律、節制等優良品質。布里格斯進一步分析道,對這四個因素的強調,并非自滿的情緒所致,而是維多利亞人“感覺到若要掌控好機器,提高生活水平,他們需要尋找到一個穩定的道德秩序,能扶助他們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與這個從18世紀80年代以來飛速發展的國家并存共榮” [10](p.451)布里格斯在分析斯邁爾斯鼓勵人們培養自助節制等美德時指出,斯邁爾斯推崇這些美德,“這反映了盡管這個社會業已取得驚人的工業成就,卻仍然存在大量的浪費和無效率現象,因而這個社會需要美德。維多利亞人尚未握有一個能讓他們馴服自然并控制機器的牢靠的道德秩序,而如若他們想要達到心中所預想的經濟增長速度,他們需要這樣的秩序”。參閱Asa Briggs, Victorian People: A Reassessment of Persons & Themes, 1851-186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124. 斯通亦指出,這一時期英國社會大量規勸引導人們行為的文學作品都一致宣揚清教教義,反對人們縱欲享樂,但不能因此認定中產階級普遍都遵從這一教義。相反,如此頻繁反復宣傳,并不能證明清教教義的勝利,反而是表明了耽于享樂等習氣頑固存在。參閱Laurence Stone and Jeanne Stone, An Open Elite?, p256這些分析都表明,維多利亞人并非已經具備了他們所津津樂道的這些美德,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無論是維多利亞社會還是維多利亞人都有賴于這些美德,因而他們孜孜以求之。。 因此,對道德生活的追求成為保障中產階級自身及社會發展之必要。于中產階級而言,他們在追求文雅生活,以及在將自身塑造成為紳士的過程亦是在追尋道德生活。與此同時,他們對道德的追求還體現在其對另一重要理想的建構——“家庭理想”,而這又關涉到另一群體,即他們的妻女——中產階級女性。
二 “家庭理想”與“家庭天使”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中產階級的道德訴求不僅體現在中產階級男士的“紳士化”(gentrification),還通過更大范圍內的“道德革命”來實現。不過,這一“道德革命”(Moral Revolution)[5](pp.280-290)的推行早于中產階級形成之前,大概從18世紀80年代即已開始。這一時期英國社會的道德觀念、行為舉止、風格品位等各方面發生的變化已開始影響人們的生活。1780—1850年間,英國變得不再是最“喜好爭斗、野蠻、粗暴、直率、喧鬧、殘忍、血腥”的國家之一,轉而變為最“壓抑、禮貌、有序、溫柔、拘謹、虛偽”的國度之一 [5](p.281)。 這一轉變無不得自當時中間階層發起的“道德革命”的影響。這場“革命”中,中間階層塑造了他們自身的高尚道德形象,抨擊貴族的腐化習氣,以及下層勞動者的墮落。從18世紀晚期開始,嚴肅的中間階層人士越發為自身求取道德領域的統治權。他們拒絕將“地產”看作榮譽之源,強調“內在精神”的首要地位,將家庭生活作為基督式的“善”的生活的必要基礎 [11](p.450)。中間階層人士構建他們理想中的鄉村家庭生活藍圖,把家庭設定為培育道德的源起之地,用以對抗城市商業生活的腐化墮落。在此精神指引下,這場“道德革命”也萌生了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家庭理想”,亦催生了這一時代的主導女性典范意象——“家庭天使”。
“家庭理想”的出現,不僅源自中產階級求取道德生活的內在需要,其成形還得益于18世紀中后期英國工業革命所創造的外在條件。這場工業革命促使家庭和工作場所分離,家庭作為生產場所的功能逐漸喪失,漸至具有隱私性,這一變化為“家庭理想”的產生奠定了實質基礎。同時,新富起來的中間階層家庭僅靠家中男性的勞動,已足以支撐整個家庭的生活用度。因此,這些家庭的女性開始退出生產性活動,賦閑家中,后來成為“家庭理想”的承載者。擺在她們面前的生活與工業革命之前已婚女性的生活迥然不同。工業革命之前的已婚女性常被稱為“完美的妻子”。她們生兒育女,打理家務,身兼重任,在生產過程中又是丈夫的幫手,農場、儲物間、廚房等到處都活躍著她們的身影。但是,工業革命之后,這些家道殷實的家庭中,家務可由專門的仆人分工承擔,家中女性開始享有更多閑暇。她們似乎迅速成為“閑散淑女”(a lady of leisure) [12](p.66)。中間階層的道德改革家們急于重塑“家”的概念,定位本階層女性的生活重心。
18世紀后期開始,福音派(Evangelicalism)將孕育道德的任務交付予家庭,重塑女性形象,規定女性在家中的道德重任。面對新興工業城市出現的種種罪惡,面對上層貴族的道德墮落之風,福音派以威廉·溫布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漢娜·摩爾(Hannah More)等為首的改革家們深切意識到提升英國國民的德性品行的緊迫性,提出了回歸鄉村、回歸家庭的理想,強調鄉村家庭生活(domesticity)對道德培育的重要意義。在定位女性的家庭角色之前,他們重塑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認知。以醫學上的新發現為依據,人們漸漸認定女性的性欲幾乎是不存在的。長期以來,女性身為性欲強的長舌婦在此之前,醫學上認為從身體構造而言,女性是男性的不完美的翻版,因此,女性必須服從于男性,而且女性的身體構造也決定了她們身上有許多不穩定的因素。男女身體構造不同,造就了性情的迥異:男性積極主動、精力充沛、勇敢強壯,女性則溫柔被動、心地善良。此外,宗教上規定,兩性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但夏娃是從亞當的肋骨所生,女性為男性而生,作為男性的配偶依附于男性。夏娃因其道德毅力孱弱,導致了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因此,女性要飽受分娩之苦,并且須承擔撫育孩子的責任。順從、虔誠是女性的優良美德,但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多數女性都缺乏這些美德,對女性的整體評價相當低,女性常以長舌婦、妓女、女巫意象出現。參閱Sara Mendelson and Patricia Crawford, 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1550-1720,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pp15—74。等負面主導形象逐漸消失 [13](pp.15-74),轉而以謙卑、被動等面目面見世人。福音派還規定了“女性氣質”(femininity)的基本內容。他們將“依賴性”定為女性本性之根本,把女性描述成虔誠的妻子與母親。女性的救贖之路在于承擔母性責任。女性與男性在精神層面上被認為是平等的,但女性在社會地位上依附于男性。當時的英國社會充斥著這些論斷,部分原因可能也是針對女權主義者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宣揚的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張。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在《為女性權利辯護》一書中指出,兩性的差異是其所受的不同教育造成的,女性在智力等方面落后的根源在于其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女性有權接受應得的教育。在此問題上,漢娜·摩爾則主張男女之間生來存在差異,男性擅長執掌公共領域,女性則適合家庭生活。兩分領域的概念(separate spheres)在這一時期開始成形,主張經濟、政治、商業、法律領域分屬男性,而女性的領域是在家庭之中。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的觀點是到了19世紀末才更多引起女權主義者的重視。她主張的男女平等教育權實際上也是針對當時的另外一脈思想而作,尤其是讓—雅克·盧梭等人所持觀點。他們否認女性接受教育的權利,把女性視為家庭的裝飾,認定女性只為愉悅男性而生。在同一問題上,摩爾認為,女性具有仁善天性、溫柔品性,并且因為久居家中,不受社會腐敗之流的影響,易保有美德,她們順理成章理應擔當起維護家庭道德的大任。摩爾摒棄了把女性作為家庭裝飾的觀念,提升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主張更為溫和,也更為當時的英國社會所普遍接受。
福音派的“家庭理想”在維多利亞時代由約翰·桑德福夫人(Mrs. John Sandford)、薩拉·路易斯(Sarah Lewis)、艾利斯夫人(Mrs. Sarah Stickney Ellis)等人承襲。她們的指導書緊隨福音派的基本主張,以女性的善良品性為出發點鋪陳細述。如桑德福夫人所言,女性可以選擇自己作為自私的人的短暫性存在,也可以選擇一種更崇高的聽從基督召喚的存在方式,把和善的影響傳播至周圍的人[14](pp. 1-13)。在《女性使命》(Womans Mission)中,薩拉·路易斯力主女性要利用其影響力使社會重獲新生。這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理想”貫穿始終的基本理念。舊日的社會原來是強調宗教和家庭合力對女性的危險性情加以遏制,如今轉而倡導女性完成使命,鼓勵她們選擇圣母瑪麗亞而非夏娃之路,這一轉變的意義是重大的 [3](p.4)。 而且她們拒斥將女性定位為家庭的擺飾,賦予家庭女性更為重要的角色。不過,福音派改革倡導的是回歸鄉村、家庭,更注重在鄉村中構筑“家庭理想”。但是,到了維多利亞時期,多數中產階級家庭都只能安居鬧市或是城郊,改革家們相應也把“家庭理想”的構建地轉移到了城市。當人們不可能享受鄉村生活時,甜美的家庭生活對于許多住在城區的中產階級家庭亦是個絕佳的替代。營造甜美生活的重任,落在了家庭女性身上。家庭是男性逃避外界、與世隔絕的場所,卻是女性的責任之地。“家庭理想”倡導者們在認可男女分域而治的前提下,試圖為女性確立發揮作用的新領地。
維多利亞時代“家庭理想”倡導者中,以艾利斯夫人的影響最深,最具代表意義,她的思想后來影響了全體中產階級女性。艾利斯的思想精髓在其第一本著述——《英國女性》(The Women of England: Their Social Duties and Domestic Habits, 1839)中亦已點明。書名中的“女性”一詞用意頗深。艾利斯指出,當時的指導書很多是為貴族淑女(lady)或生活在這些人影響之下的女士而寫,她的書卻是為“中產階級的女性”而作,主要涵括當時收入有限的職業人士、貿易制造業者、商人等中產階級群體的妻女。艾利斯的思想脈絡中首先構建了“家”的概念。在她看來,房子不僅要整潔干凈,還須迎合家中每個人的品味,不給他們造成困擾,保持寧靜平和、美麗雅致。家庭須兼具外在的“秩序”“舒適”與內在“自信的堅實壁壘”,足夠強大以阻擋任何“外界敵人”的入侵,因而女性不僅要將家庭打理體面,且要輔之以“家政管理”技巧,投入“最崇高、最良善的情感”,這樣才能營造出真正的家庭 [15](pp.25-26)。 艾利斯強調,盡管當時的女仆可以包攬各種家務,但是,構建理想家庭的重任落在女主人身上。
艾利斯認為,當時的女子教育培養出來的女性無法營造出真正的“家”。她批判將女性培養成家庭裝飾物的女子教育制度,主張中產階級女子教育應旨在培育女性無私的道德品質,使得她們能夠勝任道德重任。但是,當時該階級的女子教育仿照貴族女子教育方式,輕道德教育而重女子技藝。這些技能無益于她們承擔肩上的重任,且造就了當時女性“病態的精神萎靡”,使得她們急于逃避任何“實實在在的個人職責”[15](p.15)。 艾利斯的目的是將女性教導成為英國社會的“積極活躍且有用”的成員[15](p.265)。女性心中潛藏著美好的道德能力、廣博的同情心與善心等,但如若不能將這些品質付諸實踐,也就無法造福他人。因此,女性應在日常生活中勤加習練,培養每日向善的習慣,才不至于空有善心,無任何實際影響力。當時社會唯獨缺乏指導女性具體行動的書籍,倒是有許多關于女性行為舉止的指導書,但皆是空泛之談,沒有“直接對家庭與社交場合中的細枝末節加以定義,但其實這些細節是有助于習慣的培養,為完善道德品性奠定基礎的”[15](pp.v-vi)。艾利斯的書意在填補這一空缺,傳授女性持家之道。
艾利斯等人的“家庭理想”主要圍繞著女性的道德使命的命題展開,引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具體而微地發揮作用,影響男性,提升男性的道德高度。艾利斯和漢娜·摩爾一樣,都把家庭生活看作女性的“道德使命”。女性孜孜不倦錘煉自身道德的目的,是為了在家庭生活之中影響男性,借以遏制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日益增多的惡行。艾利斯聲稱,女性的最佳品德是極具道德感、“無關私利的善心”(disinterested kindness),居家女性應憑借自身的高尚品德影響男性,使得男性在政治經濟領域行事時能謹遵道德原則。男性需要女性在道德方面的引導。事實上,艾利斯并無貶低男性道德水準之意,而是認為他們在社會上打拼,易受引誘,導致道德下滑,而女性常居家中,更易保持道德純潔,因而很適合做男性道德良心的向導。艾利斯這樣寫道,在“市場”“交易所”“公共場所”,男性的私心一再受到引誘,正直之心稍稍動搖,利益驅動之下他的決心開始瓦解;而正是此時,女性平日里的“潛在的秘密的影響”好似已化作男性心中的“第二個良心”,男性隨身攜帶,隨時作為行事的參考或精神指引,在內心波動或外在誘惑出現時,他會想起遙遠家中孤獨守候在爐火邊的謙卑女主人,記起她的美德,這將驅散他腦中的混沌,他回到家時將變得更具智慧,也更為良善[15](pp.46-47)。女性的道德感即是如此發揮作用的。女性的道德感和道德責任的命題影響至深,甚至成為當時相當一部分女性用于定位自身的最主要要素。
艾利斯等人筆下的理想女性形象,后來因考文垂·帕特摩(Coventry Patmore)發表于1854至1862年間的贊美其妻的組詩——《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得名“家庭天使”,后又被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神化。帕特摩在名為《紫羅蘭》(The Violets)的第五章中的“比較”一節,開篇即描畫了兩性差異,女性的“被動”、“純潔”性情與男性的“進攻性”形成鮮明對照 [16](pp.146-162)。1864年,羅斯金的《皇后的花園》(Of Queens Gardens)一文更是極盡對女性溫順、純潔、虔誠形象的神化。羅斯金也將建筑理想家園的責任交予女性。他寫道,女性依靠的是她的“管理”而不是“征戰”能力,女性的智力是用以“溫柔地下發指令,做出安排和決定”的,而不是用來“發明或創造”;只要這樣的“真正的妻子”出現的地方,家就圍繞她而存在[17](pp.136-137)。羅斯金的理想家園是遠離“恐怖” “懷疑”與“分歧”的“寧和”之地;一旦紛繁復雜、充滿敵意的外在世界滲入到家庭的私密世界中,它便不再成其為家[17](p.137)。在這片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神圣之地,男性保護女性免受各種誘惑、免于受傷;女性則守護家中,給予外界歸來的飽經考驗的男性精神上的慰藉。在這些話語中,女性被推崇至極,家庭也似乎變成了宗教圣地。不僅如此,在社會生活中,維多利亞女王與阿爾伯特親王也為全民樹立了“快樂家庭”的形象,布里格斯贊譽這是維多利亞女王與阿爾伯特親王取得的諸多“成就”之一,因為維多利亞時代王室的幸福家庭生活與前任王室的荒淫無度形成鮮明對照,后者更多是因“缺點”而非“美德”聞名全國[10](p.459)。JH米勒把維多利亞人在他人身上寄予宗教般仰慕的心態歸因于維多利亞社會宗教信仰的日漸式微[18](p.96)。華特·胡頓也認為,將家庭神圣化是對“蓬勃發展的商業化生活和宗教信仰式微的回應”[7](p.348),這個時代的商業追求與“批判精神”正在摧毀一些道德與精神價值,而“家庭是這些道德與精神價值的避難所”[7](p.347)。在此意義上,“家庭理想”亦盛載了維多利亞人應對宗教信仰式微、商業腐敗等社會危機的希望。
不過,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并不僅僅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私密道德場所,還是彰顯社會地位的地方。這又涉及女性的另一角色的扮演。對此,歷史學家湯普森(F. M. L. Thompson)有過精辟的總結:“家庭作為展示社會地位的工具,同時也是外在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家的主要功能可能是用蕾絲窗簾或者女貞子樹籬來構建家庭生活的隱私,但同樣重要的可能還在于,房子的尺寸、模樣、風格和地點明顯象征著家庭主人在社會等級中的具體地位”[19](p.152)。那么,打理家庭、提升家庭社會地位的責任同樣也落在女性肩上。具體主要涉及三件事:如何起家、如何管理、如何改進。[20](p. 218)針對女性的這一任務,畢頓夫人(Mrs. Isabella Beeton)的《家政管理之書》(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華倫夫人(Mrs. Warren)的《我每年如何用兩百鎊持家》(How I Manage My House on Two Hundred Pounds a Year)等指南書具體教導女性如何明智地使用錢財,將家庭門面裝扮體面,盡顯社會地位與品味。這一時期還出現相當多的“禮儀指導書”(etiquette books),指導女性的行為舉止、穿著打扮等等。有學者指出,此類書在1804至1828年間消匿無聲,卻又在30年代悄然再次興起,這與中產階級開始求取在英國社會的地位共時,它們的興盛代表著中產階級家庭建構社會地位的需求;家庭女性在此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她們的互訪、穿著打扮、家政管理等都是家庭地位的表征[21](p.27)。因此,中產階級女性的另一緊要任務是合理利用丈夫的錢財來為家庭打造體面形象。
由此可見,“家庭理想”倡導者們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家庭女性定立了有意義、有擔當的角色:道德的守護者與體面家庭的營造者。實際上,帕特摩、羅斯金的女性與艾利斯夫人、畢頓夫人等的略微不同,這在后世一些研究著述中皆有所論及,前者渲染“家庭天使”的被動溫順,后者卻突顯女性作為能干的家庭管理者的形象[22](pp.248-249)。這些針對女性的意識形態話語,一方面強調她們在兩性關系中的依賴性和柔弱;另一方面,又期待女性能夠有效管教孩子、打理家政。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面對的顯然是多重的意識形態聲音。不過,家庭意識形態強加于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身上的多重角色之間的矛盾之處以及此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亦成為女性改變自身命運的契機。
三 “家庭天使”的現實困境與出路
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意識形態給女性的生活帶去了諸多限制。“家庭理想”的倡導者在糾正當時女子教育重技藝輕道德的偏向之時,側重強調女性道德的重要性,卻也忽視了女性的智力教育。艾利斯的指導書中也多次論及女性的“學識造詣”(intellectual attainments),指出女性是孩子生活中的啟蒙者,因而其智力教育環節對培養下一代的健全品格至關重要。艾利斯反復強調,女性不應為了掌握知識而學習,學習最終應是為了鍛煉心智,更好服務于家庭生活。但艾利斯在此話題上也只流于空泛說教,智力教育僅在她的指南書中占據極小篇幅。家庭意識形態過分注重女性道德的培育,最終也導致了女性的智力教育被嚴重忽視。
“家庭理想”的另一后果是,女性還因被賦予了道德使命而困陷家庭生活中。“家庭理想”取“天使”意象用于女性,卻僅是取其道德性和純潔性,并未給予女性“天使”般的行動自由。最初,鑒于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經濟領域之外,艾利斯夫人等人致力為中產階級女性在家庭領域中謀求一方天地,把道德領域的重任委于女性。在她們看來,女性如若卷入政經領域的利益紛爭中,不免會喪失其德性,削弱其道德影響力。薩拉·路易斯這樣分析道,女性作為男性的道德代理人、道德原則的典范、正義的代表,不偏向權宜便利,在男性心中根植不妥協的責任感和自我奉獻精神……一旦她的動機或個人品格成為受攻擊的對象,女性的和善影響隨即失效;單是這一緣由就應該耐心地督促她與公共事務隔絕 [23](pp.50-51)。有鑒于此,“家庭理想”從對女性道德感和道德責任的推崇出發,引申出其主張的核心要求,極力反對中產階級女性進入政治經濟領域,主張將其活動范圍限制在家庭領域之中。在此意義上,“家庭理想”既賦予女性影響男性的力量,卻也進一步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因此,在維多利亞時期,女性作為道德價值承載者的地位得以加固,“家庭理想”確立了中產階級女性在精神生活中的責任角色,給予了她們權利,但同時卻也限制了其活動空間。
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女性而言,婚姻是她們生來即被規定的必然命運,家庭幾乎是她們唯一能施展能力的地方。家庭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影響著維多利亞人的價值觀念。工作幾乎被看作是件丟臉的事。而且中產階級女性可從事的體面職業少之又少,僅限一兩種,薪水低廉,如家庭女教師(年收入大概在20—30英鎊之間)、貴族夫人小姐的女伴等。做店員等更是有失身份。總之,女性一旦從事跟貿易有關的職業,她很有可能會失去原有的社會地位。“體面”與“女性氣質”的規范牢牢束縛著女性的思想和行為,因而中產階級女性不到萬不得已之時也是不愿屈尊到社會上尋求工作的。中產階級女性的處境猶如:本來可能成為“花園中盛開的花”的女人現在被“馴服”,安全移居室內,成為“室內盆栽”,變成某位男士的財產,女人應是“受限制的、被馴服的、性方面受統治的”,女人必須“深植家中,以妻子、女兒或姐妹的身份,領受男性監護人的保護”[11](pp.191-192)。世俗觀念與社會現實合力將中產階級女性牢牢捆縛于家庭生活中。
中產階級女性非但不能踏出家門,她們甚至在家庭這方寸之地的道德影響力也是有限的。雖是被委以道德使命,女性在經濟上卻須依賴男性。根據宗教訓誡規定,女性與男性在精神方面是平等的,但其社會地位依附于男性,女性應服從男性的統治。艾利斯夫人認為,女性無論從她們的體質,還是從社會地位看,都是“相對性的存在”(relative creatures) [15](p.123)。而且這種從屬關系還通過法律加以鞏固。法律上,已婚女性處于極為劣勢的境地,她的一切皆由丈夫全權代表。雖然英國在1857年已出臺了《婚姻與離婚法》,英國女性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離婚的權利,但該法令明顯偏倚丈夫的利益。丈夫只要證明妻子通奸后即可離婚,但妻子若是意欲提出離婚,除證明丈夫通奸外,還須提供婚姻不幸的證據,如受虐待、遭遺棄、被施暴等。1870年《已婚婦女財產法》出臺以前,妻子的任何經濟收入,繼承或擁有的任何財產皆歸丈夫所有。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丈夫未必就如此專制,但法律加諸女性種種限制,卻是為男性在家庭中占據實際統治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法律與宗教聯合限定了女性的附屬地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家庭理想”所設定女性的“溫柔的被動的力量”[11](p.116)在現實生活中如何發揮實際作用,著實令人懷疑。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女權主義者芭芭拉·蕾·史密斯·博迪尚(Barbara Leigh Smith Bodichon)形象描述道,“女性在被追求和舉行婚禮時被當成天使,婚后卻被剝奪了作為理智與道德的人的尊嚴”[24](p.119)。另一女權主義者安·蘭姆(Ann Lamb)更是早在30年代即質疑女性被限制在家中,是否就能使得社會獲得重生,因為女性在提出道德建議時常被嘲笑,或是一笑置之 [25](pp.31-32)。女性被賦予了道德感與道德使命,卻無從施展,這一境況也推動著她們去改變命運現狀。
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理想”在其成形之時,即已為中產階級女性埋下了改變命運的種子。英國女性形象從18世紀后期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轉變,從夏娃神話轉向圣母瑪麗亞神話,從“引誘者”轉變為“救贖者”,實是對女性進行“去性別化”(de-sexualization)的過程,女性逐漸被剝離其世俗肉身本質 [3](p.8)。在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在指導書以及一些文學家筆下漸至被完全神化,幻化為“天使”。有學者認為,女性行為指南書“代表了女性原型上的巨大進步,它們刻畫了在家庭中承擔有意義的重任的女性” [26](p.19)。提升女性形象并且委以女性大任,這是“家庭理想”倡導者的重大貢獻。無論如何,女性脫去早先的不良形象,不再被視為家庭的擺飾,被冠之以高尚道德的品性,被委以維護家庭道德的重任,這亦是維多利亞社會對女性的認識的關鍵性提升。然而,身負道德使命的女性,卻又受困于智力上的無知狀態,無權與男性接受同等教育,無力贏得經濟獨立,不能服務于更廣大的社會領域。她們日后自然是要逃脫狹隘的領地,尋求發揮作用的更廣闊天地。在這層意義上,賦予女性高尚的品性,卻也是極具意義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女性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各樣矛盾,推動著她們去改變自身的命運。
[參考文獻]
[1]Virginia Woolf, “Professions for Women”, The Virginia Woolf Reader[M], ed., Mitchell A. Leaska,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4.
[2]George Levine, How to Read Victorian Novel[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3]Franoise Basch, Relative Creatures: Victorian Women in Society and the Novel[M], trans., Anthony Rudolf,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4.
[4]Laurence Stone and Jeanne C. Fawtier Stone, 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5]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6]Francois Bedarida,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51-1990[M], trans., A. S. Forster and Geoffrey Hodgkin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7]Walter E.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8]J. A. Banks, Prosperity and Parenthood: A Study of Family Planning among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e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5.
[9]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1.
[10]Asa Briggs, Victorian People: A Reassessment of Persons & Themes, 1851-1867[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11]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M]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2]J. A. Banks & Olive Banks, Feminism & Family Planning in Victorian England[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4.
[13]Sara Mendelson and Patricia Crawford, 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720[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14]Mrs. John Sandford, Woman in Her Social and Domestic Character[M],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and Green, 1831.
[15]Sarah Stickney Ellis, The Women of England: Their Social Duties and Domestic Habits[M],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839.
[16]Carol Christ, “Victorian Masculinity and the Angel in the House”, in Martha Vicinus, ed., A Widening Sphere: Changing Roles of Victorian Women[M],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7]John Ruskin, Sesame and Lilies[M],London: George Allen & Sons, 1907.
[18]J. Hillis Miller, 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Thackeray, Dickens, Trollope, George Eliot, Meredith, and Hardy[M], Cleveland: Arete Press, 1979.
[19]F. M. L. Thompson, The Rise of a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Asa Briggs, Victorian Things[M], London: B. T. Batsford Ltd., 1988.
[21]Elizabeth Langland, Nobodys Angels: Middle-Class Women and Domestic Ide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Joan Perkin, Women and Marriag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 London: Routledge, 1989.
[23]Sarah Lewis, Womans Mission[M],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0.
[24]Barbara Leigh Smith Bodichon, “Married Women and the Law”, in Janet Murray, ed., Strong-Minded Women and Other Lost Voices from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Hard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84.
[25]Ann Richelieu Lamb, Can Woman Regenerate Society? Womans Mission Womans Mission, London: Harrison & Co., 1844.
[26]Patricia Branca, Silent Sisterhood Womans Mission,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75.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文學博士)[責任編輯張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