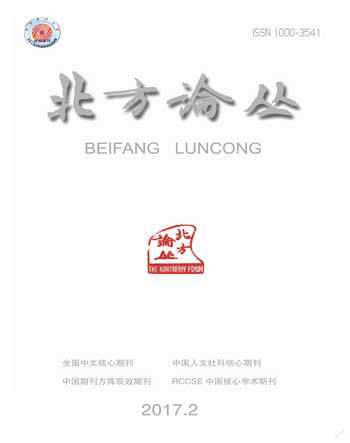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江右詩派”的雅正趣尚與明初詩壇的文治理念
溫世亮
[摘要]“江右詩派”是明初詩壇的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雅正”是其一脈相承的詩學趣尚。從“江右詩派”的精神內涵而言,其“雅正”詩學觀所具有的地域風源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同時,“江右詩派”的“雅正”詩學趣尚,不僅吻合了朱元璋的文道相貫的文治理念,而且隨著這一理念的深入推行而得以彰顯,即能貼近于明初的開國氣象而注入“鳴盛”因子。該詩派也因此受到最高統治階層的推崇褒獎,成為明初詩壇最為耀眼的文學群體之一,產生了較大的詩壇影響,成為反映明初詩壇的重要標識。
[關鍵詞]劉崧;“江右詩派”;“雅正”;詩學淵源
[中圖分類號]I2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7)02-0077-06
Abstract:“Jiangyou poetry” is an important genre of poetry at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 “righteous” is its origin of poetics and still interesting. From the spirit of the connotation of “river right poetry” and the “righteous” Poetics of regional air source is an objective fact.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Jiangyou poetry” in the “righteous” poetics still interesting,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emperor and the phase coherent sandwich concept, an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cept and can be strengthened to stick close t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founding meteorological and into the “Ming Sheng” factor. The poetry and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highest ruling classs respected praise, became the most dazzling literary group is one of the poet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poetry.
Key words:Ming Dynasty; Jiangyou poetry; righteous;poetics
①明初“江右詩派”亦有“西江派”之稱,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張廷玉《明史》、永瑢《四庫全書總目》等,均有此謂。
明初詩壇,流派紛呈,“江右詩派”①即其中之一。作為明初詩壇一個極其重要的詩歌流派,雖以地域命名,但其所產生的影響又遠非江右這一地域所能涵蓋。“江右詩派”以詩派的宗盟劉崧、魁首如陳謨、梁蘭、劉永之、王沂、劉炳等為核心,它的興起、發展和演變既有文學自身的原因,又與地域文化、時代政治等背景密切相關。唯其如此,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不僅有助于厘清“江右詩派”的生成、發展的基本脈絡,同時重點考析“江右詩派”“標宗雅正”的詩學趣尚,較為真實地還原其精神風貌,對其詩作的繼承性、發展性及其在詩壇的影響,對整個明代詩歌的深入研究都大有裨益。
一、 雅音正聲:“江右詩派”的詩學趣尚
明初“江右詩派”之目,最早見于明人胡應麟所撰《詩藪》,其謂:“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于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1](p341)胡應麟以地域為范圍、以劉崧為宗盟標榜“江右詩派”,雖然說還只是其一己之感想而已,其定義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但也為歷來學者所認可,這一標榜自然有合理性,大體符合明初詩壇的實際。因此,我們在探討“江右詩派”的藝術趣尚時,也應當以劉崧為核心,同時牽涉關聯與劉崧大致同時且多有交集的江右著名詩人,從更為寬泛的范圍展開論析,以抽繹他們彼此相通的詩學聲氣。
如果要論于“江右詩派”的詩歌藝術趣尚評價對后世產生影響最為深刻者,莫過于錢謙益的“標宗雅正”錢謙益謂“國初詩派,西江則劉泰和,閩中則張古田。泰和標宗雅正,古田以雄麗樹幟”,見《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88頁。說。錢氏以為“江右詩派”以“雅正”標宗,清代四庫館臣則順其成說而以“清和婉約之音提導后進”(《四庫全書總目·槎翁詩集》)相鼓吹。那么,以劉崧為宗盟的“江右詩派”,是否一如錢氏等人所謂的以“雅正”標宗呢?
楊士奇在《劉職方詩跋》中言:“先生八歲能詩,既長遭兵亂,雖奔竄巖谷,崎嶇無聊之際,日必賦一詩不廢。至遇朋徒相聚,或興有所發,輒累累賦之不倦也,蓋其好學之篤如此。然先生于明經,于古文尤所篤好,詩特其余事耳。”[2](p191)楊士奇的這段跋語,雖說極為簡略,卻見深意,蓋謂劉崧儒學淵深,為詩亦以儒學為先導。其實,劉崧確有一顆“夫息丘園而懷天下憂者,此天下之士也”(《贈蕭一誠赴召序》)[3](p488)的儒者心,論詩亦能守性情之正,發為議論總能見其儒家規范,以下表述大抵如此:
詩則長短句類不如律,而律又不如絕,然皆致思親遠而制調高古,其進而底于成, 蓋未可涯也。(《與張炳文》)[3](p436)
異哉,詩之能感人也。其詞雅,其為人正而有則者歟;其音和,其為人溫而不戾者歟。(《王斯和遺稿序》)[3](p477)
詩本人情而成于聲。情不能自己必因聲以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聲達而情見矣。……其辭清新而不累于陳,和婉而不傷于暴,介潔而不違于物,其情才音調之美,有足尚者矣。(《陶德嘉詩序》)[3](p490)
由此不難判斷,以情感人,追求詩歌的抒情功能乃劉崧論詩的核心所在。但其言辭中所透露出的那種守性情之正的意味又極為明晰,“人正”“詞雅”“人溫”“音和”“聲”“情”并茂而不乖于“心”,而要做到這般,則必須以“清新”“和婉”“介潔”相守恒。換言之,強調人品與詩品為一,約情以守正,又是劉崧詩學之旨歸,這恰是“發乎情,止乎禮儀”儒家詩教傳統的沿承感發,可見“雅正”正是其詩學思想中的應有之義。這樣的詩學趣尚,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劉崧的詩歌創作會呈現出平正典雅而不失正聲的風味。關于這一點,早在明初時期,劉崧友人劉炳便在其《百哀詩·劉子高》中做出了明確的評價,稱其詩有“苦力追正音,漢魏深祖述”[3](p738)之面目;而浙人烏斯道亦有過類似的看法,他在《劉職方詩集序》中指出:“先生(劉崧)之詩,不刻削而工,不峭峻而蒼,不隱晦而深,不險怪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 [2](p195)。
至于“江右詩派”中諸如楊士宏、陳謨、梁蘭、劉永之、劉仔肩、王沂、劉炳、蕭翀等與劉崧過從甚密的詩家名宿,在發掘、守護儒家詩學傳統上同樣是不惜心力的,他們大都是“雅正”詩風的樹幟者。如楊士弘,乃河南襄城人氏,如若從年歲而論,當屬劉崧的前輩詩人。不過,據梁潛《竹亭王先生行狀》,楊士弘寄寓臨江,與萬白、辛敬、周湞、劉崧、陳謨、劉永之、王沂等人“日賦詠往還,更唱迭和,以商榷雅道為己事” [5](p481),自可納入“江右詩派”的范圍。楊氏選《唐音》以表性情、觀世道,一如虞集《唐音序》所謂“蓋其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 [6](p487),他的詩學旨趣,并未游離于典雅正則之外。
陳謨、梁蘭、劉永之、王沂、劉炳等,則是劉崧的同輩人,一樣是傳承儒家詩教的有心人。陳謨乃元明之際重要的理學家,名列《宋元學案》,梁蘭《挽海桑先生》詩嘗以“立志希濂洛,研精續考亭” [7](p737)句相稱述,他論詩亦喜和平正大之音。他嘗序蕭養髙《貞固齋文集》,謂:“其所著詩文命曰《貞固齊稿》,余把玩不釋手,愛其體裁正而豐約適中,論議卓而波瀾洋溢,允為成家。諸詩小絕,多警策樸茂而不鄙,刻意而平夷,律圓妥不陳,五七言古體,寂寥者更腴,流動者絕蔓,蓋所謂不以輕心出之者。”[8](p595)評王竹間《竹間集》則稱:“夫其鐘粹稟溫故,其詩雅馴而藻潔;其中寬而有制,故其詩不矜而嚴,紆徐而達;其臨政奉法,恒務大體,不激不阿,故其詩體裁正而榘矱精;其議論古今是是非非,笑言雅雅,無詘以隨,故其詩善諷而婉……率慕漢魏盛唐之風,而無齊梁綺紈之習,其為可傳無疑。”[8](p603)其論調實與劉崧相類似,人品與詩品合一,言性情而不出于正則。又如陳謨,與其詩學見解相適應,他的詩作亦不失雅正之音聲,他的學生宴璧在序其《海桑集》時,即以“湯盤禹鼎器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正也”[8](p526)相評騭。而歆慕陳謨的梁蘭,亦不愧作者,今尚有《畦樂詩集》傳世,其詩歌創作實多與陳謨詩相符契,楊士奇《畦樂詩集序》即稱其詩“志平而氣和,識遠而思巧,故見諸篇章,沨沨焉,穆穆焉,簡寂者不失為舒徐,疏宕者必歸于雅,則優柔而確,譏切而婉”[7](p713)。視劉崧為摯友的劉永之,亦是理學中人,傳入《明儒學案》,嘗為《劉子高詩集》序,力贊其詩“簡質而極溫潤”[3](p194)的風致,這實從一個側面展示其溫雅醇正的詩學情趣。又王沂,乃劉崧同邑知交,梁潛《竹亭王先生行狀》稱其能以“沖澹瑩潔”之性發為“溫厚和平”之音,且“音律格調之嚴”則“必合于典則”[5](p482)。劉炳與劉崧交誼頗為深厚,詩名遠播于宇內,為詩能轉益多師,然而,雅正亦其詩之風標,宋濂便嘗為其詩集作序,稱其詩“溫潤清逸”“典刑古雅”[4](p755)。
至于蕭翀,曾造劉崧之門墻得其熏與濡染,乃劉崧的入室弟子。宋濂《劉職方詩集序》謂蕭翀“亦嗜于詩,蓋得劉君(劉崧)之傳者”[3](p190)。烏斯道序《劉職方詩集》,則以“清新典麗”稱蕭翀之詩。蕭翀的詩集雖然已散亡,傳世之詩亦不多,但他曾不遺余力地為劉崧編選、刊布詩集,且遍求序言于當時的名流方家以行世,由此足見其對乃師的膜拜推崇,堪稱最能傳劉崧詩學衣缽者。如果將他序與蕭翀編刊詩集的實行兩相參證,亦足可嗅出其所為詩的雅正味道。
從前文的梳理可見,從“江右詩派”的宗盟劉崧,到與其交道深厚的友朋,再及其得意門生,他們在詩歌創作上都有一顆秉承儒家雅正傳統的心志。雖然我們還無法在有限的篇幅之中一一遍覽“江右詩派”所有詩家的創作風貌,也不宜就此斷定“江右詩派”藝術追求上的唯一性;但是,據此我們又足可以宣示:“雅正”乃這一詩派的一脈相承的共同藝術趣尚之一。
二、 地域風源:“江右詩派”的詩學淵緒
任何詩派的形成,總是有其淵源可溯,明初的“江右詩派”亦不例外。既然一如前文所論,“雅正”乃“江右詩派”重要的藝術趣尚所在,那么我們在追溯其詩學的淵緒時,自然也可以“雅正”作為一個角度展開考論。與此同時,“江右詩派”作為一個地域性的詩歌流派,我們又可引入地域觀念,將“雅正”納入地域范圍對其淵緒予以論述。但需要注意的是,“雅正”作為儒家傳統詩學審美規范,它實際牽涉追求高尚健康、蕩滌邪惡污穢的思想內涵和清澹平和、凝練蘊藉的外在形式兩個方面,而往往又以前者為重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以雅正為視域來探討“江右詩派”的詩學淵緒,也應該側重于思想內涵這一節點。
受地理位置、經濟狀況、政治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自李唐五代以還,江右詩歌的興起發展相對滯后,除東晉陶淵明、晚唐鄭谷和李潛等少數詩人之外,知名于文學史者并不多見。直至宋元時期,方呈現出云蒸霞蔚、作者代興的繁興局面。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江右歷來為儒學風氣頗為濃厚的地域,而一如解縉《送劉孝章歸廬陵序》所謂:“廬陵固濂洛之淵源也”[9](p700),作為儒學最為重要的分支之一的理學,更是肇端、定型、興盛于此域。從一定程度上講,江右詩壇似乎也深深地被儒家的傳統詩教所籠罩,而對中和醇雅的藝術氣象的控馭,江右詩人則尤為擅長。從晉之陶淵明到宋之黃庭堅,元之虞集、范梈,細數這些江右名詩人,他們的創作中無不浸淫著一股濃重的雅正氣味。地域文化傳統是影響文學觀念的一個重要因素,發育于江右的明初“江右詩派”,在詩學上自然難以脫離地域傳統的熏染,派中詩人對陶、黃、虞、范等鄉賢亦多有效法。當然,要解釋清楚這一問題,仍然需要從“江右詩派”的重要作家說起。
以劉崧為例,其論詩崇尚雅正,這一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又甚得地域文化之陶染。劉崧對鄉賢陶淵明即至為膜拜,其《題陶淵明像寄劉仲修》甚至將“神閑韻自適,意遠色逾好”的陶靖節視為詩家“鼎鼎百代師”[10](p233),而一如前文所論,劉詩亦不乏清婉和雅之質,陶詩的意境風神藏掖其中。張應泰《刻劉槎翁詩選序》謂:“翁(劉崧)生末造,俗漸于夷,顧能振響天衢,一還大雅,詎不謂難?大江以西,陶元亮而后,弘紹宗風,定當以翁為適” [2](p188),評騭不無夸飾,但又有其合理處。又,前人對劉崧的詩學趣尚,多從宗唐祧宋的角度展開評判,葉盛甚至以其嘗言“宋絕無詩”大加詬病,稱其無視朱熹等宋代賢達于詩學之功深,“欲眩區區之才,無忌憚若是,詬天吠月”[11](pp256-258)。在一定程度上,后來研究者亦多借此來否定劉崧對先賢黃庭堅的效法,但這種從宗唐法宋角度來探討劉崧師法的做法也難免有其缺陷,畢竟它所關注的更多的是詩歌外在藝術表現上的差異性,往往因此忽略了彼此在內在意蘊上的相似點或共通性。實際上,劉崧《書山谷黃太史〈題醒軒詩〉后》最能見其法乳山谷的心跡,今擇其部分引述如下:
太史以宋元豐中來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倏然以自嬉于塵埃之外,若聽泉觀山,倚晴快閣,賦東禪之息軒、石基之變清,皆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于豁然開視、屬望乎禪門之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于是,去之三百年矣,顧其山水之深高者,今猶昔也……念昔太史之留題于醒心也,先師嘗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于心,然余懼其義而或泯也,幸得錄而傳之,將持歸刻于山中以無忘前聞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計是詩者,何啻太倉之一稊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又非直游戲之嘲吟而已也。余惟嘉洞然之生也后,而懷賢嗣先之意,又超然有出于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幾乎,能不負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辭為之大書太史詩于前,復識其說于左,方俾來者又將有所觀感焉。[3](p552-553)
論詩以“溫柔敦厚”為尚的黃庭堅,是宋詩的代表人物。其《題醒心軒》云:“盡日竹風談法要,無人竹影又斜陽。他時若有相應者,莫負開軒人姓黃。”山谷此詩是一首典型的宋詩體,清逸中透出幾分理思,但又堪稱為“陶情寄興”之作,亦不失為雅音正聲。劉崧稱它“非直游戲之嘲吟而已”,實際已從“義”亦即詩歌意蘊的角度予以了高度的認同,其要傳承黃氏詩學旨趣的意愿也至為明確。雖然我們必須承認劉崧與黃庭堅的詩歌在外在藝術表現上的區別,但槎翁詩所表現出的雅正基質與黃庭堅這位前輩又當存在一定的關聯,只是他對山谷詩的傳承偏重于內在理趣意蘊罷了。為此,我們又何嘗不能說其正是黃氏三百年后的“相應者”呢?
虞集、范梈這些以正大典雅樹幟的元代江右名家,同樣深得劉崧之歆慕。在《自序詩集》中,劉崧謂:
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于詩也,其猶有未至已乎!”乃斂蓄性真,湔滌故習,盡出初稿而焚之,益求漢魏而下盛唐詩以來號為大家者,得數百家遍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志所在,然后知體制之工矣。夫求聲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嘗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詠于物理,凡歡欣哀怨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之接乎其外也。吾于是而得詩之本焉,知襄誕之不如雅正也,艱僻之不如和平也,萎靡破裂不如雄渾而深厚也。” [3](p512)
因虞、范之導向而明了雅正和平、雄渾深厚乃詩家之正脈,于是盡廢少時詩作,并以“漢魏而下盛唐詩以來號為大家者”為師范,這一敘說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虞、范等鄉邦賢達對其雅正詩學觀念的啟沃之深。
陳謨、梁寅、梁蘭、劉永之等元明之際這些“江右詩派”作家,無論他們的詩學觀念,還是詩歌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雅正風概,同樣深具濃厚的地域印記。如陳謨,對陶淵明即了然于心,以陶詩之清逸舂容為詩家正則,其《郭生詩序》謂:“稱詩之軌范者,蓋曰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短章貴清夐纏綿,涵思深遠,故曰寂寥,造其極者陶、韋是也。大篇貴汪洋閎肆,開闔光焰,不激不蔓,反覆綸至,故曰舂容,其超然神動天放者則李、杜也。” [8](p619)對黃庭堅同樣欽服有加,其《和楊少府登快閣用山谷韻》所云:“長嘯城頭天宇平,碧山濃處看新晴。過客帆檣煙霧重,傍人鷗鷺畫圖明。浪花細逐金魚起,沙漲還添玉帶橫。物色分留歸少府,千年太史有詩盟。”[3](p557)不僅表達了自己對黃山谷的禮法,而詩作本身的內在情致以至外在風神,亦不乏山谷詩雄渾深厚的韻味。其他如名亦列于《宋元學案》的梁寅,為詩如四庫館臣所謂“舂容淡遠”,“規仿陶、韋,殊無塵俗之氣”[12](p620);而梁蘭,發為音聲則能“于元季繁音曼調之中,獨倏然存陶、韋之致 ”[3](p722);至于劉永之,劉崧的《題陶淵明像寄劉仲修》詩,將其與“斯人管樂儔,而分山澤槁”的陶淵明相類比,以“神閑韻自適,意遠色逾好”[10](p233)相稱道。這些點滴評價,雖然可能只是詩論家們的感性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詩學思想,乃至創作的鄉邦淵源。
不可否認,僅僅將雅正納入地域這一范圍來探討“江右詩派”的詩學淵緒,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按理諸如儒家傳統詩教、時代文化氛圍、新舊朝代更替等都應該成為探討這一問題的背景。不過,綜前所述,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從“江右詩派”的精神內涵而言,其“雅正”詩學所具有的地域風源又是客觀存在的。
三、正統根基:“江右詩派”與明初詩壇
“雅正”,較早見于《毛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由廢興也。”作為儒家傳統詩學審美規范,“雅正”在藝術表現上具有一種區別于綺靡輕浮的清醇面相。從思想內涵上而言,又與“文以載道”的崇尚相吻合。以此觀之,“雅正”顯然符合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觀,雅即代表了正規或者說正統,具有較為明顯的政治因緣,實際也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因此,也為歷代統治者所提倡、所推崇。開國之后,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統治,一方面大力改革社會積弊;另一方面,則不斷地強化文化統治,加強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管控。在文學上,他不僅主張“文儒相兼”“文以載道”,還要求詩以“鳴盛”,追求平實和雅的文學風尚,力求恢復漢唐傳統,嘗謂:“朕觀上古圣賢之言……則身修而家齊,為萬世之用不竭,斯良之至也。今之儒不然,窮經皓首,理性茫然,至于行文流水,架空妄論,自以善者矣。”[13](p137)又曾言:“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嘵淫褻之樂屏去之。” [14](p141)
從某種意義上講,“江右詩派”的“雅正”情趣不但吻合了朱元璋的文治理念,而且隨著這一理念的深入推行而得以強化,貼近于開國氣象而注入“鳴盛”因子,也因此成為明初詩壇最為耀眼的文學群體之一。劉崧元末隱居不出,洪武入仕之后,他能相時而動,不斷修正自己的雅正觀念。如在《與蕭鵬舉》一書中,劉崧不僅對弟子蕭翀所作詩文“辭情實尠而浮文勝”的缺點給予直接的批評,而且進一步指出:“今朝廷更化,去華尚質,士風丕變,于凡名稱尤不可不慎,非獨名稱也,由此推之,何莫不然,足下通敏善學,宜日新所聞,而故習未嘗盡掃除若此,甚可惜也。故特為足下言之,足下幸毋怪其多事也。”[3](p430)自覺地承擔起傳布宣揚朱元璋文治思想的責任。洪武十三年(1380年),為林鴻《鳴盛集》作序,他又謂:“詩家者流,肇于康衢之《擊壤》,虞廷之《庚歌》。繼是者,沨沨乎《三百篇》之音,流而為《離騷》,派而為漢魏,正音洋洋乎盈耳矣。六代以還,尚綺藻之習,失淳和之氣。”[15](p3)追溯詩家之源流,一以“淳和”為正音,同樣能見其以詩“鳴盛”的心曲。
至于陳謨、梁寅、梁蘭等“江右詩派”中的布衣詩人,受鄉邦傳統、時代風氣等因素影響,本來對雅正詩學觀就持贊譽的態度,因此,朱明立國后,王朝所推行的詩文鳴盛的文治策略顯然也在他們文學思想所能接納的范圍中。據宴璧《海桑集序》,陳謨便以“遭時俶擾,其制作弗及黼黻皇獻,以鳴國家之盛”為憾事,而將詩文集“題曰《海桑集》”[8](p526)。對那些能守性情之正的文學作品,陳謨亦力加推揚,如序《竹間集》,即稱“集中佳制,率慕漢魏盛唐之風而無齊梁綺紈之習,其為可傳無疑。……如君之才,其有不鳴國家之盛乎” [8](p603)。梁寅與陳謨秉性相類,其入明之后的“鳴盛”思想同樣突出,朱彝尊稱他“入禮局,雖不為好爵所縻,然《石門集》中”,諸如“萬里升平感圣朝”“赫赫大明逢盛代,載歌周雅贊皇文”一類的“感恩頌德之詞,不一而足”[16](pp57-58)。至于窮逸老死于山林的梁蘭,據楊士奇《梁先生墓志銘》,嘗言:”“士貴有益世用,非徒資祿利,茍榮其身而已”;入明后,更是每以“今幸遭明時,沐治平之澤,不可茍焉自逸,忘所施報”訓誡其子嗣,而所言“惟克有終,以不辱國命貽我羞吾,獲歸守先人邱墓以詠歌太平,盡吾之天年,為樂不既多乎”[17](p181),實乃其初心之所在。
“江右詩派”詩人的“雅正”觀念和“鳴盛”心緒,與朱明王朝推行的文治策略正相對應,這必然會使他們的詩學觀點受到朝廷的重視,并在政治力量的推轂下得以傳布。如以編選《雅音正聲》而揚名明初詩壇的江右詩人劉仔肩,其持守“雅正”規范,甚至被“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奉為明代“為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的“權輿者”[18](p584)。又據梁潛《故山東運鹽司副使蕭公墓志銘》,洪武十四(1381年)年,蕭翀以賢良入征明廷,因賦《指佞草》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許,“擢蘇州府同知”[5](p505)。對劉崧,宋濂同樣欣賞,并力加延引,序《劉職方詩集》稱崧詩“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置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后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茍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能行之于遠乎”[2](p189)。實際上,劉崧亦得朱元璋之榮寵,“屢常擢用”。洪武三年(1370年)以文材舉為職方郎中,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胡惟庸案”致仕歸里,復起用為國子監司業以助“文治”之行,成為明初文治策略的重要的見證人、代言人和執行者。朱元璋不僅以“文學雅正”(尹直《侍郎劉公崧傳》)[19](p1421)盛贊劉崧詩文,在其逝世之后,更是深表痛惜,并特為《祭國子司業劉崧文》,謂:
惟爾有學有行,發譽儒林,朕嘉爾能,屢常擢用。邇者遣使召司業成均,簡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數日間,遽然而逝,朕甚悼焉。已令有司備禮殯殮,靈車歸葬,特以牲醴致祭。[13](p453)
祭文雖然短小,但卻將劉崧的詩壇地位以皇權意志的形式確立下來,為其詩名的后世顯揚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劉崧作為“江右詩派”的宗盟,這些來自于統治階級最高層的揚譽、推舉,無疑具有深厚的政治用意,又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江右詩派”的正統根基,必然促進和強化其在詩壇的聲勢和影響力。
若論“江右詩派”的影響力之深,莫過于對明初“臺閣體”詩歌的啟沃。關于江右詩歌與“臺閣體”的關系,錢謙益所謂“江西之派,中降而歸東里,步趨‘臺閣”,四庫館臣將“江右詩派”視為“臺閣體”先聲,均非空穴來風。一方面定鼎開國的背景為“江右詩派”詩學觀念的延續奠定了良好的時空基礎。“江右詩派”本以“雅正”為緒論,而如前文所論,朱明的開國氣象則又使“鳴盛”因子成為其詩學觀念中的重要成分。“臺閣體”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流派或文學群體,其成員多來自于建文四年(1402年)創立的內閣和翰林院,為明初文治策略的代言者,這一角色決定了他們在進行詩歌創作時必須以歌詠太平為內容、以雍容大雅為特色。當然,“臺閣體”的生成又絕非以“內閣”的創立為起點,稍前于它的“江右詩派”,因闡揚“雅正”“鳴盛”相結合的詩學觀念而深受朱元璋政治集團的器重,實際又成為它們崛起的直接又重要的師法對象
另一方面,明初“臺閣體”作為一個文學群體,因其成員來自于建文四年(1402年)所創立的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禁直機構—內閣—而得名,并以江西籍文人為核心。其中要者又多與“江右詩派”中的詩人關系盤根錯節,至為密切。例如,臺閣“三楊”之楊士奇,乃劉崧同縣后學,對劉崧的文行出處每見私淑之意,這從前引《劉職方詩跋》可窺一斑;與梁蘭,則既為姻家世好,幼時又曾就學梁氏之門,“從受詩法”[17](p181);同時,他又稱陳謨為外伯祖,少嘗“從學海桑先生側”[17](p439),不失姻親師生之誼,得其教澤也深。梁蘭與梁潛、梁混,蕭翀與蕭鎡,羅以明與羅汝敬、胡子祺與胡廣、練高與練子寧、熊直與熊概等,則為父子關系,家學淵源不可不謂深厚。另外,蕭翀曾師事劉崧,蕭鎡則從學于梁潛、楊士奇,梁潛嘗及王沂之門等。總之,“江右詩派”與“臺閣體”文人之間確乎形成了一種或地緣、或師緣、或血緣的復雜關系;而在明初王朝“鳴盛”文治政策推行的背景下,薪盡而火傳,這種關系的形成又必然導致包括詩學觀念在內的思想傳衍。由此看來,胡應麟“先驅當代”之謂,若就“江右詩派”而言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結 語
文學關乎世運,文學與時代文化、社會政治等密切相關。總體看來,順應朝廷文治政策的需要,“江右詩派”本來所具有的的雅正情結,不僅在明初得以強化,植入“鳴盛”的因子,而且亦因此受到最高統治階層的推崇褒獎,從而產生了較大的詩壇影響,成為“臺閣體”詩歌的先聲,成為探討明初詩壇生態的重要參照體。質言之,在明王朝漸趨佳境的過程中,明初詩壇的五大流派,以雅正標宗的“江右詩派”何以能在其他詩派漸趨式微的情況下一家獨秀,固然有其深刻的地域文化因緣,但也同樣存在深刻的時代政治背景,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初政詩壇生態的一個實際狀況,那就是王朝政治已然成為明初詩歌走向的一股極其重要的牽引力,而一種文學趣尚繁興與否與王朝的文化策略有著緊密的聯系。
[參考文獻]
[1]胡應麟.詩藪·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劉崧.劉槎翁先生詩選[C]//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9冊.北京:文獻書目出版社,1998.
[3]劉崧.槎翁文集[C]//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7.
[4]劉炳.春雨軒集[C]//豫章叢書:集部11.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5]梁潛.泊庵先生文集[C]//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00冊.北京:文獻書目出版社,1998.
[6]虞集.虞集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7]梁蘭.畦樂詩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8]陳謨.海桑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9]解縉.文毅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0]劉崧.槎翁詩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1]葉盛.水東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1997.
[12]梁寅.石門集[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3]錢伯城.全明文:第1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4]明太祖寶訓[M].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本.
[15]林鴻.鳴盛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6]朱彝尊.靜志居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17]楊士奇.東里續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12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8]劉仔肩.雅頌正音[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9]焦竑.獻征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6.
(作者系南昌師范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責任編輯連秀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