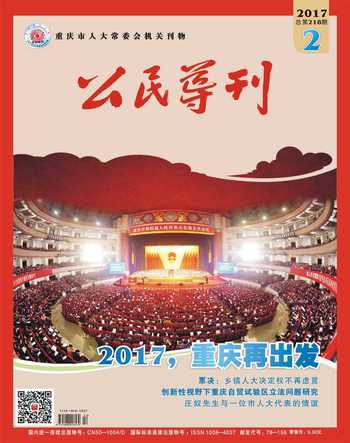改革年代的立法追求
帥恒

回望2016年的國家立法,一方面,修立并舉的立法戰略突入多個重點領域,或推動相關立法升級更新,或開疆拓土填補立法空白,從根本上重塑著法制面貌,引領法治走向縱深。另一方面,諸多關涉國計民生的重大立法,或掀起爭議波瀾,或遭遇立法難題,其最終破冰闖關,無不考驗著立法者的勇氣和智慧,亦見證了現實的立法生態。
正是這些多維開花的立法成果,描繪了2016年豐富多彩的立法畫卷,勾勒了當下法治建設的關鍵脈絡,為時代留下了回味無窮的歷史記憶。
修法授權,頒發改革通行證
踐行“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的法治原則,以滿足深化改革年代的現實需求,是最近幾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和行權的鮮明特色。2016年,為改革頒發合法性通行證的行動更是密集推出,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
其中一個基本方向是運用高效的“打包修法”方式,為改革提供法律支持。2016年7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修改了節約能源法等6部法律。11月,又對外貿易法等12部法律作出一攬子修改。經由這兩次大規模的修法行動,相關立法中的審批柵欄被批量拆除、審批流程被集中優化,進而為以簡政放權為導向的行政改革,及時鋪設了合法性軌道。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9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修改了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不僅以法律形式確認了此前在上海等4個自貿試驗區試點的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而且為這一改革機制向全國復制推廣奠定了法律基礎。由此開啟的,正是一個更加透明開放、更多制度紅利的外商投資新時代。
除了修法引領改革、推進改革,體現法治思維的另一個重要緯度是,立法機關以授權決定等方式,啟動多個領域的試點改革。2016年9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推動司法改革再邁探索步伐。12月召開的常委會會議,更是聯袂出臺在北京、山西、浙江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等4個啟動改革的決定,不僅數量之多創下歷史記錄,而且標志著,授權決定等兼顧審慎改革與法治原則、以程序正義賦予改革合法性的新路徑,已經跨越前幾年的行政審批、土地制度、司法體制等改革領域,進一步突入政治體制、社會保障、人事制度等更為廣闊、縱深的改革疆土。由此開辟的,正是一條漸行漸寬、融合法治精神與改革理想的雙贏之路。
環保稅法,“稅收法定”先行者
2016年12月出臺的環境保護稅法,不僅開啟了以稅治污的新常態,更是彰顯一項重要法治原則的先行態度。
從立法技術而言,環保稅法的立法并不復雜,其實質是推進“費改稅”改革,將實施多年的排污費制度改為環境保護稅,以構建綠色稅制、強化執法剛性。但更重要的立法價值在于,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對稅收法定原則分別作出明確要求和規定后,在一系列單行稅法的立法動議中,環保稅法草案于2016年8月率先啟動了立法審議程序,其標本意義備受矚目。而如何踐行稅收法定原則,也因此成為環保稅立法所面臨的最大考驗。
稅收法定原則的真正落實,并不能僅僅止步于“立法”這一表面形式,更須融入立法設計的具體肌理。環保稅法體現的,正是實質兌現稅收法定原則的追求。從以專章形式確立“計稅依據”、“應納稅額”、“稅收減免”等等,到以附表形式明晰征收標準,無不體現了稅收制度要素必須法定的精神。
尤為關鍵的是,基于環保稅的地方稅屬性,環保稅法授權省級政府根據本地實際需要,可以在法定稅額標準基礎上,上浮應稅污染物的適用稅額。但為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超征逐利的沖動,環保稅法同時設定了上浮不得超過10倍的上限,并明確要求省級政府提出的調整方案,報同級人大常委會決定,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換言之,環保稅的靈活調整,并不能由地方政府自行拍板,而是必須經過地方立法程序,并接受國家立法機關的監督,由此堅守的,正是稅收法定的底線原則。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15年調整后的立法規劃,增值稅法、資源稅法、房地產稅法、關稅法、船舶噸稅法、耕地占用稅法等多部稅法已被列入立法路線圖,立法機關還確定了于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立法時間表。在此背景下,率先出臺的環保稅法,及其處處忠于稅收法定原則的制度設計,無疑將對未來的稅收立法提供樣板價值、發揮示范效應,從而以一法先行,深刻影響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立法全局。
民法總則,啟動“權利法典”倒計時
清點2016年的立法進展,除了已經結出的立法碩果,電子商務法等新法律草案,水污染防治法等修法草案,亦已紛紛進入審議程序,這些正在路上的立法努力,已為未來的立法圖景埋下了伏筆。其中最為激蕩人心的,當數民法典編纂的重新出發和民法總則的立法先行。
有著“權利法典”之稱的民法典,乃是社會生活的圣經、私權保護的屏障、市場經濟的基石。然而這一現代法制不可或缺的標志,也是國人孜孜以求、多年難圓的夢想。在六十多年的時光流轉中,我國曾先后5次發起制訂民法或編纂民法典的努力,卻屢屢受挫,留下了立法史上最為坎坷的命運軌跡。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新一輪編纂民法典的努力,承載著穿越歷史三峽的艱巨使命。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役,就是民法總則的制訂。
按照立法機關確定的“兩步走”戰略,在整個民法典中擔當統率和綱領作用的民法總則,擬于2017年3月率先完成立法,成為其總則編。其后將展開各分編的編纂,最終于2020年形成統一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總則作為開篇布局之作,是決定民法典編纂成敗的關鍵所在。
從2016年6月法律草案進入審議程序后,民法總則便牽動了全社會的人心,成為舉國關注、升溫不止的熱點。諸多立法設計和創新在贏得普遍贊譽的同時,也激起了巨大的爭議聲浪。從6月到12月,民法總則草案以緊鑼密鼓的節奏,先后接受了三次審議,努力凝聚社會共識、回應立法爭議,向更加完善的方向不斷演進。
盡管仍在路上,但民法總則的立法啟航和全速前行,無疑是2016年最重大的立法事件。而民法總則的指日可待,事實上也啟動了民法典這一“權利法典”的倒計時。可以預見,由民法總則一馬當先的民法典編纂,將以史無前例、浩大精致的法律語言,總結改革成果、表達時代精神、抒寫公民權利、捍衛社會公正。最終成為深度構建現代法制的標桿,并由此開啟一個嶄新的權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