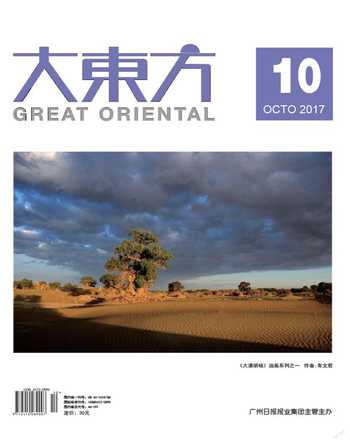日本主流報紙對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報道研究
李玨
摘要: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是關系到中日歷史問題的特殊事件,日本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尤為引人注目。本文聚焦大閱兵舉行期間《朝日新聞》的相關報道,并嘗試從報道數量、報道角度、報道手法、新聞語言四個方面對其進行深入剖析,力求在把握報道數量、特點的基礎之上,管窺日本主流媒體、日本政府對待侵略史及中日關系的真實態度。
關鍵詞: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 《朝日新聞》 日本主流媒體
一、引言
歷史問題是影響中日兩國相互形象的重要因素,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中日關系的發展。2013年1月,日本自民黨贏得了大選,日本保守右傾勢力代言人安倍晉三再次成為日本新一任首相。在歷史問題上,安倍及其右翼政治盟友長期質疑甚至企圖篡改侵略史。另一方面,安倍晉三上臺后通過各種手段不斷滲透、控制日本主要媒體,進行右翼宣傳。
正是在中日兩國間歷史問題之爭升級、安倍政府操控日本媒體肆無忌憚地對中國進行歪曲報道這一特殊時代背景下,中國舉行了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這一慶祝活動不僅受到了國內民眾和媒體的廣泛關注,還吸引了海外媒體的目光。其中,關于閱兵目的之一是“震懾日本”的說法尤其引發了日本輿論的熱議。同一場閱兵儀式,不同的海外媒體有著不同角度的解讀,有的看到了展示成就、有的看到了追求和平、有的看到了裁軍30萬……作為“當事人”——日本媒體是如何看待和報道此次活動的?通過報道此次活動日本媒體希望在日本民眾心中構建一個怎樣的“中國形象”?以“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視和平、開創未來”為目的舉行的大閱兵最后是以怎樣的面貌出現在日本公眾視線中的?……這些問題尤為引人注目,亦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選取在日本民眾中頗具輿論影響力的《朝日新聞》為研究對象,以內容分析法為基礎,針對其中與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相關的報道展開定量、定性研究。力求在把握報道數量、特點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對其新聞語言進行剖析,管窺日本政府對待侵略史及中日關系的真實態度,揭示出新聞報道背后的意識形態的影響。
二、大閱兵期間《朝日新聞》對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特點分析
2015日1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招待會上首次正式回應媒體提問時表示:“中國同有關國家一道舉辦相關紀念活動,正是為了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同日24時,《朝日新聞》上即刊登了第一篇有關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題為《抗戰勝利70周年 計劃在北京舉行閱兵式?》。在隨后的一年中,《朝日新聞》對大閱兵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并進行了追蹤報道。其中以大閱兵舉行期間(9月1日至9月7日)報道量最為密集。因此,本文主要選取這一期間《朝日新聞》的有關報道為研究對象,對其內容進行剖析,從而探究在中日歷史相關問題上日本主流媒體的報道特點和趨勢。
(1)報道數量
本文的調查對象為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舉行前后一周,即2015年9月1日至9月7日《朝日新聞》對大閱兵的報道。以“中國”、“戰勝”、“大閱兵”為關鍵詞對這一期間的朝日新聞電子版[朝日新聞電子版: 進行檢索,共搜索到與大閱兵直接相關的報道22篇,其中9月1日1篇、9月2日2篇、9月3日5篇、9月4日8篇、9月5日3篇、9月6日2篇、9月7日1篇。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朝日新聞》在大閱兵舉行前、中、后各時期持續關注了此次活動,并在大閱兵舉行當日及次日進行了集中報道。短短數日,同一媒體對同一事件的報道量突破了20篇,日最高報道量達8篇,其報道時間及數量在充分體現新聞的“時效性”原則的同時,也反映出了日本媒體對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關注程度。
(2)報道角度
不同媒體對同一新聞事件往往有著不同的關注點。通過對相關報道的梳理、分析可知,《朝日新聞》對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大閱兵舉行之目的:9月1日,題為《當今的日本 不是目標 中國駐日大使抗戰勝利慶典巡禮》一文刊載了程永華大使關于大閱兵目的的一段發言:“閱兵式針對的并非是現如今的日本”、“中國舉行此次慶祝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珍視和平、開創未來”;而9月4日,題為《“戰勝·中國” 硬軟的演出 大閱兵 軍事炫耀 裁軍30萬人表明》的報道對于大閱兵的目的則作了如下分析:“習近平主席在大閱兵后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忘卻侵略史就是背叛,是對人類良知的侮辱。據此推斷,舉行大閱兵確有牽制日本之嫌。”;(2).出席大閱兵的外國領導人陣容:有多少國家元首、代表將出席中國舉辦的抗戰勝利70周年大會?這似乎一直都是日本媒體關注的焦點。9月3日,題為《中國表明裁軍30萬人 抗戰勝利70周年‘不稱霸》中是如是描述出席大閱兵的外國領導人陣容的:“出席閱兵式的有包括俄羅斯總統普金、韓國總統樸槿惠、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內的49個國家及11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其中派遣首腦級代表的僅為20多國,且以亞非國家為主。英法兩國只派遣了部長級官員或首相特使,美國、德國、歐盟也唯有駐中國大使參加。”;(3).關于 “裁軍30萬人”: 習近平主席在大閱兵后發表了演說,相對于演說中的其他內容,最受《朝日新聞》關注的是“裁軍30萬人”這一點。對于這一舉措,《朝日新聞》認為其目的是“為了平息現階段國際社會盛傳的‘中國威脅論”(9月3日),并稱“即使裁軍,也無法改變中國擁有全世界人數最多兵力這一事實,加強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是既定路線,中國在軍備擴張的道路上鮮有要剎車的跡象”,“中國國防部強調,在削減兵力的同時,會繼續推進軍隊改革,并維持適當額度的國防費用”(9月4日);(4).中國的社會問題(空氣、反恐)及中國普通民眾對閱兵式的看法:9月2日,《朝日新聞》刊登的題為《臨近紀念典禮 北京戒嚴 動員85萬市民參與反恐》的報道中寫道:“9月3日將迎來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北京市籠罩在緊張感交織著節慶感的獨特氣氛之中”,“為了解決令人擔憂的大氣污染問題,中國似乎是賭上了國家尊嚴 ”,“政府擔心閱兵式當日空氣質量,從8月20日開始實行交通單雙號管制,北京及周邊,甚至山東、山西省的部分工廠、建筑工地也被勒令停工”,“反恐防范工作也是史無前例的森嚴”,“長安街沿線增設了大量監控攝像頭,除了警察和武警以外,還動員85萬市民成立了‘安全保障志愿者隊”。同文亦指出“北京市中心商業設施停業、醫院停診,對市民日常生活影響較大。
整體而言,《朝日新聞》對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中負面報道較多。22篇報道中消極性內容的有20篇,占據了總數的90.9%;報道內容較為客觀中立的僅為2篇,占9.1%;此外,沒有正面報道大閱兵的文章。
(3)報道手法
《朝日新聞》對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在其報道方式上有三大特點。
①借他人之口來發聲和評價。例如,《朝日新聞》的報道中大量運用了對匿名群眾的采訪,尤其是中國民眾對于閱兵式的看法。從其選取的民眾發言的內容來看,絕大多數為負面評價,正面評價僅有一人。這部分所謂的“中國市民”是否真實存在亦或是子虛烏有,無從考證。但可以確認的是其言論的確會幫助《朝日新聞》實現其報道目的,從而影響日本受眾的判斷。
②與其他國家或其他時期的類似活動作比較。《朝日新聞》將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與2005年在俄羅斯舉行的抗戰勝利慶典活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進行了比較。與他國赤裸裸的比較也好,對歷史的溫情回顧也罷,《朝日新聞》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報道方式無非是想要迂回地表達對中國舉辦的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否定,質疑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認可度。
③重點內容反復報道。《朝日新聞》還于9月3日、9月5日、9月6日、9月7日連續發文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出席此次紀念活動表示不滿。日本方面強調“聯合國必須重視中立性”,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對于“聯合國秘書長出席被冠以‘抗日戰爭勝利之名的閱兵式深感遺憾,并表示抗議”,也將以此舉有失公平為由向聯合國致函表示抗議。《朝日新聞》力圖通過這種“轟炸式”的報道方式來達到強化自身立場,加大對日本讀者影響之目的。
⑷新聞語言
語言并不像以往科學家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客觀透明的中立傳播媒介。[1]新聞語言中往往隱藏著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媒體的政治意圖。《朝日新聞》對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在其語言上也頗下功夫。
首先,在措辭上多用貶義詞或中性偏貶義的詞。例如日語中的“狙い”和“目的”都具有“目標、目的”之意,在許多場合下可以通用。但深究兩者的含義可知,“狙い”的詞源為動詞“狙う(伺機、瞄準)”,有“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計劃、野心”之語感;與之相對地,日語“目的”單純表示“目的”,且這種目標、目的往往是比較“表面的、直接的、純粹的”。而《朝日新聞》在所有涉及中國方面“目的、目標”的語句中都使用了“狙い”一詞。例如:“日本を牽制する狙いがあるとみられる。(此舉目的在于牽制日本。)”“米軍のアジア戦略に対抗する軍事力を誇示する狙いがあるとみられる。(目的是炫耀軍事力量,對抗美軍的亞洲戰略。)”“國內では國民の愛國心を訴え、勝利を導いた共産黨の求心力を強めることを狙っている(在中國國內倡導國民要具有愛國心,其目的是增強將戰爭導向勝利的共產黨的凝聚力)”。同樣地,在描述閱兵式上出現的新型武器裝備時,《朝日新聞》也選擇了帶有負面評價意味的“軍事力誇示(炫耀軍事實力、秀‘肌肉)”而不用意思更為中性的“軍事力展示(展示軍事實力)”。這些本身帶有否定“色彩”的詞語協助《朝日新聞》實現了其報道意圖。
其次,使用主觀性較強的語言表達形式。新聞報道總是力求接近事件真相,因此其語言也以客觀、準確為宜。但是在《朝日新聞》對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中卻出現了一系列主觀性較強的表述。例如,《朝日新聞》用以下這段話描述了韓國總統樸槿惠觀看閱兵式時的心境:“樸大統領が軍事パレートで過度に笑ったり、手を振ったりしている映像が伝えられると中國の軍事力をたたえているかのような誤解をあたるおそれもある。(樸槿惠總統唯恐在閱兵式上過度微笑、揮手的視頻被播出后會造成一種誤解——她似乎在對中國的軍事力量表示贊許。)”上述文字只不過是《朝日新聞》單方面的主觀推測,因為缺乏強有力的證據,只能通過“唯恐”、“似乎”等言辭來表述。這些看似站不住腳的主觀判斷,事實上仍能影響一部分受眾,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朝日新聞》的報道意圖——凸顯樸槿惠的“進退兩難”。
最后,《朝日新聞》還在報道中運用了大量敏感、偏激的詞匯。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每次提及 “大陸間彈道導彈(ICBM)”等新型武器,文章總會冠以諸如“米本土を攻撃可能(能夠攻擊到美國本土的)”、“米の活動を無力化できる(能夠使美軍活動失效的)”、“米狙える(能夠瞄準美國的)”、“米ににらむ(緊盯美國的)”、“日本をすっぽりカバーできる(能徹底覆蓋日本領土的)”等定語,從而將武器展示與威懾日美聯系在一起,造成日本讀者的不滿與恐慌;對于“DF16”、“DF26”導彈的亮相《朝日新聞》更是連用了兩個“拒否(拒絕)”,認為中國制造這些導彈是為了增強軍隊 “アクセス拒否(拒絕出入)、領域拒否(拒絕侵犯)”之能力,“不讓周邊國家接近”。兩個“拒否(拒絕)”映射出的是中國對待鄰邦的態度;《朝日新聞》還將中國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稱作是“戦勝外交(戰勝國外交)”、“歴史外交(歷史外交)”,暗示中國政府有借抗戰勝利之名謀求外交利益之嫌;此外、“覇権(霸權)”、“脅威論(威脅論)”、“反日(反日)”等詞也頻頻出現在報道之中,影響著廣大日本受眾的觀感與判斷。
三、透過《朝日新聞》的報道看日本主流紙媒對待侵略史、中日關系的態度以及對中國形象的塑造
雖然中國方面一再強調日本不是此次閱兵式的針對對象,但作為日本媒體,《朝日新聞》的報道還是不可避免地將“大閱兵”與“反日”聯系在了一起。從其報道角度、報道手法、新聞語言來看,《朝日新聞》試圖將大閱兵以“牽制日本”、“炫耀軍事”、“沒有獲得國際社會全面支持”之形式呈現在其讀者眼前;并竭力在廣大日本民眾心目中勾畫出一個“社會秩序紊亂”、“人權受到壓制”、“國民素質底下”、 “環境污染嚴重”、 “民眾對日本懷有敵意”、“其崛起后必將對美日及周邊國家造成威脅”……的中國形象。《朝日新聞》的報道中看不到絲毫與日本侵略歷史相關的信息,更看不到其作為日本主流媒體對侵略史的反省和歷史責任感。至于中日關系,除卻在9月1日發表的《當今的日本 不是目標 中國駐日大使抗戰勝利慶典巡禮》中引用了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為了和平,日中兩國必須攜手共進”以外,再也聽不到任何中日友好的呼聲。
四、結語:
《朝日新聞》曾被認為是日本全國性報紙中中國問題報道量最大、報道范圍最廣、報道立場相對比較客觀的報紙[2]。然而透過其對中國抗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不難發現,《朝日新聞》的報道基調正逐漸發生著變化。究其原因,《朝日新聞》的這一轉變與日本國內其他媒體掀起的所謂的“打擊朝日新聞”、“擊垮朝日新聞”運動以及2014年初安倍點名批評《朝日新聞》事件有著密切的關聯。正如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所言,被譽為日本“左派之王”、以“不偏不黨”為辦報宗旨的《朝日新聞》的轉變也預示著:“日本戰后的媒體界、言論界左右兩派對立的格局中,過去‘左派占優的狀況變成了‘右派占優勢的局面”。
另一方面,《朝日新聞》的妥協亦對中國有關部門今后的對日宣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勢下,如何有效地與日溝通、對日宣傳,如何改善日本主流媒體中的中國形象,進而將中日關系引領回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是擺在每一個中國媒體人面前的課題。
參考文獻:
[1] 陳中竺.批評語言學述評[J].外國教學與研究,1995(1):21—27.
[2] 劉林利.日本大眾媒體中的中國形象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