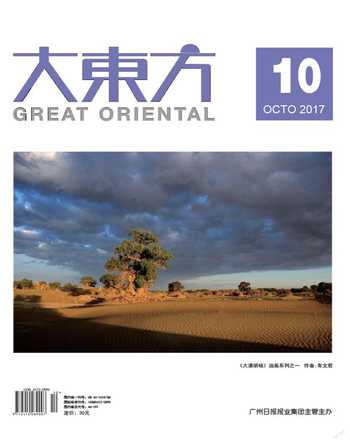從《奇幻森林》看電影如何重構文學經典
崔婷婷 于中華
摘要:2016年上映的《奇幻森林》由喬恩·費儒執導,改編自魯德亞德·吉卜林的小說《叢林之書》,影片借助強大的CG特效、眾星云集的配音及扎實的改編內容,生動再現了“狼孩”莫格里同叢林動物之間的愛恨情仇。該部電影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導演喬恩獨具匠心的情節安排、對原著主題內涵的重新解讀、對主人公同動物關系的精準拿捏,以及運用現代科技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完美呈現。
關鍵詞:《奇幻森林》;文學原著; CG特效;人與自然
電影和文學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彼此相互促進,文學是電影的基礎與源泉,電影是文學的拓展與深化。依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往往具有更廣闊的受眾范圍和更濃厚的藝術特色,一方面電影導演常常借用多種拍攝手段和技巧,將小說的情節和主題生動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另一方面敘述視角和結構的重構更能反映導演自身的藝術底蘊。喬恩·費儒作為近些年美國大熱的商業片導演,不僅對電影特效技術了解甚多,而且對當代的熱點話題—人與生態的關系把握準確。本文從影片的主題和技術兩大方面探討《奇幻森林》如何重構文學經典。
1.主題內涵的此消彼長
(1)隱退殖民色彩,強調生態和諧。小說作者吉卜林在文學評論界以“帝國號手”著稱,他的殖民思想體現在其各種體裁的作品中,《叢林之書》也不例外。由狼撫養長大的莫格里,雖具有動物的習性,但卻繼承著人類的特質,他借助自己的智慧,逐漸成為叢林中的統治者。在《叢林之書》中,吉卜林將狼孩描述為一個具有先天種族優勢的強者。“林動物是吉卜林筆下的低等民眾的化身,而他眼中的高等人物自然就是人類。在“狼孩”故事中,莫格里敢于接觸叢林動物不敢接近的紅花,而其他動物發現自己不敢直視莫格里的眼睛。通過描述這兩點,吉卜林把以莫格里為代表的人類放在高等民眾的位置,以供低等階層仰視”。動物本能地對莫格里的排斥和忌憚反映了印度土著民對英國白人殖民者恐懼又憎恨的心理。
電影《奇幻森林》則有意將小說中暗含的殖民色彩除去。這是因為“文學文本在改編成電影時,由于改編者與原著所處的時代、社會和歷史背景不同,改編者會對原著做一定的修改,使其更適應改編者身處的社會環境,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觀眾,變現改編者及其所在社會的意識形態觀”。電影于2016年上映,此時印度已擺脫了殖民地的身份。這部作品被搬到熒幕后,欲擴大其受眾范圍,電影主題更應與時代接軌,所以編劇和導演有意淡化殖民主義色彩。電影突出人與動物如何消除彼此的偏見。
(2)淡化身份焦慮,突出成長危機。翻開《叢林之書》,讀者可以感受到主人公在身份認同過程中產生的焦慮:狼群在老虎謝爾·可汗的煽動下將莫格里逐出叢林。回到人類村莊的他同樣也被村民視為妖怪。莫格里由此進入兩難境地,陷入迷惘之中。這正如作者吉卜林本人,雖然他喜愛印度,但卻因其白人身份,不得不回到英國。但在電影中,導演將該身份焦慮問題進行了弱化,有意突出了其在成長過程中如何應對人類自身人性與動物性的對立與統一,如何借助身邊的動物伙伴或敵人解決成長危機,實現自我認知。
(3)人性與動物性的矛盾運動。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強調在一定條件下,主人會具有奴隸的特征,而奴隸卻具有主人的性質,這種相互變化要在具有他者的情況下才能完成,也就是說必須有他者的存在,我們才能認識自己。在莫格里的成長過程中,其身邊的動物就扮演著他者的角色,幫他完成自我認知。
狼爸媽扮演著莫格里父母的角色,給予他溫暖和關愛;黑豹巴希拉和棕熊巴魯是人生導師,教導他“叢林法則”。而巴魯更代表著民主、自由、正義感十足。這些正面形象,是莫格里成長過程中的推力,而電影中的諸多反面形象雖為其人生路上的阻力,卻具有更深層次的隱喻意義,在其健全人格過程中最是功不可沒。首先巖蟒卡奧的出現預示著人生道路上不可避免要遇到的誘惑,通過它,莫格里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但充卡奧滿魅惑的聲音讓莫格里暫時迷失了方向,幸虧巴魯將他從中喚醒。巨猿路易王是莫格里的第二個成長危機,它是電影中新增的角色,這個具有夸張形體的猩猩,象征人類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欲望。主人公的勁敵老虎謝爾·可汗,象征著恐懼。人生道路上的恐懼猶如電影中的老虎,它邪惡、強大又無處不在,但只要我們不懈奮斗,那么恐懼,我們終將戰而勝之。“文化的使命以及對人性的弘揚并非是對動物性的徹底摒除,而是要保留人性中的動物記憶,實現人性和動物性的生態共生。要顛覆人性/動物性的二元對立,更提醒人類要實現動物的多元存在,因為人性本質上包含了被人類話語排斥在外的動物性身份,人性的本真存在應當回歸人作為動物的多元存在”。借助《奇幻森林》,導演展示了他對人性和動物性本質的深刻思考,強調動物作為他者的重要作用,表達了他對動物的倫理關懷及其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正如汪民安在《人、自然和動物》一文中所寫:“在我們現代社會,人如果和人很難建立關系,丈夫和妻子很難相互理解,家長和孩子、朋友和朋友很難共同理解,那我們去理解誰呢?我們去認知誰呢?或者說,我們通過誰來自我認知呢?這個時候動物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據了很重要的位置”。
2.重構文學經典的視聽效果
(2)CG特效下的視覺表現。《奇幻森林》采用了好萊塢科幻、魔幻大片中倍受青睞的CG特效技術。CG特效的運用是指影片本身在真實場景中拍攝并由真人表演為主,同時穿插應用大量虛擬場景及特效。通常的手法是在傳統電影中應用CG技術增加虛擬場景、角色、事物、特效等對象,以達到真假難辨,增強視覺效果的目的。而我們今天要提到的CG電影是指整部電影中所有的視覺產物,全部由計算機生成的CG動畫或CG圖片所構成的影片。電影《奇幻森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這種視覺效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搬演至銀幕上,其視覺效果的重要性已遠超內容本身。這部電影在拍攝過程中,一直是一個小男孩自己在表演,而全部的叢林世界和動物形象,均由電腦CG打造而成,為觀眾呈現了栩栩如生的叢林猛獸和奇幻的森林世界。技術人員對黑熊、棕熊和狼的動態捕捉,尤其是行走、奔跑和搏斗的動畫都渲染的非常到位,整個叢林場景,大到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小到雨滴打在一只青蛙頭頂上的水花,都令人過目不忘,達到了以假亂真的效果。
一部電影的成功離不開對每一個細節的處理。燈光的使用往往在電影中具有微妙的作用,影片中莫格里解救小象時燈光的安排最為獨具匠心,而這段人象情緣,導演在電影開始時便做了預設:當莫格里第一次遇到象群,向這些森林之神行跪拜禮時,走過莫格里身邊的小象別具深意地回頭望向莫格里。而在影片結尾,這只小象不幸陷入深坑,莫格里用他的智慧救出小象,本是黑壓壓的天空突然變得光芒四射,而這光正好籠罩在莫格里頭頂,此時他騎在大象身上,宛若一位帶有智者光環的神明,這光環一方面象征著他的智慧,一方面代表他被叢林之神大象所接受,同時也預示著他與其他動物和諧共存的場景即將到來。
(2)配音和背景音樂的聽覺盛宴。在電影的配音方面,電影采用的是超豪華明星陣容。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克里斯托弗-沃肯為猩猩路易王配音;女星斯嘉麗-約翰遜為巖蟒卡奧配音;奧斯卡最佳女配角露皮塔-尼永奧為狼媽媽配音;奧斯卡影帝本-金斯利為黑豹巴西拉配音;喜劇老戲骨比爾-默瑞為棕熊巴魯配音;伊德瑞斯·艾爾巴為老虎謝利·可汗配音;吉安卡洛·埃斯珀西多為狼爸爸阿克拉配音。這些大牌明星為片中的動物角色傾力獻聲,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這部電影的關注度和吸引力,這也是電影成功的原因之一。尤其需要指出,電影中選擇女性為巖蟒配音,一改原著小說中巖蟒的男性角色,拓展了“誘惑”的內涵邊界,從而使巖蟒這一形象更加生動可感。
在音樂應用方面這部電影改變了吉卜林原著的陰郁基調。同樣是講述印度森林中一個被狼群養大的孩子莫格里的叢林冒險之旅,電影的獨特之處在于其穿插了莫格里在叢林之旅中和動物相處時所表演的風格不同的歌舞。比如,影片呈現莫格里和巴魯在河邊嬉戲打的場景時,播放了《生活必需品》,歡快的節奏襯托出人與動物相處時的和諧愉快場面;在巖蟒卡奧講述莫格里的身世及其與老虎的恩怨時,卡奧演唱了《相信我》,其誘惑嗓音將主人公置于危險之中,帶動了觀眾的緊張情緒。此外,當巨猿路易王引誘莫格里說出“紅花”的秘密時,路易王演唱了《我想變成你》,這首歌將它的野心呈現在觀眾面前。音樂的使用不僅讓這些活靈活現的動物形象躍然于屏幕之上,而且有利地渲染了氣氛,推動了影片情節的有序發展。
一部經典文學作品的價值有賴于它能否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社會語境下被重新闡釋,喬恩·費儒勇敢地打破常規,摒棄先前探討殖民主義和身份危機的陳詞濫調,融合當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挖掘《叢林之書》中潛在的生態思想,通過展示主人公成長過程中人性與動物性的對立和統一,突出動物對于人類自我認知的重要作用,進而將人與動物置于平等的地位,啟發觀影人關懷動物。同時為了從視覺和聽覺上符合觀眾的審美需求,創作者運用強大的3D特效和精心制作的背景音樂,增強影片的藝術表現力,將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完美畫卷呈現在屏幕之上,不僅滿足了受眾口味,而且利于觀影人領略原著中與時俱進的思想魅力。因此,電影改編應當是對原作有價值的反思和評論,同時也要求改編者批判地看待“改編忠實論”,創造性地將文學經典置于新的物質和文化環境下,文字小說和電影相輔相成,共同促進彼此的長足發展。
參考文獻:
[1]鄺增乾,劉玉紅.吉卜林“狼孩”故事中老虎角色的構建與隱喻[J].雞西大學學報,2015(1):116.
[2]張沖.《文本與視覺的互動:英美文學電影改編的理論與應用》[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143.
[3]丁林棚.論《羚羊與秧雞》中人性與動物性的共生思想[J].當代外國文學,2014(2):111.
[4]汪民安.人、自然和動物[J].外國文學,2008(07):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