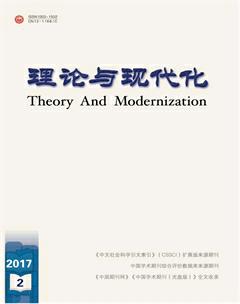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挑戰與應對
孫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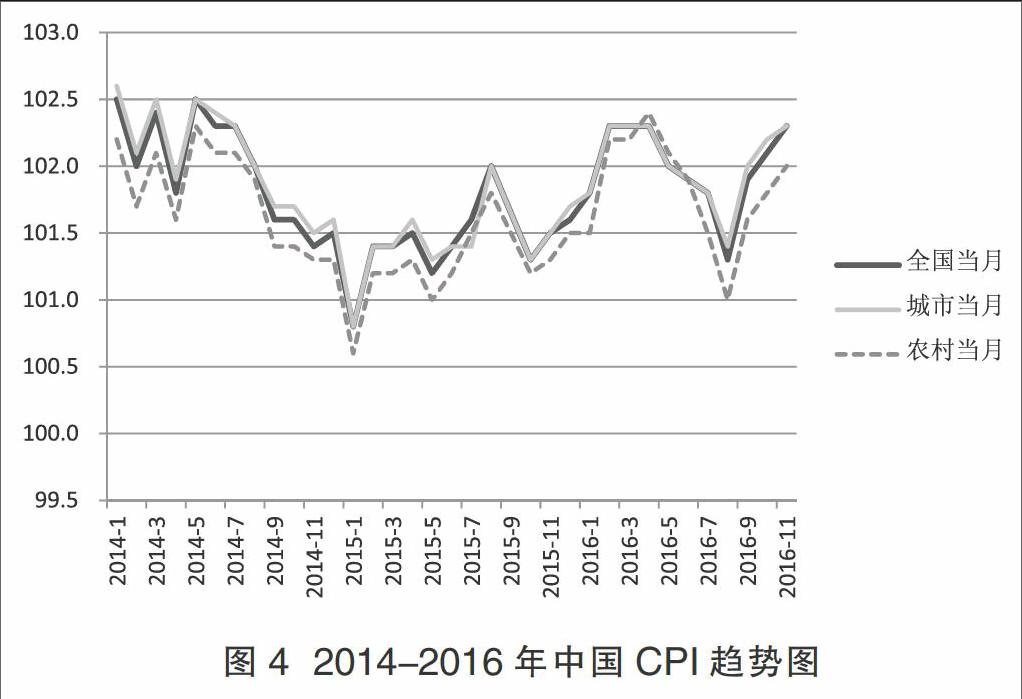

摘 要: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多元性”和“靈活性”特點的理論分析,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一年來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實際,探討進一步深入推進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重點及具體措施。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多元性;靈活性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7)02-0010-07
“十二五”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總結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九個方面的“趨勢性變化”,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進行了鋪墊性分析。2015年,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和“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表重要講話。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新的闡述,并提出了“深入推進”的具體要求。不難發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濟理念既有“一貫性”的堅守,也有“創新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本文通過回答三個問題,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一年以來,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哪些新的變化?怎樣深入推進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將“老內容”和“新提法”融會貫通,化解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具體矛盾?從而挖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多元性”和“靈活性”特點,進一步深入理解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科學內涵和政策外延,以破解“重大結構性失衡”的中國經濟發展難題。
一、供給管理的理論基礎
對于供給管理現有文獻主要從短期和長期兩個維度展開相關研究。短期供給理論主要針對如何維持短時期經濟穩定問題基于供給側視角展開討論。薩伊(J.M.Keynes,1803)提出,“賣就是買”,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并維持供給和需求間平衡關系,這就是“薩伊定理”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的核心內容[1]。“薩伊定理”成為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以“放任自由”與“不干預”為特征經濟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大蕭條,使得古典自由主義理念指引下的供給管理受到質疑,而基于“凱恩斯定律”的需求管理成為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廣泛采用的政策手段。20世紀70年代初期,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發生“滯脹”現象,為解決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的“雙高”難題,以拉弗(A.Laffer)、吉爾德(G.Gilder)和萬尼斯基(J.Wanniski)為代表的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重新得到重視,其后以此為理論依據的“里根經濟學”經濟政策在調控通脹率和經濟增長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從長期供給管理看,盡管相關文獻很少有長期供給管理的明確提法,但其中關于長期經濟增長源泉的論述無疑應當歸屬于供給學派[2]。關于長期經濟增長源泉即供給側因素包括:勞動分工和物質資本(Smith,1776)[3];創新(Schumpeter,1912)[4];物質資本積累以及體現在物質資本上的技術進步(Harrod,1939)[5];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Solow,1956)[6];人力資本(Schultz,1961)[7]和經濟制度(Gruchy,1985[8];Gregory,1988[9])等。供給管理理論認為,由于價格機制具有自動調節作用,所以短期內的供給和需求可能失衡,從長期看二者卻能夠實現動態平衡。進一步地,長期供給管理更適用于實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而短期供給管理不管在實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還是在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則同樣適用。
綜上所述,我們從短、長期供給管理的發展脈絡和演變過程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時間上的“雙維性”。供給管理可以分為短期和長期兩個維度,其管理和政策手段的側重點各有所長,短期力在“穩”,長期重在“進”,供給管理只有兩條腿走路,才能“穩中有進”,實現持續性經濟增長。所以,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做短期計劃,又要制定長期戰略,既要打好“持久戰”,又要做到“有的放矢”、“重點殲滅”。
二是要釋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靈活性。從短期維度視角出發,無論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說還是供給學派理論,無論是“里根經濟學”政策范例還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實踐。供給學派有著類似的理論重點(從供給方維持經濟穩定)和政策目標(解決供給和需求短期內失衡問題),但是也不難看出,它們賴以存在的環境和擬解決的問題卻存在著明顯的時代和國別烙印。任何一種理論都不可能脫離實際,也不是完美和萬能的靈丹妙藥,所以全盤照搬已有理論來指導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拿來主義”做法必不可取,有時要“摸著石頭過河”,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充分發揮其靈活性特性。
三是要關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多元性。從長期維度視角看,長期供給管理理論所提及的經濟增長源泉,即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創新、人力資本、經濟制度等無一不是我們今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所在,從而體現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多元性特性。
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結合需求管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之間不存在一方必然取代另一方的變化趨勢,問題的關鍵是哪種管理可以更好地解決特定國家、特定時期的特定問題。因此,政府應當從“新常態”實際出發選擇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政府不論是采取需求管理的手段還是供給管理的手段,都不能只關注這些手段對目前的需求和供給的影響,還要評估這個手段對將來需求和供給的影響,以確定它是否有助于解決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而不會在未來導致新的經濟問題。
二、為什么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按照問題導向和習近平總書記的分析思路,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是根源在于“重大結構性失衡”,即經濟結構失衡、體制結構失衡和治理結構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