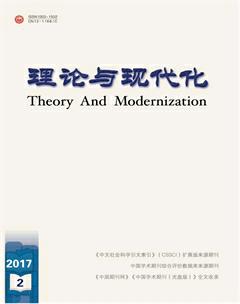由“仁”與“質”“文”之關系再探“文質之辨”
陳洪杏+劉娜
摘 要:“文質之辨”涉及“人”與“文”的張力,乃涵攝《論語》全書精義的又一重大分辨。文章結合“仁”與“質”“文”的關系,從理想的君子人格的養成和良善社會風尚的培壅兩個角度,再度探詢了“文質彬彬”的確切內涵、致取之途。一方面,就理想的君子人格的養成來說,所謂“彬彬”,意味著每個人身上“仁”的端倪(“質”)經由種種人為之“文”的潤澤而達到相當高卓的境界(“文”“質”互成而至無過不及);另一方面,就社會文化風尚的培壅來說,所謂“彬彬”,則是意味著百姓身上那點“仁”心(“質”)受到為政者的種種引導和教化這一“文”的熏陶,結果社會風氣的良善臻于醇化(“文”“質”互成而至無過不及)。
關鍵詞: 君子人格;社會風尚;文質之辨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7)02-0060-07
“文質之辨”關乎理想的君子人格和社會文化的培壅,涉及“人”與“文”的張力,乃涵攝《論語》全書精義的又一重大分辨。不過近代以來有代表性的注疏大多僅注意到“文質彬彬”與君子的關聯,至于文質彬彬的確切內涵、致取之途及與社會風尚的關系則屬意未深。這里擬由反省這段注疏史以對這一分辨再作探究。
一、“君子”說、“歷史嬗替”說、“仁”說
劉向《說苑》記載了一則饒有興味的故事,其謂:“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儒道兩家通而不同的致“道”宗旨趣味,從這個小故事可見一斑。孔子重“質”,孔子亦悅“文”,其所欲造就的是質美文盛的君子。“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這是《論語》里眾多談文、談質之章句的眼目。
何晏采包咸之解注此章謂:“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朱子承襲此說并引楊時語謂:“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余,補不足,至于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于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近代以來的注家多從,如康有為、簡朝亮、王恩洋、蔣伯潛、徐英、錢穆、朱維煥、黃吉村等。這一見解專就“君子”之德的培育而發,所論不無道理,只是“文質相半”、“物相雜而適均”諸語尚淺。
與包氏、朱子有別,清代公羊學巨擘劉逢祿注稱:“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蔽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春秋》救周之敝,當復返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 劉氏此說承自東漢大儒何休《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所注,其謂:“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蔽,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蔽,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于質。” 劉氏之后,宋翔鳳指出:“禮有文有質,謂之備。勝文勝質,謂之不備。文質不因勢利導,謂之不當。文質彬彬,君子之體,謂之由禮。” 戴望融通以上諸說,謂:“質,質性;文,儀貌。質由中出,文自外作。野人多直情徑行,不為儀貌。史,祝史也,唯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君子貴文質得中。彬彬,雜半貌。禮所以有質家文家者,為王者起,有所改制,順天地之道。……三王之道,若循環,非有所舉,有所遺也。夏教尚忠而文,文家尊尊,尊尊之過,流而為史。殷救之以質,質家親親,親親之過,流而為野,周復救之以文。然而原其始制,主質者有文,主文者有質,三代之初皆彬彬君子也。《春秋》救周之敝,將變周文以從殷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乘殷之路,尚質也;服周之冕,貴文也。” 此外王闿運亦持相近說法。 撇開公羊學“三世”、“三統”說的背景,這一詮說亦可謂將歷史嬗替的秘密歸之于“文質相復”。此見理境恢宏,視閾遼遠,“原其始制,主質者有文,主文者有質,三代之初皆彬彬君子”諸語尤其耐人咀嚼。
不過,以上二說皆未觸及“文質彬彬”的底蘊。《禮記·中庸》謂:“仁者,人也。”《孟子》謂:“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而孔子亦稱:“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見《孟子·離婁上》)又謂:“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同上)。這些把“仁”、“人”(“君子”乃“人”之典型)、“道”有機聯結起來的說法是意味深長的。在近代以來的注家中開始將“文質之辨”置于“仁”道燭照之下的,首推黃克劍和王邦雄等人。王氏等分析道:“殷尚質,周尚文,周文隳敗,有文而無質,故孔夫子是以殷為質,救周之文。孔子以為‘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是文勝質,是很少有真實的情意的,孔子又說:‘剛毅木訥近仁,剛毅木訥是質勝文,是較切近仁本來的樸質。孔子反省周文‘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是文,仁則是禮樂之文的實質了。仁心發用,落在禮上實踐,就是文質彬彬,才能成就君子的人格德行,孔子‘吾從周,僅就‘文講,重振周文,就當復活它的精神實質。……這一實質,也不是道家的自然樸質,而是做為道德根源的仁心,是真切的道德情感。” 這里“仁心發用,落在禮上實踐,就是文質彬彬”的說法,以及將“質”把握為“道德根源的仁心”、“真切的道德情感”的見解,都頗具慧識。但“文質彬彬”契于“仁”道的閟機,仍有待進一步抉示。黃克劍指出:
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既同“質”關聯著,也同“文”關聯著。就“仁”在人稟受于天的自然性情(“天命之謂性”)中有其根柢而言,這根柢構成“仁”——使人成其為人——的“質”或質地,但就這根柢畢竟只是“仁”的端倪,一如后來孟子所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言,“仁”成其為“仁”還須從其根柢或端倪處予以擴充和提升,這擴充和提升則在于相應于“質”的人為之“文”。人在“文質彬彬”(“文”與“質”相配稱、兼相成)中得以成全為君子,而使人成其為人的“仁”也在“文質彬彬”中得以成全為“仁”。
“仁”被領悟為“既同‘質關聯著,也同‘文關聯著”,致“仁”被進而闡釋為必得經由“文質彬彬”之途,此時,“文質彬彬”的深義便可謂獲得了真切的抉發,與之相隨,被明確地提出來的還有由“仁”而“圣”的道路。下文便嘗試依循黃氏的指點,結合“仁”與“質”、“文”的關系,分別從君子人格的養成、社會風尚的淳化兩方面對“文質彬彬”再作尋究。
二、從君子人格的養成看“文質彬彬”
周朝末期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對此歷史上曾有三位人物先后以“文敝”或“文弊”概括,如司馬遷謂:“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史記·高祖本紀》)韓愈謂:“又自周后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答呂毉山人書》)劉基謂:“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樸。”(《蘇平仲文集序》)所謂“文敝”或“文弊”,乃指“文”起初是人對人的自由自覺的“類”特性、人的“本質力量”進行自我確證的產物,或人創造出來用以對其生命作更豐贍之成全的東西,無論是哪一種情形,“文”起初皆內蘊著人的蓬勃的生命力而為人所主導。然而,吊詭的是,“文”作為人的自我實現的同時,也作為人的自我設限存在著,它對于人自始即有一種疏離或異在的傾向。換言之,“文”,不管是客觀化了的人的精神,如器物、倫常、制度、典章等,抑或是以別一種形態出現的人的精神,如技藝、科學、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等,皆有賴于人的內在的、虛靈的精神去激活它、突破它、提升它,一旦人的生命開始萎縮,不再能充實“文”、養潤“文”,不再能宰制“文”而使其在人之為人的追求上為人所用,這時,“文”的生命便隨之委落,開始淪為一種徒有其表的形式,一種限制人的生命的正向申達的阻礙,一種戕害人的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升華的桎梏,甚至墮落為一種用于掩蓋某種居心的偽飾,成了藏污納垢之所。 “文敝”在不同境況有不同的表現,晚周時這種“文敝”典型地表現于“禮”“樂”的崩、壞。所謂“禮”“樂”的崩、壞,并非指禮的儀文、儀式或儀號、儀章的殘缺,亦非指樂的理趣、演奏技藝或所涉舞、《詩》的遺失或散亂,而是指當禮的儀文、儀式、儀號、儀章和樂的理趣、演奏技藝、所涉之舞、所涉之《詩》流為一種裝飾或被越位越分者僭用時,禮、樂因失去了原先的節制人、潤澤人的生命的意義而隳壞了。此即20世紀新儒家學者牟宗三先生所指出的:“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這套禮樂,到春秋的時候就出問題了,所以我叫它做‘周文疲弊。……這一套周文并不是它本身有毛病,周文之所以失效,沒有客觀的有效性,主要是因為那些貴族生命腐敗墮落,不能承擔這一套禮樂。因為貴族生命墮落,所以他們不能實踐這一套周文。不能來實踐,那周文不就掛空了嗎?掛空就成了形式,成為所謂的形式主義(formalism),成了空文,虛文。”
老子、孔子是最早意識到這一文化危機而試圖從一種人生的終極處予以回應的哲人。這用黃克劍的話說,即是:“他們各自立于一種‘道,而由此把社會、人生的千頭萬緒納入一個焦點:對于生命本始稟受于‘天(自然)的‘人說來,‘禮、‘樂之‘文究竟意義何在?” 老子的答案是否定性的,在他看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老子》五十二章),相反,“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十九章)因此,他主張“復歸于嬰兒”、“復歸于樸”(《老子》二十八章),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老子的學說可謂擯棄任何人為之“文”的“素”“樸”(“質”)價值一元論。同老子一樣,孔子對周末禮樂積垢成敝的狀況亦有深刻的洞察,其不僅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的喟嘆之語,甚而有“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鄉愿,德之賊也”(《論語?陽貨》)的警世之辭。不過有意味的是,孔子并沒有停留于對人的性情之“自然”(“質”)的一味看重,而是嘗試把“人”“文”關系的問題復雜化并由此將其深刻化。在孔子這里,“質樸是人的托底的價值,但托底的價值還不就是人可祈向的可能圓滿的價值。” 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上的可能充分的成全的期待,使孔子并沒有在“文”“質”之間作一種非此即彼的抉擇,而是把它引向對“文”、“質”當如何互成的尋問。
與老子不同,為孔子所稱賞的“質”乃是人的性情之“自然”,此即孟子所說的作為仁義禮智之端倪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誠然,孔子本人并沒有這樣的說法,但從其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一類自勵勵人之語,已可看出他對“仁”在人的天性里自有其根荄的默冥。這根荄可喻之以“質”。在老子那里,“天”、人關系是單向度的,“天道”的顯發沒有給人留下絲毫涉足的余地。在孔子這里,“天”之所“命”的這點“仁”的根荄使人有了成其為人的初始根據,同時“仁”的根荄亦只是在人的覺悟中才真正被確認為“仁”的根荄,其由一種“幾希”之明(“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弘大至“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的“圣”“神”之境,有待于人的孜孜不倦的擴充、提升。“仁”使人成其為人,人亦使“仁”成其為“仁”,并最終由此使踐“仁”之人真正成為有著高尚情操之人,這一“仁”、人相即相成的過程所祈慕的“仁”的性向及其所指向的虛靈的“圣”的理想境地,便一起融成了孔子之“道”。此后孟子曾就這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的“仁”道作了精辟的闡釋,申稱:“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人對“仁”的覺悟、提升,使有著自然之根的“仁”在此過程中構成對人說來的一種應然,這是一種不違于亦不落于人的性情自然之“質”的有為,它本身即是“文”,一種值得肯定的文化創造。人對“仁”的覺悟、提升不能沒有種種人為之“文”(“禮”、“樂”等教化),這些人為之“文”作為前人文化創造遺留下來的產物,原是能夠滋養、擴充這“仁”的根荄的,它的被激活、被喚醒有待于人。人在對“仁”的覺悟、提升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新的種種人為之“文”,其所以生氣蓬勃,乃是由于它亦充盈著人的元始樸素的真性情。孔子由對人生的可能圓滿的意義的期待,遂對“文”的價值作了重新認定。
“仁”就其端倪而言可謂之“質”,就此端倪為人所覺悟、提升而言可謂之“文”,或者更確切地說,“仁”的端倪只是在人的覺悟中才被認定為“仁”的“端倪”,而覺悟本身已是一種人為之“文”,因此“仁”的端倪在被肯認為“質”之際即已非“文”外之“質”。就此來說,所謂“文質之辨”是無從說起的。即便是在老子學說那里,亦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樸”或“質”。不過,“仁”的端倪畢竟是側重于“仁”在人這里的性情自然之根,而對此端倪的覺悟畢竟是側重于人對它的有意識的、有旨趣的反省,就此來說,二者又可勉為分說,而將前者強字之曰“質”,后者勉稱之為“文”。因此“文質之辨”僅就儒家而言。在孔子看來,如果沉溺于原初用于引導、提升“質”的種種人為之“文”,或一味逐求“文”的華美,以至遺忘了“質”甚而有悖于“質”之真趣,便可能“文勝質則史”(文飾、虛飾、偽飾),使對“仁”之端倪的覺悟、提升就此停滯甚至乖離其初衷。另一方面,倘滯濡于“質”或一味地遷就先天之“質”,不對其進行適度的引導、匡束,亦可能“質勝文則野”(野樸、野拙、野陋、野鄙),使人的原本可許之以“好”的“仁”性從此生機遲滯乃至凋零。關于前者,上文圍繞“文敝”所作的種種闡釋足資說明,這里不再贅述。關于后者,此處宜略加敷衍。孔子嘆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在他看來,他所以能竭盡做人的本份,不僅在于天之所賦的“忠信”之“質”,還在于他能“學而不厭”(《論語·述而》)。依“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這里的與“教”相稱之“學”當是指學《詩》《書》《禮》《樂》《易》等古代典籍,并將從中領悟到的一種做人的道理付諸生命的踐履,以陶養在人的天性自有其質的“忠信”之德。反言之,那些忠信如孔子的人所以最終不能盡其天之所賦,將忠信之質提升到相當的境界,究其根底,乃在于他未能足夠自覺而持久地以“學”來化導、提升這份資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這可以說是一則更為典型的論及先天之“質”必有待于后天之“文”的輔翼、匡正的章句。“恭”“慎”“勇”“直”作為人的值得珍視的天性皆可謂之“善”,其中“恭”“慎”皆有“讓”意,“勇”“直”則相對缺少。“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倘不能對它們用禮儀規范予以引導、匡束,一味地循著人的天性之所趨,不僅“勇”“直”會由于缺乏禮的必要引導,難以受到“讓”德的潤澤而橫生暴亂或落于偏激,“恭”“慎”這兩種本身即有“讓”意的德性,亦會由于缺乏禮的必要規范,不能始終將“讓”保持在一種中正、真切的境地上,以至流于勞屈、勞煩或怯懦、畏懼,如此,原初的“勇”“直”“恭”“慎”之“善”都將喪失。所以“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作為一種必要的教化依然是孔子所倡導的。不過,經驗中的人在踐“仁”致“道”的過程中,往往不是偏于“文勝質”便是落于“質勝文”,倘前者可謂之“過”,后者則可謂之“不及”,而“文”“質”相融互攝至恰到好處便是“中”。孔子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所謂“彬彬”,其實即是就“仁”的端倪(“質”)經由種種人為之“文”的潤澤而達到相當高卓的境界(“文”、“質”互成而至無過不及)而作的一種形容。
三、從社會風尚的淳化再看“文質彬彬”
何休、劉逢祿、宋翔鳳、戴望、王闿運從歷史嬗替來理解“文質彬彬”,此說淵源有自。《禮記·表記》載: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這里的“子曰”未必即完全為孔子本人所說,不過《論語》里確載有“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亦載有“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戴望諸人將歷史的遷徙與“文質之辨”相連乃在孔子理致之內。在闡發三代乃至百世如何“改制質文”時,他們除了舉出上述兩章外,還反復論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論語·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路,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靈公》)諸章。當“建五始”“張三世”“通三統”這些公羊學特有的“文化錯覺”徹底失去了吸引人心的效力,植根于此的戴氏等人上述看法也就此退出歷史的舞臺。不過這一看法所運用的方法卻依然能給人們啟示,此即,對“文質之辨”的領會不必拘泥于君子之德的培壅,還可從社會風尚的嬗替予以把握。
同談君子人格的養成一樣,孔子談到社會風尚的下委時,亦時常從人的真性情這一人的天性之“質”的窳敗來說,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談到社會風尚的淳化時,孔子同樣強調了對人的真性情的培壅,如《八佾》全篇輻輳于可視為“禮之本”的人的率真天性的存養,同時孔子亦主張當以人為之“文”將人的天性之“質”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如孔子倡導以修習《詩》《書》《禮》《樂》《易》等古代典籍為主的新“六藝”。最后,談到理想的社會風尚時,孔子亦傾心于“文質彬彬”,如稱“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不過,社會風尚的遷善畢竟有別于君子人格的培育,后者可納入為仁范疇,前者更多歸于為政畛域。孔子為此更多地寄望于在位者的“為政以德”和對百姓的“道之以德”(《論語·為政》),正是從這里出發,孔子談到了值得后學再三玩味的“直道”:
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論語·衛靈公》)
這章最耐人玩味的是末句。何晏注引馬融語謂:“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馬氏以“用”釋“所以”之“以”,認為三代之王不敢欺罔“直”心、“直”情自在之民,而以直道處之。朱子酌取此解注稱:“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近代以來的注家多從何晏、馬融、朱子,認為意指三代之王以直道相待或相率。如宦懋庸謂:“誰毀誰譽?有所試,即直之道也。斯,此也。民,亦人也。行,謂率民而民從之也。夫子既言己之不輕毀譽,又言此民三代以直道率之而即行,以見春秋之時政教非不可行,特在上者曲徇一己好惡之私,不以直道行之耳。” 鄭浩謂:“直道而行,由乎人性本直。三代時此民此性,今亦此民此性。不以直道行之,是非紛淆,民俗澆薄,謂為今民不古若,是誣我民也。以直道行之,則亦復其本然之直矣。觀秦俗之偷,至漢文景,風俗淳厚,幾至刑措,亦可驗矣。” 即便戴望亦謂:“言三代用人,皆以民之好惡,無所偏私,是以云‘直道而行也。《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實,悉本于三代之法。董子曰:‘《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 這些說法似皆可通,不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譽以“道”的“直”與未經陶染的素樸之“直”,并非可以相提并論。“直道”的意趣在這里未有顯發。
近代以來的注家亦有另辟蹊徑者。如錢穆謂:“斯民即今世與吾同生之民。今日之民,亦即自古三代之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謂三代之直道即行于當時之民,亦謂即以當時之民而行斯直道。積三代之久,而知民之所毀譽,莫不有直道,如禹、湯、文、武、周公莫不譽,桀、紂、幽、厲莫不毀。就其毀譽,可以見直道之行于斯民矣。故直道本于人心之大公。人心有大公,故我可以不加毀譽而直道自見。” 依此說,“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的“三代”乃“三代之民”。錢說亦看似有理,其實不然。“直道本于人心之大公”之說無誤,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有些時代“直道”的綻露更明顯些,有些時代“直道”則幾不可見。倘依錢說,亦可謂“春秋末造(之民)之所以直道而行”乎?“三代”之義在這里同樣未獲彰顯。
又,清儒包慎言謂:“‘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于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而入于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睹也。蓋‘斯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于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為善哉?”劉寶楠深贊此說。黃吉村、李炳南、周群振皆信服。如黃氏謂:“《為政》:‘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圣人不以一時之善而譽之,亦不以一時之惡而毀之。若有所譽,所以勉其向善也。若有所毀,所以待其改過也。” 周氏謂:“所謂‘三代,即夏、商、周之盛世。‘直道而行,即彼時圣王之秉持中正大道而治天下,天下之(斯)民,在其至德之處分和試煉下,業已界劃得善惡兩類明白。于是,善者善之,惡者惡之,援舉糾彈,公允平直,悉由超越之義理為準據以判定” 。二說微有差異。依前說,三代之王以“直道”教化百姓,使之改過遷善;依后說,三代之王以“至德”督導、試煉百姓,使之能以“超越之義理”或“直道”行于人間。不過,前說中的“直道”亦不妨理解為“直”,此說的弊端依然是“直道”的意趣未獲顯現。與周說相唱和的是黃克劍的見解,他在同一方向上探索并將“直道”的底蘊歸結于“仁”,將“直道”把握為潛在、現驗之在兩種情形(未經陶染的素樸之“直”、可譽以“道”的“直”):“‘直道所以‘直,其根柢在于‘仁;就其為百姓(‘民)日用而不知言之,‘直道也可謂非自覺的‘仁道或潛在的‘仁道。三代之民和春秋衰世之民在潛在的素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依孔子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相推——乃是因為三代的王者能夠在使民‘富之之后對民‘教之。‘民中自有‘直道,問題在于引導和教化,以使其由非自覺達到自覺,由潛在或自在轉化為現驗的在。” 至此,“直道”說透露出了它最能誘引人的心靈的韻致。
孔子謂:“人之生也直”(《論語·雍也》),但對一己之私的一時偏執,卻有可能導致這天性之“直”在某個人或某些人那里晦昧不明。有趣的是,正如經驗中的圓形總會有著或此或彼的缺陷,當那些在圓之間的對視中開始顯現的缺陷被人的心靈所察覺時,一種完滿而虛靈的圓形反倒可能會被渴慕著更圓乃至最圓的心靈升華出來,它作為一種人之心靈所祈的理想超出了那些有缺陷的圓形。同樣,當這些偏私在對置中使各自的局限開始曝露出來,并在相互制約中得以抵消于人人之際而被揚棄后,一種體現公意的“直”反倒可能獲得原本不同程度囿于私利的眾人的由衷贊可。由此亦可說人群本“直”。然而“直”在不同時代其表現程度并不盡相同。這里的玄機在于是否對“直”心有所導引或誘發。當孔子說“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試”無疑是試之于有一種素樸的“直”心默運其中的“民”。孔子以此“民”為其品鑒人物、褒貶世風的衡準之所出,不過他并沒有止步于此。在他看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民的潛在質素無異,為政者若以政令督導人,以刑罰整治人,所引出的民風將是“免而無恥”;為政者若以道德引導人,以禮儀治理人,所引出的民風則會是“有恥且格”。與此相通,自發的“直”若能得到持續的誘發、引導,不僅人群中的“枉者”或不直之人將受到進一步的匡束,并由此使其晦昧的“直”心轉為清明,普通民眾亦有望使其萌動中的“直”心獲得升華,成為“直”德愈發純厚之人。為政者若能不倦地做下去,自發之“直”便可望被提升到相當高的境界而幾于“道”的境地。反之,自發之“直”若長期遭到漠視,甚至枉曲之風還被有意無意地鼓噪,“直”必將隳敗,以至于隱沒,盡管在某個特殊的時刻它仍可能會有極珍貴的閃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正因為有這些心中自有褒貶尺度并在后天受到三代之王以“德”“禮”引導的百姓,三代才得以直道而行。“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矜”“愚”皆是“疾”,不過古之民雖狂猶肆、雖矜猶廉、雖愚猶直,“肆”“廉”皆有“直”意,古之民即便在修德方面存有不足,仍不失“直”的底色;今之民狂也蕩、矜也忿戾、愚也詐,已全然不見“直”性。這段話可以看作對三代能夠直道而行、春秋衰世難以為繼的注腳。如果說“直”心更多地落于“質”的意趣上,對“直”心的覺悟、提升有待于“文”的成全,那么“直道”便在于把握“文”“質”之張力以向著其“彬彬”之“中”的求取。
除了“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章外,《論語》里眾多強調為政者對民眾“道之以德”的章句,皆可結合社會風尚的再度淳化從“文質之辨”來理解。
結 論
就“文質之辨”這個話題而言,除了“文質彬彬”章外,最有意味的恐怕是以下一則了:“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論語·公冶長》)
這章將君子人格的培育與一定社會風氣下的范本引導相聯系。子賤堪稱君子,能熏陶出子賤這般志士的魯國,必定是講求君子之行而不乏可稱君子之人的國度。在這里,子賤身上那點“仁”心,那點“質”,受到了種種君子之行這一“文”的陶冶,子賤因之也漸入文質彬彬之境。孔子對子賤的評價,不僅表達了對子賤個人德行的贊賞,更是表達了他對魯國尚存文質彬彬之祈求的社會風習的肯定。這章意蘊豐贍,堪稱談論“文質之辨”的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