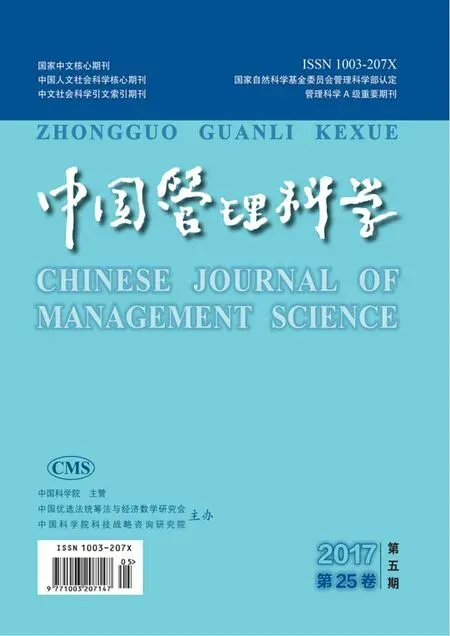企業組織內部學習、外部學習及其協同作用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研究
陳國權,劉 薇
(1.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2.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北京 100081)
?
企業組織內部學習、外部學習及其協同作用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研究
陳國權1,劉 薇2
(1.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2.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北京 100081)
盡管前人對于組織學習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已經展開了較多的研究,但是組織學習對組織績效產生的影響并不是孤立的,組織學習要與組織內、外部情境因素相適應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是強調組織學習不同來源的兩種重要類型,而內部學習、外部學習及二者的協同作用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會受到組織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怎樣的調節作用還尚未得到探索和研究。本研究采用來自中國企業的213個樣本,根據調查數據發現了,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特征對組織學習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同時起到了調節作用。組織外部環境動態性越高,組織內部有機結構程度越高,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提升作用越明顯。然而,在探討不同內、外部環境條件下,內部和外部學習的協同作用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時,研究發現有機結構依舊能夠支持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協同發揮對績效的促進作用,而動態性較高的環境卻不利于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的協同,只有在穩定性較低的環境中,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才能協同促進組織績效。本研究的特點在于系統地分析組織內、外部學習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更好地提升組織績效的環境和條件,同時考慮組織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兩種情境因素的作用,對組織學習理論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對管理實踐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最后,對研究的局限性進行了分析,并提出未來改進和發展的方向。
組織學習;內部學習;外部學習;組織結構;環境動態性;組織績效
1 引言
在當今復雜變化的環境下,組織學習對企業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作為不同來源的兩種組織學習方式,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具有影響作用。在實踐中,聯想的“復盤”學習方法,就是組織內部學習的最好體現,“復盤”強調對成功或者失敗的事例都要進行深刻反思和規律總結,同時也要考慮企業的邊界條件;華為通過從企業外部引進技術和知識,才得以不斷進步發展,體現出外部學習的重要性。在理論上,學者們對內部和外部學習影響組織績效已經進行了一些研究,然而,系統地考慮組織內部和外部情境因素對內部學習、外部學習及二者協同影響組織績效的調節作用,是當今組織學習理論和實踐領域非常重要、但未被實證探討的問題。本文將從權變理論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性研究。
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強調一切都不是靜態的,目標、產出、技術和市場不斷變化,對組織的每個子單元來說,意味著相應的權力形式和組織形態就會發生變化[1]。在目前中國的市場環境中,外部環境變化愈加迅速,使得權變理論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應用。對于組織發展,既包括組織對于外部環境的適應,通過相應的組織結構和戰略設計與市場環境相結合[2],同時還需要匹配組織內部的文化、學習等因素,了解組織中的各個單元之間如何相互協調配合[3]。組織學習的提出為組織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復雜的外部環境提供了方向,組織學習對于組織長期持續發展的作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重視[4-5]。作為促進組織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組織學習會受到組織內、外部不同情境因素的調節作用,依據權變理論思想,組織學習實施的有效性不僅取決于學習本身,還要考慮到其是否能夠適合于組織外部環境資源和特征、與組織內各子系統及戰略目標之間是否能夠彼此配合[6-9]。同時,不同的組織學習方式之間也需要根據內、外部環境情況進行協同[10],才能夠對組織績效的促進產生最佳效果。
因此,前人較多分析了組織內部和外部學習及其協同作用會對組織績效產生影響,本文主要研究和希望解決的問題是,系統地分析組織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如何影響組織內部學習、外部學習及二者的協同作用與組織績效的關系。
2 研究概念
2.1 組織學習(內部學習與外部學習)
學者們將組織學習進行了多種方式的分類,本研究重點強調學習范圍和知識獲取的來源,將組織學習分為內部學習(Internal learning)和外部學習(External learning)[11-12]。內部學習主要指基于組織自身的經驗,組織成員在企業內部范圍內產生和分享新知識,更加強調組織內部的交流和溝通,形成了知識創造的良好氛圍和內部來源[11,13]。企業進行內部學習,主要通過內部的資源和能力發展自有技術,內部學習過程的起點為成員的知識創造,提出對產品和業務流程改進的新思路,在組織內部共享并與其他知識相互整合[14-15]。組織通過內部積累自身經驗獲取的學習,有益于生產率的改進和提高,對學習過程有更強的控制,有助于建立核心競爭力[11]。
外部學習則更多是組織通過其他企業的經驗,由組織邊界成員(Boundary-spanning individual)將組織外部資源和知識通過獲取或者模仿的方式帶入企業,并在組織內傳播[11]。外部學習通過知識獲取為組織信息的更新與創造提供了比較異質化的來源,通過協議、合同和承諾的方式進行知識分享、轉移和發展[13,15]。外部學習的起點為識別外部(顧客、供應商、競爭對手以及合作者等)新的信息,由成員引入并傳播[14]。內部學習較為系統性,時間周期更長,可以建立核心競爭力;而外部學習更為迅速和靈活,對企業的吸收能力要求較高,有助于企業打破技術邊界,建立和擴大知識庫[11,16]。
實證研究發現,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都與組織績效和創新能力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8,16-17]。內部學習針對產品和工作流程的改善提高,將新的知識和內部現有知識相連接,提升成員的整體學習水平;外部學習幫助組織擴大知識庫、識別機會和威脅、增加新市場和技術能力,使企業能夠保持最新的信息來源并維持自身彈性[18]。然而,目前對內、外部學習的研究僅從影響績效的角度進行分析,尚未探討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對這種影響的調節作用。
2.2 組織內部結構(機械結構與有機結構)
組織結構指的是組織中角色和管理機制的正式設計,用以控制和整合工作活動和資源流向[19]。Burns 和Stalker[20]將組織結構分為機械結構(Mechanistic Structure)和有機結構(Organic Structure)兩種類型。機械結構和有機結構都在企業中被廣泛應用,二者的特征具有差異性。
Lee和Yang[21]總結得出,機械結構中組織層級和正式化規則更多、決策中心化程度高、管理范圍較小、溝通過程更依賴于縱向溝通;員工工作專業化程度高、內容嚴格限定、組織中的信息一般按照固定方向傳播[22];另外,機械結構管理關系比較固化、組織正式化程度高、組織成員嚴格遵守層級化的價值觀和原則[23]。
有機結構更能夠有效適應和靈活應對新的問題和機會,采用權力和控制的分散化鼓勵內部的廣泛交流[21]。有機結構的優勢體現在管理關系的靈活性、非正式化、合理授權等方面;有機結構的組織層級和正式化規則更少、組織分權化、管理范圍較寬泛、溝通模式水平化、信息可以沿多方向進行傳遞[22,23]。Martínez-León和Martínez-García[24]提出,探討何種組織結構能夠為組織學習提供最適宜的條件是非常有意義的,組織結構是保障組織及成員能夠進行學習和知識創造的基本機制,對學習過程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25]。
2.3 組織外部環境(環境動態性)
影響組織學習效果的因素包括環境、組織文化、組織結構以及組織內部技術能力,其中環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16]。企業的環境包括政治、文化、法律及內外部各種資源等。環境動態性關注企業外部環境穩定性,包括環境因素的變化程度和不確定性大小,環境動態性會導致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企業難以正確評價目前和未來的環境態勢[26]。本研究對環境動態性的定義在Miller[27]、Jansen[4]等研究的基礎上,總結認為環境動態性指組織的競爭對手、顧客、合作伙伴、政府等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或需求的變化程度,及企業產品與服務類型、所處行業的趨勢和技術創新的變化程度。
3 理論與假設
3.1 組織內部學習對績效的影響關系中,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
對于組織學習,權變理論認為在特定環境下,存在最優的學習戰略,并且這種最優學習戰略需要特定的組織結構和管理系統的支撐[28]。組織的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是組織建立競爭優勢的主要促進因素,應選取相應的結構模式與之匹配。組織結構會影響學習過程各個主體之間如何互動、以及組織學習行為的產生[24]。內部學習過程需要內部協調和溝通,組織結構決定了協調的機制,影響學習過程中的信息流動。有機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更強、組織層級更少,有助于學習主體之間充分有效的溝通。在有機結構中信息自由流動,從內部獲取的知識可以被廣泛交流、達成共識,并將共享的知識轉變為具體行動、提升組織績效。然而,機械結構中個體的職能和分工較明確、部門之間壁壘較高,導致組織內部知識難以充分共享,阻礙了知識和信息進一步轉化為具體行動,不利于提升組織績效。因此,組織內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會受到機械式組織結構的負向調節作用。由此,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1a:機械式組織結構負向調節(有機式組織結構正向調節)內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即組織的機械式結構程度越高(有機式結構程度越低),內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弱;
在組織學習理論研究中,比較重要的三個組織學習要素包括:學習源、組織學習方式和外部環境,根據知識的來源,將學習源分為內部和外部學習源,外部環境對不同學習源的學習效果產生作用[29]。動態的環境使得組織產生緊迫感,外部的環境壓力促進組織更快地、更有效地運用從內部獲得的經驗和知識對現有工作進行改進,將不斷總結出的經驗教訓轉化為行動,提升組織績效。因此,組織內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會受到外部環境動態性的正向調節作用。由此,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1b:環境動態性正向調節內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即環境動態性越強,內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強;
然而,組織內部學習對績效的促進,既需要外部環境的動態激發,同時也需要內部結構的有效保障,內部學習如何同時與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相匹配,影響組織績效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理想的組織結構設計是能夠適應企業外部環境的,組織學習需要在相匹配的結構和環境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30]。組織的有機結構比機械結構更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有機結構可以促進交流溝通,對市場和行業需求迅速反應;而機械結構更適合于穩定的環境條件[23],機械結構會抑制環境動態性對組織內部學習影響組織績效的激發作用。如上面H1a和H1b所述,動態的環境使組織產生緊迫感,不斷總結自身經驗和知識,并轉化為具體行動,同時有機結構保證了知識在內部的分享和交流,提高組織績效。綜上所述,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1c:環境動態性越強,機械式組織結構程度越低(有機化組織結構程度越高),內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強。
3.2 組織外部學習對績效的影響關系中,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
有機結構對外部信息更加開放并具有吸納性,加深了組織對外部新知識和信息的吸收,并產生分享和共同的理解,促進信息和知識轉化為具體行動,進而提升組織績效。在機械結構中,由于信息流動方向的固化,難以幫助組織對外部有效知識和信息的獲取、吸收、理解和運用,不利于提升組織績效。Bresman和Zellmer-Bruhn[31]在團隊層面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組織結構性(中心化、專業化、層級性程度)越強,團隊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程度越低,越不利于績效的提升。因此,機械結構會抑制環境動態性對組織外部學習影響組織績效的激發作用。由此,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2a:機械式組織結構負向調節(有機式組織結構正向調節)外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即組織的機械式結構程度越高(有機式結構程度越低),外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弱;
Bao Yongchuan等[9]根據權變理論提出,外部學習的有效性取決于學習策略與環境是否匹配。他們還將外部學習分為管理學習和技術學習,發現技術動蕩性和競爭性分別增強了兩種學習方式對創新的影響。吳價寶等[5]在團隊層面上提出,環境打造了團隊的學習氛圍、對團隊學習產生的影響作用。處于動態環境中的企業,能夠通過組織外部學習的過程更加關注外部市場的不斷變化。同時,動態環境增強了組織的緊迫感,需要組織將從外部獲取的學習和知識更迅速、更有效地轉化為行動,不斷提升組織績效,建立自身競爭優勢,以適應環境的變化程度和速度。由此,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2b:環境動態性正向調節外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即環境動態性越強,外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強。
Ramezan[32]的研究中強調了,變化環境下有機結構具有重要作用,有機結構更加有助于吸納組織外部的行業、技術和商業環境信息。有機結構更適合于不穩定的(Unstable)和變化的(Changing)環境,包括出現新的問題和不可預見的要求,外部環境動態性較高時,組織外部信息、技術和知識流動性較高,需要企業不斷進行調整和適應。機械結構中工作任務和流程較為固化,信息傳播的方向和途徑也較為單一,不利于組織從外部獲取知識和信息。如H2a和H2b所述,動態環境增加組織緊迫感,使其不斷獲取外部知識信息,而有機結構促使這些知識信息的有效吸收、共享理解和轉化運用,并提升組織績效。綜上所述,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2c:環境動態性越強,機械式組織結構程度越低(有機式組織結構程度越高),外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強。
3.3 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績效的協同影響關系中,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
由于組織內的資源有限,同時采用兩種組織學習方式可能會導致激烈的資源競爭,不利于達到良好的學習成效[10]。然而,兩種組織學習從不同的來源獲取知識,同時采用也可能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組織內部和外部學習具有差異性的學習內容和知識來源,能否將其有效整合受到內、外部環境條件的限制。組織需要根據不同的內、外部情境因素作用,了解和判斷組織內部和外部學習是否可以相互協同,共同促進組織績效的提升。本研究提出,組織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動態性,都會影響組織內外學習之間的協同作用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
對于組織內部結構,組織有機結構中資源分配的渠道更靈活、適應性和變通性更高[33]。有機結構中資源的流動性高,能夠滿足有限資源在不同學習方式之間流動和轉化,而有機結構內部的有效溝通和合作,有助于組織通過內部和外部學習獲取、整合不同的知識信息,進而相互配合促進組織績效發展。機械結構中,組織信息溝通和交流的渠道較嚴格,制度和等級明確,不利于資源在兩種學習方式之間的流動,內部和外部學習難以獲取足夠的資源進行績效提升;另外,機械結構也難以整合兩種學習方式獲取的知識和信息,不利于組織績效的提升。由此,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3:組織結構有機式程度更高時,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向的交互作用。
對于組織外部環境,在環境動態性較低的情況下,組織不需要調動較多資源去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因而有較為充足的資源同時采取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兩種學習方式能夠協調發揮作用;環境動態性較低還能夠提供較為平穩的條件和較為充足的時間,使得這兩種學習方式所獲取的知識和信息進行溝通、共享和整合,被組織更好地消化和吸收,從而促進組織績效的提升。環境動態性較高的情況下,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迅速,組織需要調動較多的資源去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限資源使得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難以發揮協同作用;環境動態性較高還會導致兩種學習方式獲取的信息和知識內容差異性增大,內部經驗和外部知識難以有效互融和整合。由此,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4:組織環境動態性較低時,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向的交互作用。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本文研究框架
4 研究方法
4.1 概念的測量
調查問卷采用7點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
4.1.1 組織學習:內部學習與外部學習
本研究對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的測量基于陳國權[34]的研究進行構建,內部學習主要指的是組織從內部獲取知識和經驗,如:“企業善于對以前的工作進行反思,總結出經驗或教訓”等。外部學習主要指的是企業從外部獲取知識和經驗,如:“企業善于從外部獲取知識和經驗”等。
4.1.2 組織結構:有機結構與機械機構
關于組織有機結構和機械結構的測量分為兩種情況,Covin和Slevin[23]提出,機械結構和有機結構是兩個對立統一體,機械式和有機式處于對立的兩端,用相同的條目對其進行測量,得分越高機械結構越強,同時得分越低有機結構越強;Su Zhongfeng等[33]的研究中也采用了同樣的方法。陳建勛、凌媛媛和王濤[35]提出,機械結構和有機結構是相互獨立的構念,采用不同的條目對其進行測量。根據本研究對于組織結構的界定和分析,認為機械結構和有機結構為兩種對立的組織結構形式,主要采用第一種方法,使用相同的條目對其進行測量。
陳國權[34]在其《組織行為學》中引用Burns 和Stalker[20]及Courtright, Fairhurst和Rogers[36]等的研究,對機械、有機兩種組織結構的特征進行了歸納,機械機構特點為:員工工作高度專業化、工作內容嚴格限定、命令鏈明確嚴格、管理高度正規化、管理幅度窄、信息只能沿固定方向傳遞、決策集中于上層、采用集中控制管理,有機結構特點則相反。共7個測量條目,如:“員工工作高度專業化”,“員工工作內容嚴格限定”等。
4.1.3 環境動態性
環境動態性采用Miller[27]的量表,動態性操作化定義為市場中顧客需求、產品和服務技術以及企業主要產業競爭態勢的變化程度。共7個測量條目,如:“本企業的市場和客戶的需求變化快”,“本企業相關的政府部門的政策和要求變化快”等。
4.1.4 組織績效
本研究根據Dess和Robinson[37],以及McDougall等[38]的研究對組織績效進行測量,將組織績效定義為組織在整體產出上的表現情況。共6個測量條目,如:“與同行相比,本企業在投資回報率上具有競爭優勢”等。
4.1.5 控制變量
考慮通常在中國情境下常用的控制變量,具體為:(1)企業所在地區(虛擬變量,企業所在地區為東部時為1,非東部為0);(2)企業所處行業(虛擬變量,企業為制造業為1,非制造業為0);(3)企業所有制性質(虛擬變量,國有企業為1,非國有企業為0);(4)企業年齡;(5)企業人數,對企業員工總人數取對數處理。
4.2 研究樣本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選取的調查對象主要為中國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具體包括參加北京某高校管理教育項目的企業管理人員,及其所在單位的其他中高層管理者。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約300份,將其中填寫不完整和沒有認真填寫的問卷進行刪除后,得到有效問卷共213份。調查樣本總體情況如下:來自制造業企業占25%,非制造業占75%;來自國有企業占36%,非國有企業占64%;來自東部地區企業占78%,非東部地區占22%。被調查者的總體情況如下:男性69%,女性31%;平均年齡38.8歲;在本企業的平均工作年限為9年。
5 研究結果
5.1 信度效度分析
首先使用LISREL8.7對內部學習、外部學習、環境動態性和組織績效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各變量的標準因子載荷如表1所示,擬合指標為:χ2=697.94,df=242,χ2/df=2.88, RMSEA=0.098, CFI=0.93, NNFI=0.92,NFI=0.90,GFI=0.78。測量具有較高的收斂效度和判別效度,潛變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值大于0.5,說明收斂效度較好,相關系數小于潛變量的AVE值平方根說明判別效度較好。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由于數據采用的是被試自評的量表,對同源數據進行Harman單因子檢驗評估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39],包括驗證性因子分析(CFA)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1)對數據進行驗證性單因子檢驗,χ2=2095.65,df=252,χ2/df=8.31,RMSEA=0.22, CFI=0.73, NNFI=0.70,NFI=0.70,GFI=0.46。單因子模型的擬合度明顯沒有多因子更好;(2)對數據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對所有變量的測量條目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滿足Hair等[40]給出的標準,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不超過50%,則可接受。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旋轉后第一個因子解釋變異量為33.4%,研究結果不會受到同源數據的顯著影響。
對于內部學習、外部學習、環境動態性和組織績效進行信度分析,使用SPSS17.0進行檢驗,各變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均大于0.8,如表1所示,說明量表信度較好,根據因子分析結果,去除了組織結構測量中標準載荷較低的題項。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CFA)與信度檢驗
N=213。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
注:*p<.05;**p<.01(雙尾檢驗);N=213;對角線上為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5.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對所有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研究變量在后面構建乘積項時都采用中心化后的數據(取z值)。
5.3 假設檢驗
5.3.1 假設H1的檢驗
對假設H1進行檢驗,組織內部學習作為自變量時,利用SPSS軟件采用分層逐步回歸的方法,如表3所示,內部學習(β=0.424,p<0.01)會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交互項作為第三層變量進行回歸方程構建模型4,內部學習與組織結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β=-0.092,p>0.1),假設H1a沒有得到驗證。一方面,機械式結構不利于組織內部非正式的溝通和交流,內部學習難以轉化為組織績效;但是另一方面,機械式結構促進知識和經驗的正式傳達,以及知識和經驗在組織中的存儲。譬如,Ramezan[32]就提出,機械結構更注重內部知識、經驗和技能的正式積累,能夠促進學習和建立競爭優勢。這兩個方面的影響相互抵消,使得調節作用不顯著。內部學習與環境動態性的乘積項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作用(β=0.113,p<0.05),假設H1b得到了驗證。
內部學習、組織結構和環境動態性三項的乘積項作為第四層變量進行回歸方程構建模型5,三項交互的乘積項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作用顯著(β=-0.100,p<0.05),且符號與內部學習與環境動態性的交互作用相反,說明組織結構(機械結構)抑制了環境動態性對組織內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關系的正向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在組織結構機械式程度較低(有機式程度較高)、組織外部環境動態性較高的情境下,組織內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假設H1c得到驗證。

表3 內部學習對績效的影響關系中,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
注:p<0.10;*p<0.05;**p<0.01(雙尾檢驗);N=213。
5.3.2 假設H2的檢驗
組織外部學習作為自變量時,如表4所示,外部學習(β=0.469,p<0.01)會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外部學習與機械式組織結構的乘積對組織績效有顯著影響(β=-0.112,p<0.05),機械式組織結構對外部學習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起到負向調節作用,假設H2a得到驗證;外部學習與環境動態性的乘積項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β=0.141,p<0.01),環境動態性對外部學習與組織績效的調節作用顯著,假設H2b得到了驗證。
外部學習、組織結構和環境動態性三項交互的乘積項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作用顯著(β=-0.136,p<0.01),且符號與內部學習與環境動態性的交互作用相反,說明組織結構(機械結構)抑制了環境動態性對組織外部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間關系的正向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在組織結構機械式程度較低(有機式程度較高)、組織外部環境動態性較高的情境下,組織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假設H2c得到驗證。

表4 外部學習對績效的影響關系中,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
注:p<0.10;*p<0.05;**p<0.01(雙尾檢驗);N=213.
5.3.3 假設H1c和H2c的對比分析
組織的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都會受到組織結構和外部環境動態性的調節作用,假設H1c(內部學習、組織結構和環境動態性的三項交互作用)和假設H2c(外部學習、組織結構和環境動態性的三項交互作用)都得到了驗證。但是,對兩個模型5進行比較,相對于內部學習(β=-0.100,p<0.05)來說,機械式組織結構和外部環境對于組織外部學習(β=-0.136,p<0.01)的調節作用更顯著。在組織結構機械式較低、外部環境動態性較高的組織中,外部學習對于績效提升作用更明顯。換句話說,在有機式組織結構和動態性的外部環境中,組織外部學習可以發揮更強的作用。
5.3.4 假設H3的檢驗
將樣本根據組織結構機械式程度相對高低分為兩組,機械式程度較低的企業認為主要采取有機結構,機械式程度較高的企業認為主要采取機械結構,對兩組樣本分別進行逐步回歸,如表5所示。

表5 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的協同作用對績效的影響關系中,組織結構的調節作用
注:p<0.10;*p<0.05;**p<0.01(雙尾檢驗);N=213。
在更為有機化結構的組織中,組織內部學習(β=0.223,p<0.05)和外部學習(β=0.278,p<0.05)都會對組織績效產生影響,組織外部學習的影響系數較高且更為顯著。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產生了正向的交互作用(β=0.184,p<0.05),組織采取有機結構時,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可以協同對組織績效產生影響作用。在更為機械化結構的組織中,組織內部學習(β=0.029,p>0.1)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不顯著,而外部學習(β=0.255,p<0.05)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比較顯著,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產生了一定的負向交互作用(β=-0.014,p>0.1),但是并不顯著,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機械結構中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是難以協同的。由此,假設H3得以驗證:組織有機式結構程度更高時,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向的交互作用。
5.3.5 假設H4的檢驗
將樣本根據環境動態性相對高低分為兩組,環境動態性較低的企業認為是處于較為平穩的環境中,環境動態性較高的企業認為是處于較為動蕩的環境中,對兩組樣本分別進行逐步回歸,如表6所示。
在較為平穩環境中,組織內部學習(β=0.243,p<0.05)和外部學習(β=0.206,p<0.1)都會對組織績效產生影響作用,組織內部學習的影響系數較高且更為顯著,說明在較為平穩的外部環境中,組織從內部進行經驗和知識的總結、歸納、創造和分享,對組織績效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產生了一定的正向交互作用(β=0.118,p=0.1),說明在環境動態性較低時,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促進,協同發揮作用。在較為動蕩環境中,組織內部學習(β=0.155,p>0.1)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不顯著,而外部學習(β=0.431,p<0.01)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非常顯著,說明在較為動蕩的環境中,組織從外部獲取新知識和新信息,更有助于組織績效的提升,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產生了一定的負向交互作用(β=-0.056,p>0.1)。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動蕩環境中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是難以協同的,與之前單獨考慮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影響的結論相反,環境低動態性環境中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才能產生協同作用。由此,假設H4得以驗證:環境動態性較低時,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向的交互作用。

表6 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的協同作用對績效的影響關系中,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
注:p<0.10;*p<0.05;**p<0.01(雙尾檢驗);N=213。
6 結語
本研究從權變思想的角度,探討對組織學習效果產生影響的內、外部權變情境因素,研究發現,在有機結構和動態性較高的環境中,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能夠更顯著地促進績效;在有機結構和動態性較低的環境中,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的協同作用能夠更顯著地促進績效。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組織內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組織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組織內部結構有機化程度越高(機械式程度越低),組織外部環境的動態性越強,組織內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越明顯。外部環境的動態性高,決定了組織需要進行內部學習和提升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外部市場和需求,內部結構的有機式程度決定了員工工作自主性和積極性水平,員工可以在組織內部充分共享與交流知識和信息,進而更好地促進了組織績效增長。
第二,組織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組織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組織內部結構有機式程度越高(機械式程度越低),組織外部環境的動態性越強,組織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越明顯。對于高動態性外部環境來說,不斷產生新的知識、技術和信息,激發了組織外部學習的需求和有效性。在這種條件下,有機結構中組織靈活性和適應性相對較高,能夠幫助企業更加高效地識別和獲取有效信息,外部市場中的需求和技術也能及時被企業采納和吸收,使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的促進作用更明顯。
第三,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的協同作用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組織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在內部結構有機性強、外部環境動態性低的組織中,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向的交互作用。與內部和外部學習單獨進行調節作用的結論一致,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的協同作用在有機結構中更顯著。在有機結構中,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對組織績效都有積極作用,有機結構保障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動,能夠有效整合內、外部不同的信息,使兩種學習方式協調發揮作用;而在機械結構組織中,組織制度明確、資源和信息的流動性較低,難以克服資源的有限性問題。然而,與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單獨進行調節作用的結論不一致,內部和外部學習的正向交互作用在環境動態性較低的情況下更顯著。環境動態性較高時,組織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都能夠對組織績效產生促進作用,但是二者的協同性不強;而且外部變化更快,組織獲取的自身經驗和外部知識差異性較大,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難以有效互融和整合。環境動態性較低時,企業可以協同采取兩種學習方式對知識和信息進行多方面獲取和吸收,內、外部學習相互促進提高組織績效。
本研究對于中國企業實踐具有重要的管理啟示和指導意義,首先,企業需要意識到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都會對組織績效產生影響作用,因此兩種學習方式都應該得到企業的關注和重視。其次,企業應該時刻關注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適應環境的動態性,在動蕩的外部環境中盡可能采取單一的組織學習方式,而在較為平穩的環境中不同類型的組織學習得以共存發揮協同作用。另外,在環境不可調整的情況下,企業可以通過投入更多的資源促進組織學習,還可以通過提高組織結構的有機化程度進行內部的組織結構設計,增強組織內部的溝通交流和靈活性的運作方式,來加強組織資源的流動性。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內部學習和外部學習作為不同來源的學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斥性,但是流動性的資源有助于二者相互補充和促進,避免了兩種學習方式由于有限資源而產生的相互排斥,對組織績效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本研究在組織學習理論和權變理論領域具有一定的理論貢獻和實踐意義,但是仍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未來的研究方向。本研究主要以企業樣本為主,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展樣本量和樣本中組織的多樣性,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研究結論的普遍適用性。本研究的樣本數據采用被試自我報告的測量方法,并進行了Harman單因子檢驗評估了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度,分析結果表明研究結果是在可接受范圍的,但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盡量采用非同源或客觀指標數據,更好地保證結果的有效性。此外,本研究重點探討了組織學習與內部結構、外部環境的匹配對組織績效的作用,然而,組織的良性可持續發展也需要兼顧其他組織有效性,未來研究可以更加關注組織學習與內、外部情境因素的匹配,對其他組織結果變量(例如,員工發展和滿意度等方面)的影響。
作者希望本文關于組織學習、組織結構、外部環境與組織績效之間關系的探索性研究,能對組織學習領域研究和實踐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將不斷進行改進,使之更加完善。
[1] Hickson D J, Hinings C R, Lee C A, et al. A strategic contingencies' theory of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1,16(2): 216-229.
[2] Gresov C. Exploring fit and misfit with multiple contingencie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9, 34(3): 431-453.
[3] Hong K K, Kim Y G.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ERP implementation: An organizational fit perspective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2, 40(1): 25-40.
[4] Jansen J J P, Vera D, Crossan M. Strategic leadership for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9, 20(1): 5-18.
[5] 吳價寶, 張帥兵, 蔣嬌. 組織中團隊間學習環境, 學習模式與團隊間學習績效關系研究 [J]. 科技管理研究, 2013, 33(21): 206-210.
[6] Hong J. Structuring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 Learning Organization, 1999, 6(4): 173-186.
[7] 陳國權.組織與環境的關系及組織學習 [J]. 管理科學學報, 2001, 4(5): 39-49.
[8] 王鐵男, 陳濤, 賈榕霞. 組織學習, 戰略柔性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 [J]. 管理科學學報, 2010, 13(7): 42-59.
[9] Bao Yongchuan, Chen Xiaoyun, Zhou K Z. External learning, market dynamics, and radic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tech fir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2, 65(8): 1226-1233.
[10] He Zilin, Wong P K. 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 [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4, 15(4): 481-494.
[11] Bierly P, Chakrabarti A. Generic knowledge strategies in the U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WINTER): 123-135.
[12] Wong S S. Distal and local group learning: Performance trade-offs and tension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6): 645-656.
[13] 孫永風, 李垣. 基于組織內部溝通與整合能力的內外部知識整合與創新 [J]. 中國管理科學, 2005, 13(1): 56-61.
[14] 曾德明, 張運生, 陳立勇. 高新技術企業內外部學習的契合機制研究 [J]. 軟科學, 2003, 17(6): 93-96.
[15] Xu Rui, Zhao Liankun. Impact of extern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on radical innov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 Management,Kitakyushu,Japan,November 30-December 2, 2011.
[16] Kessler E H, Bierly P E, Gopalakrishnan S. Internal vs. external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Effects on speed, cost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R&D Management, 2000, 30(3): 213-224.
[17] 謝洪明, 張霞蓉, 程聰, 等.網絡關系強度, 企業學習能力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2, 33(2): 55-62.
[18] López-Sáez P, Navas-López J E, Martín-de-Castro G, et al.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processes in knowledge-intensive clusters [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0, 14(5): 690-707.
[19] Olson E M, Walker O C, Ruekert R W. Organizing for effectiv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duct innovativeness [J].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5, 59(1): 48-62.
[20] Burns T, Stalker G M.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M]. London: Tavistock,1961.
[21] Lee C L, Yang H J. Organization structure,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and their joint effects on performance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11, 22(2): 84-104.
[22] 陳國權.組織行為學 [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12016.
[23] Covin J G, Slevin D P.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n the utility of an entrepreneurial top management styl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88, 25(3): 217-234.
[24] Martínez-León I M, Martínez-García J A.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011, 32(5/6): 537-566.
[25] Bapuji H, Crossan M. From questions to answers: Review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research [J]. Management Learning, 2004, 35(4): 397-417.
[26] Simerly R L, Li Mingfang. Environmental dynamism,capit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an empirical tes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 31-49.
[27] Miller D. The stru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business strateg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7, 8(1): 55-76.
[28] Miles R E, Snow C C.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evolv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7, 25(2): 459-463.
[29] 謝言, 高山行.組織學習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實證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 2013,(1): 11-17.
[30] De Groot T, Brownlee A L. Effect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on th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department effectiveness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6, 59(10): 1116-1123.
[31] Bresman H, Zellmer-Bruhn M. The structural context of team learn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d team structure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4(4): 1120-1139.
[32] Ramezan M.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organic structure in knowledge society: How are these concepts relate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1, 31(1): 88-95.
[33] Su Zhongfeng, Li Jingyu, Yang Zhiping, et al.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28(4): 697-714.
[34] 陳國權.組織學習和學習型組織:概念, 能力模型, 測量及對績效的影響 [J]. 管理評論, 2009, 21(1): 107-116.
[35] 陳建勛, 凌媛媛, 王濤. 組織結構對技術創新影響作用的實證研究 [J]. 管理評論, 2011, 23(7): 62-71.
[36] CourtrightJ A, Fairhurst G T, Rogers L E.Interaction patterns in organic and mechanistic syste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32(4): 773-802.
[37] Dess G G, Robinson R B.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absence of objective measures: The case of the privately-held firm and conglomerate business uni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3): 265-273.
[38] McDougall P P, Covin J G, Robinson R B, et al. The effects of industry growth and strategic breadth on newventure performance and strategy cont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15(7): 537-554.
[39] Podsakoff P, Organ D.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6, 12(4): 531-544.
[40] Hair J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5th ed.)[M]. London: Prentice Hall,1989.
Organizational Internal Learning, Extern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Corporations: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Dynamism
CHEN Guo-quan1,LIU We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Business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reasoning, models and hypothesis about 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ternal learning and exter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echanistic structure and organic structur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performance are b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gency theory. With a sample of 213 Chinese companie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are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moderation. Evidence is foun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es by showing that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both internal learning and external learning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re moderated b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dynamics. The higher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and the lower the mechanistic structure (the higher the organic structure), the more obvious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both internal learning and external learning, on performanc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internal learning and external learning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organic structure and stable environment. While in mechanistic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internal learning and external learning don’t have synergistic effect on performance. In this stud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organizations are combined to discuss, which mak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bout how to create better condition and environment fo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hinese companies should emphasiz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and integrate the two learning styles by structural design and environmental recognition. Finall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re analyz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s propose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ternal learning; exter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1003-207(2017)05-0175-12
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17.05.021
2016-06-06;
2016-11-2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項目(71421061,71121001);國家杰出青年基金項目(7062500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重大項目(06JJD630013);教育部博士點基金(20090002110037)
劉薇(1987-),女(蒙族),內蒙古人,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組織學習與員工學習、領導力、情緒影響個體行為等,E-mail:liuwei@cufe.edu.cn.
C93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