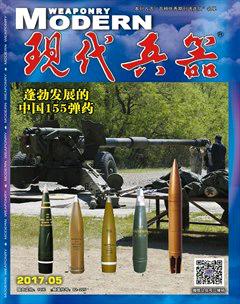曲折之路 淺談美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體制的建立和完善(3)
竇超++張旭
越南戰(zhàn)爭
與朝鮮戰(zhàn)爭的情況相比,美軍在越南戰(zhàn)爭中的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體制卻出現(xiàn)了倒退。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將侵越空中力量分為三部分:一是駐越軍援司令部,直接指揮駐越軍援司令部空中部隊(duì),后者對隸屬于第13航空隊(duì)的第2空軍師實(shí)施作戰(zhàn)控制;二是太平洋司令部空軍,指揮第13航空隊(duì),后者又直接指揮第2空軍師;三是太平洋艦隊(duì),下轄第7艦隊(duì),第7艦隊(duì)對第17特混艦隊(duì)的航空兵實(shí)施指揮。這三者之間關(guān)系復(fù)雜,造成了指揮上人為的混亂。
作為在越南實(shí)際負(fù)責(zé)當(dāng)?shù)刈鲬?zhàn)指揮任務(wù)的駐越軍援司令部,最初卻并沒有一個(gè)專門負(fù)責(zé)空中作戰(zhàn)的副司令。時(shí)任駐越軍援司令部司令的威斯特摩蘭認(rèn)為,美軍在南越的主要作戰(zhàn)任務(wù)是地面作戰(zhàn),因此他的副司令必須是一名與他一樣的陸軍將軍,以此來分擔(dān)他的工作。面對空軍方面的壓力,威斯特摩蘭提議由一名空軍中將來擔(dān)任主管空軍作戰(zhàn)的副司令,同時(shí)讓他兼任第2空軍師師長。需要注意的是,這名副司令只主管空軍作戰(zhàn),而不是像通常的副司令一樣擁有指揮整個(gè)下屬部隊(duì)的權(quán)力。空軍方面爭取未果,只好同意了這一提議。
穆爾空軍中將擔(dān)任主管空軍作戰(zhàn)的副司令后,立即提出要求有權(quán)控制陸軍直升機(jī)部隊(duì)。他建議,在戰(zhàn)術(shù)航空兵控制中心內(nèi)設(shè)置陸軍航空兵的代表。這樣一來,戰(zhàn)術(shù)航空兵控制中心就可以像指揮空軍飛機(jī)一樣地指揮直升機(jī)進(jìn)行作戰(zhàn)。但這一提議立即遭到了來自陸軍方面的抵制,從而在整個(gè)戰(zhàn)爭期間戰(zhàn)術(shù)航空兵控制中心都處于缺乏此種控制權(quán)的狀態(tài)。

越南戰(zhàn)爭中的美國陸軍UH-1D直升機(jī)群
而在與直升機(jī)一樣同地面作戰(zhàn)關(guān)系緊密的海軍陸戰(zhàn)隊(duì)航空兵方面,同樣是處于各自為戰(zhàn)的狀態(tài)。1965年5月6日,駐越軍援司令部發(fā)布指令稱:“陸戰(zhàn)隊(duì)航空兵的資源屬于陸戰(zhàn)隊(duì)第3航空聯(lián)隊(duì)的建制,在支援戰(zhàn)術(shù)性的作戰(zhàn)活動(dòng)中,按陸戰(zhàn)隊(duì)第3 航空聯(lián)隊(duì)司令官的指示進(jìn)行指揮和引導(dǎo)。對于支援陸戰(zhàn)隊(duì)的作戰(zhàn)活動(dòng)的所有陸戰(zhàn)隊(duì)飛機(jī),以及可能支援此種作戰(zhàn)活動(dòng)的其他飛機(jī),陸戰(zhàn)隊(duì)的戰(zhàn)術(shù)航空兵控制系統(tǒng)將實(shí)施確實(shí)無誤的控制。在美駐越南軍援司令部宣布重大的緊急情況下,第2空軍師將對美駐越南軍援司令部所指定的某些航空兵資源行使作戰(zhàn)控制之權(quán)。”
這樣一來,美軍在越南的空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duì)航空兵就處于兩個(gè)指揮系統(tǒng)之下,從而成為兩支并行的戰(zhàn)術(shù)航空兵力量。負(fù)責(zé)空軍作戰(zhàn)的副司令也就沒有權(quán)力指揮海軍陸戰(zhàn)隊(duì)航空兵,只有“在美駐越南軍援司令部宣布重大的緊急情況下”,第2空軍師才可能根據(jù)駐越軍援司令部的指令對“某些航空兵資源行使作戰(zhàn)控制之權(quán)”。
空軍未能獲得海軍陸戰(zhàn)隊(duì)航空兵的作戰(zhàn)控制權(quán),這樣的努力在海軍那里更是遭到強(qiáng)烈抵制。如果想要對現(xiàn)有的戰(zhàn)術(shù)航空兵力量實(shí)施統(tǒng)一指揮,那么最好的辦法是由第2空軍師(后擴(kuò)編為第7航空隊(duì))統(tǒng)一指揮戰(zhàn)術(shù)航空兵力量。然而,當(dāng)空軍提出這樣的想法時(shí),海軍立即做出強(qiáng)烈反應(yīng)。海軍太平洋艦隊(duì)司令爭辯說,海軍的空中力量是艦隊(duì)的一個(gè)固有部分,是艦隊(duì)完成其使命所必需的,不能分離出去。這位艦隊(duì)司令提出,可以指定某一軍種為“負(fù)責(zé)組織協(xié)調(diào)的單位”,其權(quán)力只限于諸如交換有關(guān)突擊計(jì)劃的情況,為特定的作戰(zhàn)活動(dòng)要求支援以及制定一些避免各方面的活動(dòng)發(fā)生矛盾的程序。這樣的單位實(shí)際上只是一個(gè)協(xié)調(diào)者而非指揮者,是起不到統(tǒng)一指揮的作用的。
最后,太平洋司令部空軍被指定為負(fù)責(zé)“滾雷”作戰(zhàn)的組織協(xié)調(diào)單位,對海軍艦載機(jī)部隊(duì)沒有作戰(zhàn)控制權(quán)。穆爾與海軍第77特混艦隊(duì)組成一個(gè)工作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擬定在上述精神基礎(chǔ)上的兩支部隊(duì)的作戰(zhàn)方案。空軍方面最初提出了時(shí)間劃分方案,即由空軍飛機(jī)和海軍飛機(jī)以3小時(shí)為一段任務(wù)時(shí)限分別進(jìn)行輪流作戰(zhàn);而海軍不喜歡這一方案,提出以地段劃分為基礎(chǔ)的方案。雙方不斷爭辯和做出讓步,最后形成了“包干區(qū)”的解決方案。美軍將北越劃分為6個(gè)包干區(qū),其中第6個(gè)又劃分為空軍和海軍分別負(fù)責(zé)的兩個(gè)部分。這樣劃分之后,空軍分到了3個(gè)區(qū),而海軍則分到4個(gè)區(qū)。空軍分到的包干區(qū)雖然數(shù)量少,但面積卻大得多,而且作戰(zhàn)困難也大得多。除了在最后幾個(gè)月在包干區(qū)劃分上有所調(diào)整之外,包干區(qū)的方式一直持續(xù)到戰(zhàn)爭結(jié)束。
負(fù)責(zé)指揮B-52戰(zhàn)略轟炸機(jī)的戰(zhàn)略航空兵的指揮協(xié)調(diào)也是一個(gè)問題。戰(zhàn)略航空兵在駐越軍援司令部內(nèi)設(shè)立了一個(gè)聯(lián)絡(luò)組,負(fù)責(zé)對后者提出的空中突擊計(jì)劃進(jìn)行協(xié)調(diào)。該聯(lián)絡(luò)組主要是與駐關(guān)島的戰(zhàn)略航空兵所屬第8航空隊(duì)聯(lián)系,后者指揮東南亞地區(qū)的所有B-52轟炸機(jī)、加油機(jī)和戰(zhàn)略偵察機(jī)。而具體負(fù)責(zé)越南空中作戰(zhàn)的第7航空隊(duì)卻對此無權(quán)控制。直到1972年,第7航空隊(duì)才開始通過戰(zhàn)略航空兵前方指揮所對B-52進(jìn)行控制,但仍然是在沒有正式授權(quán)的情況下進(jìn)行的。
上述辦法雖然是各個(gè)軍種取得共識(shí)的結(jié)果,但事實(shí)證明卻是嚴(yán)重影響空中作戰(zhàn)效率的辦法。美軍后來認(rèn)為,空中力量未能給越南方面以足夠的壓力,致使整個(gè)戰(zhàn)爭過程被嚴(yán)重拖長,最后導(dǎo)致以撤出越南告終。后來擔(dān)任美軍參聯(lián)會(huì)主席的戴維·瓊斯空軍上將稱越南戰(zhàn)爭“也許是我們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目標(biāo)不明、職責(zé)不清的典型”,各軍種“將越南戰(zhàn)爭看作是自己的戰(zhàn)爭,并爭搶任務(wù)”。甚至在1975年從西貢撤退時(shí),“兩個(gè)司令部還實(shí)行條塊分割,一個(gè)負(fù)責(zé)海上,一個(gè)負(fù)責(zé)陸上,行動(dòng)開始時(shí)間各不相同,造成了混亂和拖延”。對于空戰(zhàn),瓊斯認(rèn)為越南戰(zhàn)爭上“至少有六場不同的空戰(zhàn):海軍在北部的空戰(zhàn)、空軍在北部的空戰(zhàn)、戰(zhàn)略空軍的空戰(zhàn)、空軍在南部的空戰(zhàn)、越南人的空戰(zhàn)以及陸軍直升機(jī)的空戰(zhàn)”。這恰恰說明了美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體制在這一時(shí)期所具有的嚴(yán)重弊病。
“普韋布洛”號(hào)事件
在著名的“普韋布洛”號(hào)間諜船被朝鮮抓捕事件中,美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體制再次出現(xiàn)了嚴(yán)重問題。說到此次事件中美軍的失誤,就不能不提到美軍在20世紀(jì)50年代后期對太平洋地區(qū)指揮體制的變動(dòng),這是造成此次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軍遠(yuǎn)東司令部撤消后,作為太平洋司令部職能擴(kuò)大的一部分,在日本和朝鮮建立了低一級(jí)的聯(lián)合司令部,稱之為下級(jí)聯(lián)合司令部,也就是今天駐日美軍和駐韓美軍指揮機(jī)構(gòu)的前身。當(dāng)時(shí),駐日美軍司令是一名空軍中將,直接向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負(fù)責(zé)。但奇怪的是,這名駐日美軍的聯(lián)合司令部司令除了指揮自己兼任司令的第5航空隊(duì)之外,對駐日陸軍和海軍部隊(duì)卻并沒有指揮權(quán),而是只有“規(guī)劃和協(xié)調(diào)”的權(quán)力。也就是說,這位聯(lián)合司令部司令只能指揮自己的空軍部隊(duì),其他軍種可以聽他的“規(guī)劃和協(xié)調(diào)”,當(dāng)然也可以不聽。駐韓美軍司令更有意思,他只對美國太平洋司令部陸軍司令負(fù)責(zé),而不是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負(fù)責(zé),對其他軍種同樣也沒有指揮權(quán)。
1957年的指揮體制調(diào)整更具破壞性——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指揮權(quán)限擴(kuò)大后,華盛頓卻剝奪了他對太平洋艦隊(duì)的指揮權(quán),而將這項(xiàng)權(quán)力令人匪夷所思地轉(zhuǎn)交給他的副手。第二年,一個(gè)獨(dú)立的更具競爭性的職位出現(xiàn)了,這就是負(fù)責(zé)指揮太平洋地區(qū)所有海軍艦隊(duì)的太平洋艦隊(duì)司令。這位艦隊(duì)司令雖然名義上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下級(jí),但其對于上級(jí)的競爭卻非常強(qiáng)勁。
1968年1月23日,美國海軍“普韋布洛”號(hào)間諜船在距朝鮮海岸線約24千米的地方,被朝鮮海軍俘獲。在“普韋布洛”號(hào)被迫開到朝鮮元山港的4個(gè)小時(shí)內(nèi),美軍原本是可以展開援救行動(dòng)的,但卻因?yàn)橹笓]體制上的問題延誤了時(shí)間而未能實(shí)施。在“普韋布洛”號(hào)實(shí)施偵察行動(dòng)之前,美軍指揮當(dāng)局并不認(rèn)為該船執(zhí)行的任務(wù)有什么危險(xiǎn)性。因?yàn)樵谥暗男袆?dòng)中,雖然針對蘇聯(lián)進(jìn)行的偵察曾經(jīng)多次遭到監(jiān)視或干擾甚至碰撞,但針對朝鮮的行動(dòng)卻未發(fā)生過這樣的情況。因此,美軍駐日海軍艦隊(duì)司令約翰遜海軍少將并沒有具體部署任何針對“普韋布洛”號(hào)行動(dòng)的海空支援部隊(duì)和應(yīng)急方案。

停泊在朝鮮首都平壤南部大同江畔的“普韋布洛”號(hào)間諜船
但在事件發(fā)生25天以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向參聯(lián)會(huì)下轄的聯(lián)合偵察中心發(fā)出警告,稱“普韋布洛”號(hào)有遭到朝鮮攻擊的危險(xiǎn),建議評(píng)估該船的防護(hù)措施。聯(lián)合偵察中心將情報(bào)發(fā)送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和海軍作戰(zhàn)部長。前者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將情報(bào)轉(zhuǎn)發(fā)給了下級(jí)司令部。駐韓美軍空軍部隊(duì)司令本來與此事沒有什么直接關(guān)系,但他通過朝方在最近表現(xiàn)的敵對態(tài)度,看到“普韋布洛”號(hào)的行動(dòng)說明后認(rèn)為這是“一種非常冒險(xiǎn)的態(tài)度”。他要求參謀人員與駐日第5航空隊(duì)司令部聯(lián)系,以確認(rèn)他是否需要“準(zhǔn)備應(yīng)急跑道或者采取其他預(yù)防措施來保障該船的安全”。駐日海軍的回答是,沒有必要準(zhǔn)備應(yīng)急跑道。3天后,面對空軍的再次詢問,海軍仍然給予否定的答復(fù)。海軍可能當(dāng)時(shí)對空軍的這種“狗拿耗子多管閑事”還有點(diǎn)不耐煩。
就在這種情況下,“普韋布洛”號(hào)于1月11日離開日本港口前往任務(wù)區(qū)域。23日12時(shí)54分半,“普韋布洛”號(hào)發(fā)出警報(bào),說此次干擾行動(dòng)不是通常的干擾。1個(gè)半小時(shí)后,該船發(fā)出了最后一份電報(bào):“我們被迫停船并立即接受登船檢查”。該船于16時(shí)45分被押往元山港。在這4個(gè)小時(shí)時(shí)間內(nèi),美軍卻因?yàn)橹笓]體制上的重重阻隔無法采取行動(dòng)。駐日海軍司令約翰遜因?yàn)闆]有預(yù)先準(zhǔn)備援助“普韋布洛”號(hào)的措施,只能向駐日美軍司令同時(shí)也是第5航空隊(duì)司令的麥基空軍中將求助。而這一要求卻因?yàn)閮蓚€(gè)軍種之間溝通不暢(駐日美軍海軍和空軍司令部之間沒有緊急直通電話),經(jīng)過40分鐘才送到麥基手中。
駐韓美軍飛機(jī)裝備了核武器而無法執(zhí)行這一援救任務(wù),同時(shí)駐日本本土的美軍空軍部隊(duì)也因?yàn)槭艿轿溲b部隊(duì)地位條約約束而不能在日本本土發(fā)起軍事行動(dòng)。這樣,麥基就只能動(dòng)用南方483千米之外的駐沖繩的空軍部隊(duì)。但問題是他們距離“普韋布洛”號(hào)有1127千米之遙。麥基下令該部立即派出飛機(jī)前往韓國烏山加油后,對朝鮮的“任何敵對部隊(duì)進(jìn)行攻擊”。收到命令1小時(shí)23分鐘后,2架F-105戰(zhàn)斗轟炸機(jī)起飛。但它們到達(dá)烏山后,已經(jīng)無法在天黑前到達(dá)“普韋布洛”號(hào)所在區(qū)域。
事件發(fā)生時(shí),駐日本的隸屬于太平洋艦隊(duì)海軍陸戰(zhàn)隊(duì)前方司令部的2個(gè)攻擊機(jī)分隊(duì)正在進(jìn)行空對地攻擊訓(xùn)練,它們距離“普韋布洛”號(hào)只有1小時(shí)的航程。但它們的上級(jí)司令部卻與“普韋布洛”號(hào)不屬于同一通信網(wǎng),直到第二天才聽說發(fā)生了此次危機(jī)。當(dāng)時(shí),麥基雖然知道海軍陸戰(zhàn)隊(duì)航空兵部隊(duì)就在附近,但是他的身份和指揮權(quán)限卻令他無權(quán)指揮這些部隊(duì)。如果想要?jiǎng)佑眠@些部隊(duì),他需要請求太平洋司令部空軍指揮官與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或太平洋艦隊(duì)司令進(jìn)行溝通協(xié)商此事后,才能通過海軍指揮系統(tǒng)將相應(yīng)命令下達(dá)到陸戰(zhàn)隊(duì)航空兵部隊(duì)。這樣一來,實(shí)在是“黃瓜菜都涼了”。
“普韋布洛”號(hào)遇險(xiǎn)時(shí),同屬于海軍的第7艦隊(duì)下屬“企業(yè)”號(hào)航空母艦正在距事發(fā)海域約500海里的地方進(jìn)行演習(xí)。如果措施得當(dāng),“企業(yè)”號(hào)是可以及時(shí)援助“普韋布洛”號(hào)的。然而,約翰遜少將自己認(rèn)為華盛頓會(huì)下令第7艦隊(duì)司令布林格爾海軍上將援助“普韋布洛”號(hào),因此沒有提出請求。下午14時(shí)30分,“企業(yè)”號(hào)獲悉了“普韋布洛”號(hào)的處境通報(bào),但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dòng)。如果當(dāng)時(shí)派出可以執(zhí)行作戰(zhàn)任務(wù)的35架飛機(jī)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在2個(gè)半小時(shí)內(nèi)到達(dá)“普韋布洛”號(hào)的位置的。然而,布林格爾下達(dá)的命令卻是:“沒有接到進(jìn)一步通知前,任何艦船和飛機(jī)都不要采取過激行動(dòng)”。就這樣,“普韋布洛”號(hào)最后獲得支援的機(jī)會(huì)也失去了。

“普韋布洛”號(hào)間諜船的船員獲釋
后來,被關(guān)押近一年才被釋放的“普韋布洛”號(hào)船員在海軍偵訊法庭上說:“我和其他的船員所受到的毒打,與我們向這支世界上最強(qiáng)海軍求援,而他們卻無動(dòng)于衷相比,其傷害程度不及后者的一半”。這次事件充分說明,雖然當(dāng)時(shí)駐日和駐韓美軍的下級(jí)聯(lián)合司令部實(shí)現(xiàn)了陸軍和空軍力量的統(tǒng)一指揮,但是海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duì)通信系統(tǒng)卻不與其兼容。甚至在海軍內(nèi)部,第7艦隊(duì)和駐日、駐韓海軍司令的指揮體系也是分離的。因此,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相互協(xié)作。同時(shí),指揮體系的分離也造成畫地為牢的弊病。各地區(qū)的海軍司令官只對毗鄰海域負(fù)責(zé),也就是說駐韓美軍海軍司令對由駐日海軍司令派出的“普韋布洛”號(hào)的行動(dòng)無權(quán)進(jìn)行干預(yù),而前者卻是對半島軍事形勢最為了解的人。
伊朗與格林納達(dá)
在1980年的營救伊朗人質(zhì)行動(dòng)中,美軍在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體制方面的不足仍然是固有的重大缺陷。如在營救伊朗扣押的美國人質(zhì)的行動(dòng)中,執(zhí)行營救任務(wù)的聯(lián)合特遣部隊(duì)完全是臨時(shí)搭起來的“草臺(tái)班子”。由于沒有聯(lián)合條令和程序,以及參加行動(dòng)的官兵缺乏跨軍種經(jīng)驗(yàn),使得完成任務(wù)變得困難重重。結(jié)果是各軍種參戰(zhàn)分隊(duì)并沒有在一起訓(xùn)練,而是在各自的指揮官帶領(lǐng)下,按照本軍種的條令和程序進(jìn)行訓(xùn)練。聯(lián)合參謀部雖然成立了制定計(jì)劃的機(jī)構(gòu),但卻是臨時(shí)性質(zhì),經(jīng)驗(yàn)不足,權(quán)力和責(zé)任也不明確,造成“結(jié)構(gòu)混亂,官僚習(xí)氣嚴(yán)重,內(nèi)部各部分之間交流困難,有些時(shí)候甚至很難進(jìn)行”。
當(dāng)時(shí),美軍已經(jīng)了解到伊朗人只需要15分鐘就可以將人質(zhì)轉(zhuǎn)移,但由于過分強(qiáng)調(diào)行動(dòng)的保密,使得參與行動(dòng)的每個(gè)人只知道與自己有關(guān)的部分,造成整個(gè)行動(dòng)準(zhǔn)備缺乏整體性,計(jì)劃本身存在的缺陷未能被察覺。只是因?yàn)閰⒓有袆?dòng)的直升機(jī)要從航空母艦上起飛,飛行員就使用來自海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的人員。這次行動(dòng)要求夜間秘密滲透飛行,必須進(jìn)行超低空貼地飛行,而這些飛行員實(shí)際上嚴(yán)重缺乏這方面的訓(xùn)練和經(jīng)驗(yàn)。本來,空軍有96名飛行員擁有這樣的能力,卻因?yàn)檐姺N間的競爭而沒有使用他們,最終釀成了RH-53D直升機(jī)與C-130運(yùn)輸機(jī)相撞的慘劇。由于聯(lián)合特遣隊(duì)沒有建立完善的指揮和控制程序,同時(shí)指揮權(quán)限也不明確,造成現(xiàn)場有4名指揮官卻讓參戰(zhàn)人員搞不清楚到底“誰負(fù)責(zé)”。在一片指揮混亂的情況下,整個(gè)行動(dòng)最終以悲劇告終。
3年之后的入侵格林納達(dá)行動(dòng)美軍取得了勝利,然而行動(dòng)的細(xì)節(jié)卻同樣顯示出美軍在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體制方面的不足。最能表現(xiàn)這一情況的莫過于,參戰(zhàn)的美國陸軍部隊(duì)和海軍陸戰(zhàn)隊(duì)分別在各自的指揮體系下進(jìn)行作戰(zhàn)。入侵行動(dòng)是由大西洋司令部負(fù)責(zé)的(這是一個(gè)以海軍為主組成的司令部,人員也是海軍軍官占絕大多數(shù)),指揮官麥克唐納海軍上將本來并沒有打算讓海軍陸戰(zhàn)隊(duì)參加這次行動(dòng),只需動(dòng)用部分陸軍部隊(duì)和海軍特種部隊(duì)就夠了。然而,當(dāng)他向參聯(lián)會(huì)報(bào)告作戰(zhàn)計(jì)劃時(shí),海軍陸戰(zhàn)隊(duì)司令凱里陸戰(zhàn)隊(duì)上將卻要求海軍陸戰(zhàn)隊(duì)加入這一行動(dòng),并且得到了參聯(lián)會(huì)成員們的贊同。當(dāng)時(shí),距在貝魯特的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duì)軍營遭到自殺汽車炸彈襲擊僅僅過了12個(gè)小時(shí),實(shí)在是讓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陸戰(zhàn)隊(duì)企圖利用此次作戰(zhàn)挽回面子。
更要命的是,海軍陸戰(zhàn)隊(duì)不愿意在陸軍的指揮下作戰(zhàn)。最后,參聯(lián)會(huì)將格林納達(dá)的作戰(zhàn)區(qū)域分成兩部分,分別由陸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duì)負(fù)責(zé),從而在統(tǒng)一的戰(zhàn)場環(huán)境中人為地打入了一個(gè)楔子。第2艦隊(duì)司令梅特卡夫海軍中將受命指揮參戰(zhàn)的聯(lián)合特遣部隊(duì)。然而,直到行動(dòng)開始前的最后一刻,陸軍第24機(jī)步師師長施瓦茨科普夫少將(即后來海灣戰(zhàn)爭中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和2位陸軍少校才加入到海軍主導(dǎo)的聯(lián)合特遣部隊(duì)參謀班子里來。這樣,參謀班子里總算有了一個(gè)懂得陸戰(zhàn)的高級(jí)將領(lǐng),而在此之前這一機(jī)構(gòu)里面沒有一個(gè)陸軍軍官。施瓦茨科普夫后來回憶說,陸軍軍官當(dāng)天進(jìn)入?yún)⒅\班子時(shí)“像腮腺炎一樣被迎接”。麥克唐納很刺耳地告訴他:“看在上帝的份上,試試看能不能幫上忙?我們?nèi)蝿?wù)艱巨,我們不需要陸軍讓我們很難堪。”

飛行在格林納達(dá)上空的美國海軍A-7E攻擊機(jī)
行動(dòng)開始后,當(dāng)陸軍直升機(jī)降落在海軍軍艦上時(shí),海軍指揮官卻收到了從華盛頓海軍審計(jì)員那里發(fā)來的緊急電報(bào)。電報(bào)警告說海軍不應(yīng)該給陸軍直升機(jī)加油,因?yàn)椤昂完戃姷呢?cái)務(wù)交接還沒有做出來”。不過,海軍指揮官總算沒有把這個(gè)電報(bào)當(dāng)成上級(jí)的命令,陸軍直升機(jī)還是得到了油料。當(dāng)施瓦茨科普夫需要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直升機(jī)運(yùn)載他的突擊隊(duì)員和空降兵去一所醫(yī)學(xué)院營救那里的美國學(xué)生時(shí),一名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的上校卻拒絕說:“我們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的直升機(jī)不載陸軍的士兵”。氣急敗壞的施瓦茨科普夫隨即威脅要把這位上校送上軍事法庭,上校的態(tài)度才變得溫和起來。
通訊方面的問題造成各軍種之間聯(lián)系非常困難。海軍使用的無線電系統(tǒng)和使用文森加密無線設(shè)備的陸軍部隊(duì)無法直接聯(lián)系,使得請求海軍進(jìn)行火力支援變得極為復(fù)雜。即使陸軍部隊(duì)目視能看到海軍軍艦時(shí)也無法請求其實(shí)施火力支援,只能等到空軍的飛機(jī)和陸軍的直升機(jī)趕來支援才能發(fā)起攻擊。
在一次行動(dòng)中,一名陸軍突擊隊(duì)指揮官發(fā)現(xiàn)自己的無線電無法與在視距內(nèi)的海軍戰(zhàn)艦聯(lián)系,而此時(shí)他的部隊(duì)又急需艦炮火力支援。此時(shí),這位指揮官想到了一個(gè)聰明絕頂?shù)霓k法。他走進(jìn)一個(gè)電話亭,使用美國電話電報(bào)公司的電話卡打電話給布拉格堡的陸軍指揮機(jī)構(gòu),然后通過那里轉(zhuǎn)接到諾福克的海軍指揮部,最后再從諾福克轉(zhuǎn)接到自己能看到的軍艦上。后來,有人對此說到:“陸軍軍官打電話指揮槍炮作戰(zhàn),這一舉動(dòng)全新地詮釋了美國電話電報(bào)公司的口號(hào)‘伸出你的手,聯(lián)系世界任何角落”。這一略帶喜感的故事,實(shí)際上正是說明了當(dāng)時(shí)美軍在聯(lián)合作戰(zhàn)方面的嚴(yán)重缺陷。
各軍種之間的不協(xié)調(diào),最終還是釀成了誤傷。由海軍陸戰(zhàn)隊(duì)和海軍人員組成的一個(gè)岸上火力控制小組,使用無線電引導(dǎo)一架海軍A-7攻擊機(jī)轟炸了隸屬于陸軍第82空降師的一個(gè)旅部,造成17人受傷,其中3人重傷。當(dāng)時(shí),這個(gè)小組正試圖引導(dǎo)飛機(jī)攻擊敵軍的一個(gè)火力點(diǎn)。造成這一事件的原因是岸上火力控制小組不了解陸軍當(dāng)時(shí)的態(tài)勢,也沒有使用第82空降師的地圖坐標(biāo)系統(tǒng)。美軍依靠占有絕對優(yōu)勢的軍力取得了這次入侵的勝利,但正如馬克·艾德金在《緊急狂暴:格林納達(dá)戰(zhàn)斗》一書中寫的那樣:“事實(shí)上這就是一場煙幕,它掩蓋了這次行動(dòng)實(shí)際上是‘搞砸了的令人沮喪的事實(shí)。如果要說軍方曾碰得頭破血流的話,那就是在格林納達(dá)”。美軍參聯(lián)會(huì)后來也承認(rèn),這次行動(dòng)“加深了人們對聯(lián)合體制不力的認(rèn)識(shí)”。
軍種利益之爭
美軍在20世紀(jì)80年代以前的戰(zhàn)爭經(jīng)歷已經(jīng)說明了其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體制一直是其強(qiáng)大的軍事實(shí)力中的一塊短板,而和平時(shí)期的實(shí)例卻同樣能夠證明這一點(diǎn)。太平洋司令部于80年代初期給各軍種作戰(zhàn)物資規(guī)定了各自的儲(chǔ)備地點(diǎn),然而太平洋艦隊(duì)卻拒絕服從。太平洋艦隊(duì)的海軍高級(jí)將領(lǐng)認(rèn)為,后勤仍然是軍種內(nèi)部事務(wù),他們自己有權(quán)決定后勤物資的儲(chǔ)備地點(diǎn)。太平洋司令部自從成立那一天起,其司令的人選都是從海軍產(chǎn)生的,而太平洋艦隊(duì)卻不服從自己軍種派出的聯(lián)合司令部司令的指揮,看起來海軍已經(jīng)不把這樣的軍官看成是能夠代表自己軍種利益的人了。
時(shí)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克羅海軍上將認(rèn)為:“像其他聯(lián)合司令部指揮官一樣,我只能通過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的司令官來指揮作戰(zhàn),他們處在我和野戰(zhàn)部隊(duì)之間。這種編制的問題是,雖然聯(lián)合指揮官負(fù)有全部的責(zé)任,但是他沒有足夠的權(quán)力。他下屬的軍種指揮官向各自軍種的部長匯報(bào)行政、后勤和訓(xùn)練事宜,而各軍種部長可以使用這個(gè)途徑越過聯(lián)合司令部司令官進(jìn)行指揮。這可能造成大規(guī)模的混亂和沖突。”
太平洋司令部屬下部隊(duì)中的另一件事也非常能說明問題。很長時(shí)間以來,駐沖繩島的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第3師都是每次派一個(gè)炮兵營到朝鮮半島靠近非軍事區(qū)的射擊場進(jìn)行射擊訓(xùn)練。這個(gè)名為“噩夢”的射擊場離非軍事區(qū)只有24千米,在美國陸軍第1軍的防御區(qū)內(nèi)。該軍軍長庫仕曼中將向當(dāng)時(shí)任駐韓美軍司令維希上將負(fù)責(zé),他向海軍陸戰(zhàn)師的指揮官建議,當(dāng)這個(gè)炮兵營訓(xùn)練時(shí)如果遭到朝鮮攻擊,就把這個(gè)營劃歸美軍第2步兵師炮兵指揮,以發(fā)揮其最大的威力用于防御作戰(zhàn)。
誰知,海軍陸戰(zhàn)師指揮官立即表示抗議,并指出海軍陸戰(zhàn)隊(duì)條令規(guī)定,海軍陸戰(zhàn)隊(duì)各部隊(duì)必須在海軍陸戰(zhàn)師的指揮下作戰(zhàn)。庫仕曼對此感到極為不解:“如果真的打起仗來,我會(huì)感到奇怪,在該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炮營與敵人交火之前,可能會(huì)發(fā)現(xiàn)該營正在等著一個(gè)海軍陸戰(zhàn)師或其他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編制的總部的出現(xiàn)。”可是,庫仕曼卻解決不了這個(gè)問題,他的上司也不能解決這個(gè)問題。最后,形成了這樣一個(gè)奇怪的局面:維希上將轄區(qū)內(nèi)有個(gè)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炮營,距離任何海軍力量都有幾百英里遠(yuǎn),作為陸軍上將的他卻沒有指揮這個(gè)營的權(quán)力。
有時(shí),狹隘的軍種利益之爭真真正正體現(xiàn)在細(xì)微之處。在20世紀(jì)50年代,美國空軍上將幾乎都有自己的個(gè)人豪華專機(jī),而空軍有時(shí)卻找不到一架飛機(jī)用來運(yùn)送陸軍部長。冷戰(zhàn)對峙的高潮期,美國空軍駐歐洲的一家醫(yī)院被認(rèn)為一旦開戰(zhàn)必然會(huì)遭到攻擊而毀滅,因此做出計(jì)劃準(zhǔn)備在戰(zhàn)爭開始時(shí)將其疏散。然而與此同時(shí),陸軍卻計(jì)劃著轉(zhuǎn)移過來,當(dāng)空軍離開后使用這家醫(yī)院。出現(xiàn)這樣的差錯(cuò),美軍卻不知道要由誰來負(fù)責(zé)。
在武器裝備發(fā)展方面,各個(gè)軍種爭斗起來更是不遺余力。有這樣一個(gè)例子:美蘇對抗最高潮的時(shí)代,美國陸軍的防空導(dǎo)彈曾有一部分裝備了核彈頭。這一情況對于那些準(zhǔn)備襲擊美國目標(biāo)的蘇聯(lián)轟炸機(jī)來說,肯定是非常可怕的。然而,對于這些防空導(dǎo)彈所要保衛(wèi)的地面上的人們來說,同樣是非常可怕的。因?yàn)檫@些防空導(dǎo)彈在消滅蘇聯(lián)轟炸機(jī)的同時(shí),也會(huì)順帶著將地面上的東西一同大部毀滅。這一現(xiàn)在看起來非常愚蠢的主意,完全是軍種之間的明爭暗斗決定了陸軍決心同樣要在蘇聯(lián)轟炸機(jī)的威脅下“有所作為”。
相對于有職責(zé)而沒有相應(yīng)權(quán)力的聯(lián)合司令部,美軍各軍種通過控制“軍事必需品——財(cái)力、人力、物資、武器的研發(fā)和選擇,以及最重要的人事的分配與提升”,“非常成功地維持了許多職責(zé)和特權(quán)”。有時(shí),參聯(lián)會(huì)居然要靠拋硬幣的方式來解決有關(guān)主要武器系統(tǒng)撥款的嚴(yán)重分歧。《1958年國防部改組法》規(guī)定建立了聯(lián)合司令部,同時(shí)賦予了其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權(quán)。但是,美軍各軍種卻通過各種手段來拆聯(lián)合司令部的臺(tái),最終使得其成了有名無實(shí)的“擺設(shè)”。
美國陸軍上將戈?duì)柭?983年5月接管了總部在巴拿馬的南方司令部,從而成為美軍聯(lián)合司令部司令。戈?duì)柭先沃蠛芸炀桶l(fā)現(xiàn),現(xiàn)有的聯(lián)合司令部在各個(gè)方面都有重大缺陷,根本就難以遂行擔(dān)負(fù)的任務(wù)。據(jù)他回憶,他自己是“被指派到南方司令部總部的唯一一位將官。被指派到那里的軍銜僅次于我的軍官是個(gè)陸軍上校”。戈?duì)柭窒碌目哲娊M成部隊(duì)司令,同時(shí)也兼任聯(lián)合司令部的副司令的人是一個(gè)空軍少將,后來因?yàn)榘┌Y死在這個(gè)崗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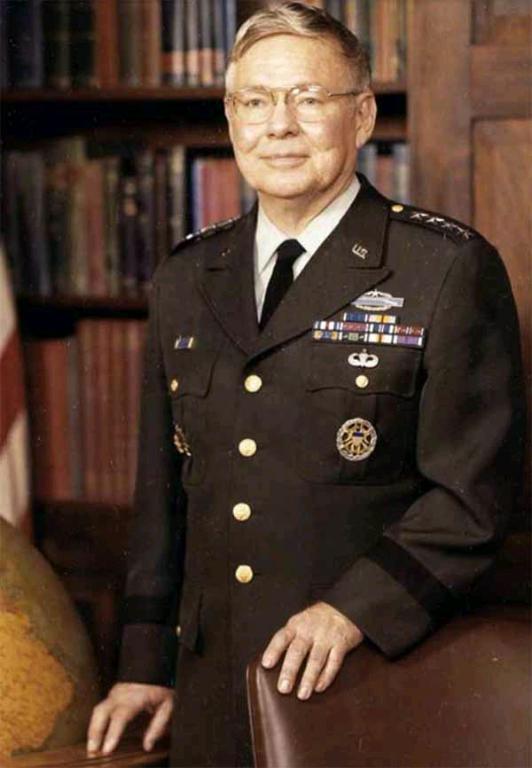
美國陸軍上將戈?duì)柭?/p>
戈?duì)柭f:“空軍并不認(rèn)為他的工作很重要,于是就把他丟在那里……我需要太多的協(xié)助,而我的空軍組成部隊(duì)指揮官遠(yuǎn)遠(yuǎn)不能提供那些幫助……我很少看到他。他不在崗位上。我根本就沒有副司令。”每個(gè)軍種派到南方司令部工作的人員期限,也因?yàn)楦鬈姺N不同的人事制度而不同。每當(dāng)戈?duì)柭M成自己的團(tuán)隊(duì)不久,就會(huì)有來自不同軍種的軍官離開而不得不再次重新組建。
與此同時(shí),每個(gè)被派到聯(lián)合司令部工作的來自各軍種的軍官自己也認(rèn)為是受到了所在軍種的排斥而被攆了出來,在這里工作的經(jīng)歷非但沒有益處,反而會(huì)大大影響自己在本軍種內(nèi)的發(fā)展。因此,很多人也將聯(lián)合司令部的工作看成是自己職業(yè)道路上的障礙,而非獲得提升的途徑。
南方司令部司令還發(fā)現(xiàn)自己對指派到手下的各部隊(duì)的掌控是有限的。例如,在巴拿馬的陸軍旅隸屬于陸軍的一個(gè)部隊(duì)司令部,其所有資源都來自于這個(gè)司令部。戈?duì)柭笓]這個(gè)旅的企圖總是受到這樣一個(gè)以美國為基地的、有預(yù)算責(zé)任但沒有作戰(zhàn)責(zé)任的指揮部的限制。戈?duì)柭谫Y源的使用上也被置于較低的優(yōu)先度上,作為陸軍上將司令的他只被分配給一架陸軍螺旋槳式C-12飛機(jī)。當(dāng)來自于各個(gè)軍種的四星上將們乘坐現(xiàn)代化的噴氣式運(yùn)輸機(jī)往返于各地時(shí),戈?duì)柭鼌s只能坐著這種低級(jí)別的飛機(jī)慢慢騰騰地飛行。據(jù)說,戈?duì)柭磕甓加?1天時(shí)間在這種飛行緩慢的飛機(jī)上渡過。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聯(lián)合司令部如果不掌握至關(guān)重要的人事和資源分配權(quán),那么想高效運(yùn)作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這一情況直到1986年的《改組法》通過之前,都是不能得到解決的。
(未完待續(xù))
(編輯/筆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