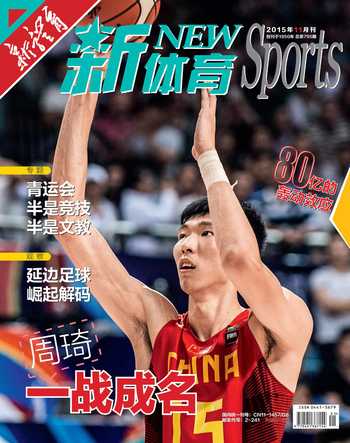控衛(wèi)雙子星
程青山
男籃亞錦賽強(qiáng)勢奪冠,重回亞洲之巔,讓國人為之振奮。同時,由郭艾倫和趙繼偉組成的雙控衛(wèi)讓所有人眼前一亮,被人們視為中國男籃未來十年的后衛(wèi)線。
這兩個年輕人究竟用怎樣的表現(xiàn)征服了球迷,他們又是如何做到了這一切?年少成名,他們的未來又會有怎樣的發(fā)展?
亞錦賽小組賽階段的第二場,中國男籃遭遇到嚴(yán)峻的考驗,首節(jié)比賽陷入大比分落后,第二節(jié)開始后一度分差擴(kuò)大到20分。就在這樣一個令人近乎絕望的時刻,宮魯鳴做出了一次關(guān)鍵的換人調(diào)整,讓郭艾倫和趙繼偉這一對兒來自遼寧的控衛(wèi)同時出現(xiàn)在場上。
或許沒有多少人能夠想到這一變化竟然成了那場比賽的轉(zhuǎn)折點!在兩名控衛(wèi)的聯(lián)手策動下,中國男籃一點點搶回主動權(quán),拉近比分,最后憑借郭艾倫的一次助攻和一次犀利突破,實現(xiàn)了逆轉(zhuǎn)。
在當(dāng)時,沒有多少人能夠想到,這一變化居然讓原來的戰(zhàn)術(shù)變得靈活,中國男籃憑借這個雙控衛(wèi)打法,一路毫無阻礙地直達(dá)亞洲籃球的榮譽(yù)之巔!
總共9場比賽,雙控衛(wèi)成為中國男籃的戰(zhàn)術(shù)發(fā)動機(jī),兩個人都很好展示了自己的出色才能。郭艾倫場均11分、4次助攻、3.2個籃板和1.4次搶斷,只有1.5次失誤;趙繼偉也打出了場均4.9分、3.1個籃板、3次助攻和0.8次搶斷的數(shù)據(jù),失誤僅1.4次。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兩人除了全面的能力,還擁有讓對手羨慕的年齡。郭艾倫22歲,趙繼偉20歲,年輕就是資本。因為年輕,即使在決賽中兩人都暴露出了犯規(guī)、失誤過多的問題,但是他們有著足夠的時間去進(jìn)步。因為年輕,已經(jīng)站在亞洲之巔的他們未來有著無限的可能。
對于中國男籃而言,此前十年一直飽受詬病的控衛(wèi)短板似乎已經(jīng)迎來轉(zhuǎn)機(jī)。

當(dāng)雙控衛(wèi)的風(fēng)暴席卷亞錦賽后,這個曾經(jīng)流行一時又幾度沉寂的戰(zhàn)術(shù)再一次成為焦點。這個戰(zhàn)術(shù)究竟是男籃暗藏的殺手锏,還是誤打誤撞的靈光一現(xiàn)?
之所以有這樣的疑惑,主要源于郭艾倫的壓哨歸隊。在幾乎錯過了一個夏天與全隊的合練之后,郭艾倫能否在短暫的時間內(nèi)同全隊演練出行云流水般的雙控衛(wèi)戰(zhàn)術(shù)?對于其他球員來說,在這漫長的集訓(xùn)期間曾打過多場熱身賽,為什么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這樣的戰(zhàn)術(shù)?其實,雙控衛(wèi)的成功是有一點意外,但不能算是偶然。
首先,球隊并沒有把其作為常規(guī)戰(zhàn)術(shù)來看待,只是諸多戰(zhàn)術(shù)儲備中的一項,以便應(yīng)對各種不同的場上情況。但是,當(dāng)這個組合是來自遼寧的郭艾倫和趙繼偉時,一切就變得不同了。郭艾倫打法獨特,以往在國家隊中擔(dān)任控衛(wèi)時,要肩負(fù)起組織全隊的重任,很大程度上犧牲了自己在進(jìn)攻中的創(chuàng)造性和侵略性。這一次因為有趙繼偉,宮魯鳴給了郭艾倫非常特殊的權(quán)限,就是在出現(xiàn)反擊機(jī)會時可以自由選擇,這激活了郭艾倫的攻擊性。因此,大家才在亞錦賽上一次又一次看到郭艾倫那標(biāo)志性的貫穿全場的反擊,讓人熱血沸騰。
其次,趙繼偉也扮演了關(guān)鍵的角色,他的控球能力和戰(zhàn)術(shù)組織的大局觀在國內(nèi)后衛(wèi)中都是頂級的,能夠很好地分擔(dān)郭艾倫的壓力,同時讓球隊多出一個進(jìn)攻發(fā)起點,進(jìn)攻方式更為多樣,令對手防不勝防。
郭艾倫和趙繼偉在亞錦賽上出色發(fā)揮,讓球迷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遼寧這片土地上,因為這里被稱為中國籃球后衛(wèi)的搖籃。
2008年,趙繼偉因為在體校比賽中表現(xiàn)突出,被選拔進(jìn)入遼少梯隊。那時候,他第一次認(rèn)識了大自己兩歲的師兄郭艾倫。嚴(yán)格來說,二人在一起接受訓(xùn)練的時間并不多。當(dāng)時的郭艾倫已經(jīng)是希望之星,入選國少,參加大賽。趙繼偉則沿著郭艾倫曾經(jīng)的腳步,在進(jìn)入遼少之后繼續(xù)錘煉基本功。
兩年之后,當(dāng)郭艾倫以17歲的年紀(jì)成為國手,開始涉足CBA的時候,趙繼偉也在眾多少年中脫穎而出,成為遼寧全
運(yùn)會U18梯隊的儲備力量,隨后開始在國際大賽中揚(yáng)名,逐漸引起了CBA教練的注意。
遼寧籃球的青訓(xùn)體系如同老工業(yè)基地那些精密的生產(chǎn)線,按照固定的模式,培養(yǎng)出一代代優(yōu)秀的籃球人才。盡管兩人進(jìn)隊時間不同,但接受的是同樣方式的訓(xùn)練,聆聽的是同一個教練的指導(dǎo),烙下的是同樣的“遼寧”印記。

兩個同樣才華橫溢的年輕后衛(wèi)之間總是有聊不完的話。在趙繼偉升入一隊之前,兩個人的交集主要在夏訓(xùn)中。一線隊和青年隊經(jīng)常進(jìn)行教學(xué)比賽,兩人直接交手的機(jī)會非常多。對于趙繼偉來說,郭艾倫是自己追趕的目標(biāo),也是鞭策自己進(jìn)步的動力。在郭艾倫眼中,趙繼偉同樣是一個可以和自己分享打球心得,一起磨練球技的好兄弟。
當(dāng)兩個人終于進(jìn)入遼寧一線隊之后,經(jīng)常可以看到他們訓(xùn)練后留下來單挑的身影,最喜歡的PK方式就是面對面抗干擾情況下三分球投籃,有時也會進(jìn)行斗牛式的技巧對抗。兩個年輕人你來我往,互不服輸,常常是場邊的隊友們都換完衣服了,他們還沉浸在單挑的快樂之中。
師出同門的淵源,加上朝夕相處的熟識,讓兩個人之間有著充分的默契。當(dāng)這種默契在賽場上得以體現(xiàn)的時候,人們看到了一個強(qiáng)勢的雙控衛(wèi)組合!
當(dāng)亞錦賽奪冠的喜悅隨著時間的漸漸淡去,球迷們的注意力逐漸回歸到CBA聯(lián)賽。對于這一對兒雙控衛(wèi)組合,球迷們自然有更多的期待,盼望他們在聯(lián)賽中奉獻(xiàn)出更多精彩的表演。
或許人生的道路注定不會一路平坦,在告別亞錦賽到迎來聯(lián)賽的這一段時間里,郭艾倫和趙繼偉有著各自的不順。
最受人們關(guān)注的無疑就是郭艾倫的續(xù)約風(fēng)波。當(dāng)亞錦賽前爆出他尚未與遼籃完成續(xù)約的時候,并沒有多少人為此擔(dān)心,認(rèn)為那只是因為國家隊的集訓(xùn)耽誤了一些談判進(jìn)度。隨著中國籃協(xié)第二次公布新賽季注冊球員名單中仍然沒有他的名字,媒體不斷爆出談判分歧、郭艾倫究竟何時才能和遼寧簽約的疑問,幾乎成為貫穿整個10月的主題。
且不談續(xù)約背后的種種分歧和內(nèi)幕,單純從遲遲不能續(xù)約來看,無論對郭艾倫還是遼寧隊,都是一種損失。郭艾倫不能順利簽約,意味著他和俱樂部之間的分歧還沒有消除,很可能影響他的情緒。如果最后迫于無奈簽約,那么,他帶著情緒打球,在聯(lián)賽中能否有穩(wěn)定的發(fā)揮?郭艾倫遲遲不能歸隊,已經(jīng)使他與新外援蘭多夫之間的磨合時間越來越少,這對球隊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兒。

趙繼偉的情況又不相同,在亞錦賽后回到遼寧隊,他很快投入了訓(xùn)練,并且為新賽季做好了充分的準(zhǔn)備。但是在季前賽上,意外受傷為他的新賽季蒙上一層陰影。肩膀脫臼,這個傷勢不算太嚴(yán)重,但是需要靜養(yǎng)一段時間,甚至可能影響常規(guī)賽初期的一些比賽。
年紀(jì)輕輕,就登上了榮譽(yù)的高峰,或許命運(yùn)從來都是公平的,就是要看他們?nèi)绾慰朔部琅c磨礪,然后再成長。相信當(dāng)他們擺脫了各自的不順之后,會在聯(lián)賽中讓人們看到更多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