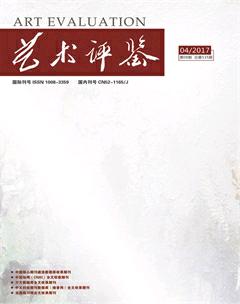音樂劇《花木蘭》唱段《我希望》演唱探究
麥喜曉
摘要:音樂劇的發展已有百年的歷史,百老匯的音樂劇、倫敦西區的音樂劇更是聞名遐邇,《貓》《悲慘世界》《媽媽咪呀》等音樂劇造就了無數的經典唱段,正是這些優秀的作品推動著音樂劇蓬勃發展。20世紀80年代音樂劇開始傳入中國,在探索發展的前進道路當中音樂劇《花木蘭》應運而生,它是中國人對音樂劇探索中的一次重要成果。本文將對音樂劇的起源、《花木蘭》的創作背景作概述,對該劇中的經典唱段《我希望》作演唱探究。
關鍵詞:音樂劇 《花木蘭》 《我希望》 演唱技巧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08-0024-02
一、音樂劇《花木蘭》
音樂劇也稱“歌舞劇”,它起源于十九世紀的英國,前身是“輕歌劇”“喜歌劇”和“黑人劇”。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音樂劇迎來了黃金時代,優秀劇目開始大量涌現。音樂劇與歌劇有相似之處,但其獨特之處在于將“音樂、歌曲、舞蹈、對白”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現代音樂劇廣泛的采用高科技舞美技術,運用流行音樂元素與流行樂器的編制,在演唱方面也不一定采用美聲唱法,劇中并無“宣敘調”與“詠嘆調”的區分。
音樂劇《花木蘭》由中國歌劇舞劇院獨立創作,首演于2004年。該劇由郝維亞作曲,喻江、邱玉璞作詞,凝結了老中青三代藝術家的創作智慧。全劇圍繞“信仰會帶來奇跡”這一主題展開。與傳統《花木蘭》的故事不同,音樂劇《花木蘭》在劇中注入了大量的現代元素,在人物塑造方面“美好的愛情、殘酷的現實、異域風情”為“花木蘭”這個傳統人物賦予了現代意義;在音樂方面“電子音樂、吉他、流行音樂”等現代樂器的運用,增加了“花木蘭”音樂形象的現代感。
在接受李詩原的采訪時郝維亞說到:“《花木蘭》講究戲劇性與抒情性的統一,作曲家并沒有采用傳統的主題貫穿發展手法,更沒有讓音樂去展現戲劇張力,而是把重點放在描繪劇中人物的內心和情感揭示上。”作曲家用抒情的旋律和抒情性樂器展現出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情感矛盾以此去推動戲劇性發展。在該劇中,單曲比整體的戲劇性音樂架構更加重要。
二、《我希望》的創作背景
與傳統的《花木蘭》表達的“孝”不同,音樂劇版《花木蘭》主要的表達的是“愛”。全劇講述了國家邊疆戰事告急全國征兵,征兵花名冊上赫然寫到了花木蘭年邁的父親花弧的名字,木蘭得知此事后想到父親年事已高,弟弟花木棣年紀尚淺,遂決定用弟弟的名字替父出征。而木蘭的青梅竹馬白玉溪也決定同花木蘭一并前往戰場,守護自己的愛人。殘酷的戰場掩埋了花木蘭的性別,卻點燃了木蘭與玉溪的愛情,在戰火中兩人互相扶持,最后贏得了美好的結局。《我希望》出現在劇中第一幕第二場,是女主角花木蘭的經典唱段。該曲體現了花木蘭從得知年邁的父親將被征兵入伍的恐懼迷茫,到幾經掙扎后決定拋開恐懼毅然決定替父從軍的勇敢。這是一首女高音作品,適合用美聲唱法演唱,曲調開闊抒情、氣息綿長、旋律寬廣、節奏抒情、藝術性強。演唱該曲須有一定的演唱基本功,在聲音方面不僅需要很好的技術處理,在情感演繹方面也需要演唱者深層次的剖析歌曲的音樂內涵,才能在二度創作當中唱出“愛與希望”。
三、演唱技巧的處理
《我希望》作為一首音樂劇中的女高音獨唱歌曲,對于聲樂技巧要求很高,而歌唱中的各技巧則需要服從于各音樂要素。下面筆者將根據歌曲的戲劇內容將該曲分為三個部分,從歌唱的氣息、歌唱的語言、歌唱的情感三個角度去探析該曲。
(一)第一部分:閨閣中的女子
音樂起始于女高音的中音區上,旋律呈波浪式進行,以兩個P的力度開始,每分鐘62拍。木蘭的形象在音樂的前半部分是憂愁、恐懼與迷茫的,訴說式的演唱方式最能表達她的情感,氣息需要均勻的吐出,聲音壓著氣息走,自然流動的聲音才能表現出花木蘭此時還是一個閨閣中的女子。彭曉玲在《聲樂基礎理論》中提到“歌唱在呼氣的階段中進行,在歌唱的過程中需要體現對抗和平衡的狀態,在唱連貫的慢速的句子時呼吸之間始終體現著該感覺。”在咬字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元音之間的連接,要做到咬字清晰。值得注意的是歌曲中的三個音程大跳和句末長音。音程大跳在音樂中起著情感推動的作用,也是演唱的難點。第一個大跳出現在音樂的起始句“我希望”,音樂的開始需要我們用一種半聲的有控制的演唱,軟腭在元音“o”和“i”稍作調整,輕盈的掛上鼻咽腔,此時是情之所起,是含蓄的。第二和第三處大跳是一個八度大跳,分別是“甜蜜的夢啊”和“美麗的傳說”,音樂中這兩個句子是音樂第一部分的高潮,木蘭此時的情感是激動且迷茫的,演唱這個地方,氣息要起著首要的支撐作用,兩肋打開讓橫膈膜下沉作為支點,口腔圓潤舌根放松讓聲音自然的往前送。盡管旋律有所拉寬,也要把握演唱中的整體情感,不能將該部分的大跳唱得聲音重、強。“句末長音”是句子結束也是樂段的終止,保持聲音高位共鳴,通過共鳴腔震動獲得泛音,控制音量自然的結束,達到直擊心靈的效果。
(二)第二部分:勇敢的花木蘭
歌曲的中間部分展現的是花木蘭堅毅勇敢的性格,以及暗自替父從軍的決心,她將自己的眼淚掩藏起來,寄希望于月光,拋開恐懼與憂愁。演唱情感與前一部分形成鮮明的對比。該部分的旋律與第一部分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樂段的結尾部分旋律上行的處理。相同的旋律在不同的和聲襯托下表現出了木蘭性格中的張力與她剛毅的一面,結尾處的旋律上行表達了木蘭從軍的決心,也為引出轉調段落埋下伏筆。首先在演唱力度上該部分與上部分要形成鮮明對比,行腔咬字要有一定的力度,音質飽滿,情感隨著旋律的升高而高漲。第一個句末長音“愛的牽掛”在音樂中起到了情感肯定的作用,表達了木蘭決心要拋掉憂愁和恐懼,在演唱中需要控制氣息的呼出需要呼吸韌性的支持,弱音往往表達了內心深處的情感的分量,在演唱中為了表達音樂情感的延伸,呼氣也要作相應的延長,做到聲斷氣不斷,聲音才能直擊心靈。第二個句末長音“天亮”是該段落的難點。“天亮”二字都是在高音區上的長音,“天”字的六拍延長、“亮”字三個F的力度,要求我們在歌唱中高音要加強呼氣的氣勢。金鐵霖教授在《淺談我的聲樂訓練方法》中指出“我們知道,嘆氣狀態是向下的又是放松的,這是符合歌唱的氣息要求的。”體現呼吸堅實有力的支持時身體不能僵硬,要松弛有度才能更好的支持我們的高音演唱。
(三)第三部分:和平英雄女戰士
歌曲的第三部分,由F大調升至降A大調,戲劇張力及演唱情緒達到全曲之最。這一部分是中間部分后半段的轉調模進,演唱情緒在承接上一段的基礎上更為爆發。這時的木蘭已經表現出了堅定的替父從軍的決心,此刻的恐懼憂愁已經完全拋之腦后,她期待著戰爭后的和平。相同的歌詞在更為高亢的旋律下表現出的是更加果敢的心。旋律在高音區上級進環繞式的進行,連續的高音要求演唱者的氣息始終要有強有力的支持,聲音要更加的深厚飽滿,咬字時注意共鳴腔體的打開,喉頭下落、牙關打開、軟腭保持抬起,聲音線條明朗有指向性。此時的木蘭不再是閨閣中的女子,她是一個期待和平的女戰士,因此強勁有力的聲音才符合此刻的人物形象。“此刻我們一起等待天亮”是全曲的結束句,它是木蘭慷慨激昂后內心的升華,也是對和平的無限渴望。演唱時要回到“以說帶唱”的聲音形態,“天”字的五連音要打開上共鳴腔,讓聲音在共鳴腔內輕聲環繞,“亮”字從中音區向上八度滑至高音區,要以哼唱的方法延長弱收,使全曲在無限的遐想當中結束。
四、結語
音樂劇《花木蘭》給人以一種浪漫主義風格的氣息,旋律的西式化,浪漫的語言,基本為西方化的和聲旋律,帶給了觀眾不一樣的感受。將古老的故事賦予現代的意義使現代觀眾更容易接受及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我希望》進行演唱研究,可為演唱者對花木蘭這一人物塑造形象、表現人物性格做參考。該曲的戲劇張力與演唱技巧也可為女高音訓練二度創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演唱該曲需要有很強的聲樂基本功與音樂素養,希望其他演唱者可以借鑒學習。
參考文獻:
[1]彭曉玲.聲樂基礎理論[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顯舟.重看《花木蘭》[J].音樂周報,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