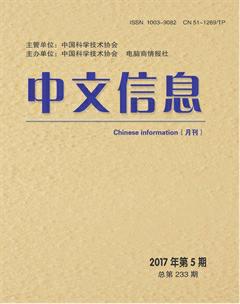設計社會治理法治化評價指標的總體思路
劉翀
摘 要: 將社會治理納入法治的軌道已經成為共識和趨勢,而社會治理的法治化需要設計相應的指標體系來予以評估和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在宏觀上應體現這樣一些思路,即將社會治理體制、模式與社會治理結構作為建構評價指標體系的著力點,同時體現社會治理的動態性與過程性等特征,體現多元主體的互動與參與等內容,體現從傳統的“管理”向現代的“治理”跨越等理念。
關鍵詞:社會治理 治理結構 多元主體 動態過程 參與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7)05-0260-01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將社會治理納入法治的軌道已經成為共識和趨勢,而社會治理的法治化需要設計相應的指標體系來予以評估和推進。從目前的掌握的資料來看,專門就社會治理法治化來設計評價標準及相應評估指標體系的并不多見,實踐中主要是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口號提出之后,國內部分地方所進行的以“社會管理法治化”為目標的努力。例如湖南省長沙市強調要“加快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化進程”,并為此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舉措;[1]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在社會管理法治化及評價指標體系建設方面也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構想與做法。盡管這些嘗試是推動區域社會治理向法治化目標邁進的重要努力,但其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本文以為,對社會治理法治化設計評價標準或指標體系,在宏觀上應體現社會治理模式與結構的范式轉換,治理過程的動態性,主體上的多元互動和參與以及理念上從傳統的“管理”向“治理”跨越等思路。
一、以社會治理體制、模式與社會治理結構為中心來設計
社會治理法治化的評價標準及指標體系在設計上可以根據社會治理的具體領域和內容來進行,即從現代法治的視角和立場出發,梳理出具體行業或部門及各類主體在參與社會治理時應當遵循的實體性標準。但社會治理的任務極其繁重,內容十分旁雜,涉及到民生保障,公共服務與公共安全,流動人口與特殊人群管理,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網絡監管,社會組織的培育與發展、社會糾紛的防范和化解,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社會管理隊伍建設等方方面面,要想做到巨細無遺并不容易。而且當下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又使整個社會日益呈現出開放性特征,社會關系變動不息,新情況新問題紛至沓來,不僅帶來社會治理具體內容的日新月異,而且也給按照治理內容來設計包羅萬象的指標體系造成了困難。為此,應當以社會治理格局、體制建設與社會治理結構的范式轉換為切入點和核心,注重探索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各部門與領域應當普遍建立的體制性指標和應當普遍遵循的操作機理,并以此為核心來設計評價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指標體系。筆者認為,建立什么樣的治理體制,謀求怎樣的治理模式與治理結構,遵循何種運作機理是社會治理法治化中最具首要性和根本性的問題,當前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很多問題無不與社會治理體制不健全、機制不合理及治理模式未能及時轉換等密切相關,這些可以也理應成為對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予以評估的著力點。
二、體現社會治理的動態性與過程性等特征
現代法治的范式并不統一,有關法治的理想類型與具體標準在理論上頗多爭議。但在形式法范式與實質法范式深刻對立進而引發西方法律傳統的危機之后,現代法治的一個明顯的轉向是開始普遍強調法治的程序主義特征,強調法律的治理是一個能不斷回應社會變遷與需求的動態過程,而非僵硬地固守規則和照搬法條或強加某種實質性的價值立場。社會治理的法治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將這種程序主義的法治觀融入其中,進而將社會治理看作一個動態的過程,強調通過此動態的治理過程來吸收不滿、化解矛盾和解決分歧,最終在各種社會事務上,達成政府、民眾等各類主體均可接受的結果。事實上,在利益分化和價值多元的當下,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的“善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被視為是以過程為指向的,這恰如在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研究報告對治理的定義指出的那樣,“治理更多是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管理共同事務的持續互動過程的意義上被界定的,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2]為體現社會治理的動態性與過程性,在治理環節上,要使管理關口前移,要從重事后處置向更加重視源頭與過程的治理轉變,以此來努力擺脫事后疲于應對的被動局面,盡可能使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在動態的治理過程中被化解吸收。此外,要體現社會治理的動態性和過程性,還應特別注意加強社會治理過程中的程序建設,這意味著有關社會治理的決策與決策的執行要遵循有關的程序性制度規定,決策過程中的信息要充分地公開、透明并易于理解,要通過建立和完善社會治理中相關的程序性制度并維護其運作來真正破解社會治理中的難題。相關的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在設計時自然應充分體現社會治理作為一個過程所應具有的動態性等特征。
三、體現多元主體的互動與參與等內容
當下我國的社會治理應當蘊涵大眾參與及社會公正等理念,謀求多主體間的廣泛溝通和交流,強調國家與社會認同合作基礎上的共同參與和管理。因此,無論是之前的“社會管理”還是當下強調的“社會治理”,都不應簡單地將理解成政府作為單一管理主體對社會進行的管制。但在實踐中,部分地方傾向于將社會管理或社會治理的主要內容看成是“政府管理社會”或“政府治理社會”,并進而將政府管理或治理社會理解為防范管控社會,通過強化甚至擴張權力來編織嚴密的防控之網將社會一網打盡。雖然在這過程中也強調法律的作用,但法律具有深厚的便利管控的工具主義色彩,容易輕視以人為本、公共服務和權利保障等蘊涵于現代法治背后的那些價值追求,而在法律執行過程中則強調管理對象服從和配合的義務,如此,很容易窒息政府以外的其它社會主體的生機與活力,并在法律數量不斷擴張的過程中產生“治下不治上”、“治人不治己”和“治民不治官”等法治異化現象。當下我國的社會治理應是一種包括政府管理在內的,有全社會參與的,多中心與開放式的公共治理。在社會治理過程中,黨委是領導性的力量,政府是主導性的力量,但領導和主導并非包攬,而是以多元治理力量的存在和尊重為前提的,除黨委和政府外,其它力量也參與其中并與政府形成互動。這種治理模式或結構的轉換與現代法治所強調的國家與社會、權利與權力、私域與公域適當分離及多元、互動、平衡的發展取向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在其相應的法治標準與指標體系的框架中,就應當體現和明確社會治理中的多元主體,各自的職權、功能和角色定位,相互間的參與協商與協同配合關系,既要充分體現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又要同時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協同、自治作用,確保各種社會力量能夠形成推動社會和諧發展、保障社會安定有序的合力。為此,社會治理法治化指標體系的設計就不能只針對黨委和政府,也不能只以政府為中心,把社會治理僅當成政府管理,還應將各類社會組織乃至普通公民納入到評價指標之內。
四、體現從傳統“管理”向現代“治理”跨越等理念
在改革開放之前,與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的封閉保守等特征相適應,我國的社會治理是一種靜態的管理模式,強調以管、控、壓、罰等壓制型手段來實現管理目標,維持社會秩序,缺少平等對話、溝通、商談等管理理念與措施。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社會管理的實踐雖有變化,但仍呈現出“重管理輕服務,重控制輕商談,重秩序輕權利,重結果輕程序,重經濟效率輕社會公平”[3]等一系列特征,與現代社會治理的理念取向背離太多。而對社會治理法治化的評價,實質上是要以法治的標準來衡量社會治理水平,這勢必要求社會治理水平的評價標準或指標體系的設計能體現現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從而令其能對社會治理的實踐工作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進而使社會治理方式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為此,社會治理法治化的評價標準與具體指標體系應當體現公共服務理念,以人為本理念,執法為民理念,商談溝通理念,權利保障理念、法治思維理念等現代法治理念與價值取向,以此來克服傳統的“社會管理”在理念與實踐操作上的誤區及諸多不合時宜的做法。
參考文獻
[1]中共長沙市委長沙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長沙市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化實施綱要》的通知[EB/OL].http://www.changsha.gov.cn/xxgk/szfgbmxxgkml/
szfgzbmxxgkml/szffzb/tzgg_1966/201206/t20120619_337724.html.
[2]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5).
[3]龔廷泰.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發展的法治實踐動力系統[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