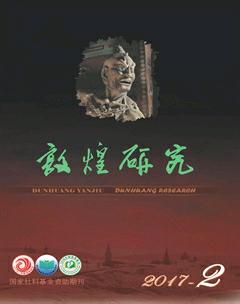《張淮深墓志銘》與張淮深被害事件再探
楊寶玉
內容摘要:本文主要根據法藏敦煌文書P.2913V《張淮深墓志銘》及從非常著名的《張淮深碑》抄件(S.6161A+S.3329+
S.141564+S.6161B+S.6973+P.2762)卷背詩文中新找到的相關記述,對這些文書及其折射的歸義軍史諸問題進行了辨析考證。指出:《張淮深墓志銘》為葬后補寫,當撰于索勛當政期間,即景福二年至乾寧元年(893—894),略晚于同是張球所撰作的《索勛紀德碑》;通過對上述文書及當時敦煌史事的分析可知,索勛掌權后曾有過遷改葬張淮深及其諸子以安撫張淮深舊屬等舉動,表明在張氏家族的內訌爭斗中索勛的態度相對和緩,不像張淮鼎、張議潮十四女及李氏諸子那樣激烈;與張淮深同時遇害的主要就是其與陳氏夫人所生六子,并無陳氏本人,張淮深其余兒子則因非陳氏所生而沒有死于此難,推測張淮深當與諸嫡子政見一致,而諸庶子在此次血腥政變中的地位與作用特殊;張球撰作上述文書時非常用心,遣詞用字均仔細斟酌考慮,透過其于字里行間的隱晦表述,我們既可以索解出部分研究線索,又可以感受到張球與張淮深感情之深厚與行文之老到。
關鍵詞:張淮深;張球;索勛;敦煌;歸義軍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7)02-0064-06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textual study on P.2913, Zhang Huaishens Epitaph, collected in France and the related records on the back of the manuscripts Stele Inscription about Zhang Huaishens Construction of Caves and Related Commentary, both of which cast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Gui-yi-jun regime.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Zhang Huaishens epitaph was added after his burial and might have been written in the period when Suo Xun was in power, namely from the second year of the Jingfu era to the first year of the Ganning era (892—894), a little later than the creation of the Stele Recording of Suo Xuns Merits, written by the same author, Zhang Qiu. By analyzing the above-mentioned manuscripts and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Dunhuang at that time, it is known that Suo Xun had reburied Zhang Huaishen and his sons after coming into power in order to appease the former followers of Zhuang Huaishen, indicating that Suo Xun was relatively moderate in resolving the internal strife of the Zhang Family, unlike Zhang Huaiding, the fourteenth daughter of Zhang Yichao, and the sons of the Li Family further noted in relevant texts. Those who were killed in one mentioned purge include the six sons born by Zhang Haishens legal wife, Lady Chen, though not including Lady Chen herself. Zhang Huaishens other sons were not killed because Lady Chen was not their birth mother. From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Zhang Huaishen likely shared the same political views as his sons born by his legal wife, and that his other sons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is bloody coup. Zhang Qiu was very careful with the wording of these inscriptions and epitaph and from his somewhat oblique statements we can not only obtain some clues about the historical event, but even feel Zhang Qius affection for Zhang Haishen through his excellent penmanship.
Keywords: Zhang Huaishen; Zhang Qiu; Suo Xun; Dunhuang; Gui-yi-jun
在張氏歸義軍史諸政治事件中,大順元年(890)二月發生的張淮深及其主要親眷集體遇害一事一直備受學界關注。但是,目前學界已知的記述這一事件的史料非常少,主要就是法藏敦煌文書P.2913背面所抄《張淮深墓志銘》,而該銘文的表述又相當隱晦,以致不同學者對這一事件的解讀異見紛呈,對此事與其前后歸義軍史某些現象之間的聯系的認知也有待深入。
筆者在整理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張球作品的過程中,對署名張景球,實即張球{1}所撰《張淮深墓志銘》進行了重新校理,并注意到由多卷英藏或法藏敦煌文書拼合而成的《張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詩文(作者均為張球)中存有與《張淮深墓志銘》有關的記錄,遂結合兩者并參考以其他相關文書勉力探究,逐漸形成了幾點看法,今特借參加此次學術會議之機,略陳管見,不當之處,敬請專家學者教正。
一 《張淮深墓志銘》并非寫于銘主被害后不久之補論
關于《張淮深墓志銘》的撰作時間,學界主要存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主張當撰寫于張淮深被殺后不久,如鄭炳林《〈索勛紀德碑〉研究·碑文作者張景俅有關問題》{2},即認為該銘文寫于大順元年(890)二月廿二日后不久。另一種觀點則傾向于索勛當政時期。例如,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第2章《歸義軍歷任節度使的卒立世系與稱號》即云:“從墓志中用大順紀年,以及‘豎牛作孽,君主見欺等詞句看,墓志應是張淮深的政敵張淮鼎死后才寫成的,很可能完稿于892—894年索勛執政期間。”[1]再如,李麗《關于〈張淮深墓志銘〉的兩個問題》[2]更提出“張球撰《張淮深墓志銘》在《索勛紀德碑》之后”,“當在893年初”,該文又稱是索勛禮葬了淮深夫婦及其六子,時間則在刻《索勛紀德碑》之后不久。筆者基本贊同后一種觀點,并擬作一些具體論證與補充。
考本件文書為墓志銘抄件,這一特殊體裁自然與推論銘文撰寫時間有關,因為墓志一般都是要隨棺下葬的,即墓志銘的撰寫時間當在下葬之前。那么,敦煌地區一般是在何時埋葬逝者呢?著名敦煌民俗學家譚蟬雪先生曾指出“葬才是出殯”,“敦煌的出殯日期以七日為極限,可少于但絕不能超過七日”[3],還據當時敦煌社會上流傳的《十王經》對個中原因進行了解析。據此可知,由于深受《十王經》影響,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行用的喪俗是七日內下葬。具體到張淮深,也不應例外,何況他是政變中的失敗者,不可能被超期停棺祭拜,他的入土當然應在被殺后不久的當年二月月底之前。
這樣,如按常理推測,《張淮深墓志銘》就應撰寫于銘主去世七日之內,即890年二月二十二日至月底之間,前面介紹的關于《張淮深墓志銘》撰寫時間的第一種觀點應是基于這種考慮的。
但是,《張淮深墓志銘》中年號的使用情況卻并不支持第一種觀點,因為該銘文在記敘張淮深去世時間時使用的是“大順元年二月廿二日”。大順元年時當公元890年,該年正月初一改元大順,但其時正當唐末離亂,敦煌又偏處西陲,不可能在一個多月后即獲知改元消息,其時敦煌民眾仍在沿用此前的“龍紀”年號,我們在敦煌文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證。比如,同樣是張球撰寫的《李明振墓志銘》(P.4615+P.4010V)即記銘主卒于“龍紀二祀七月十有六日”{1}。考“龍紀”年號僅用一年,所謂“龍紀二祀”正是不知改元而沿用過時年號的。既然890年七月中下旬敦煌尚不知改元,五個月前的二月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所以,僅從年號使用情況考慮,已改用新年號的《張淮深墓志銘》不可能撰寫于890年七月下旬之前,而只能是在銘主入土至少半年后補寫的,情況非常特殊。
那么《張淮深墓志銘》究竟是在怎樣的情形下產生的呢?
二 張淮深的葬儀及其折射的敦煌政治形勢與《張淮深墓志銘》撰作時間推論
這三個問題密切相關,故擬合在一起探討。
一般說來,補寫的墓志銘均應是為遷葬改葬之類的第二次葬儀準備的,所以,存留至今的這件《張淮深墓志銘》足以說明銘主此前曾經歷過一次葬儀。
實際上,P.2913V《張淮深墓志銘》對銘主的第一次葬儀是進行了追記的,即:
公以大順元年二月廿二日殞斃于本郡,時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鄉漠高里之南原,禮也。兼夫人穎(潁)川郡陳氏六子:長曰延暉、次延禮、次延壽、次延鍔、次延信、次延武等,并連墳一塋,以防陵谷之變。
這段銘文中十分引人注意的一語是“并連墳一塋”。根據學界對890年前后歸義軍政權政治格局的研究,張淮深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中被殺害的,在血腥政變中獲勝的政敵張淮鼎等不可能厚葬淮深及其諸子。因而可以推知,張淮深經歷的第一次所謂葬儀必然十分凄慘不堪,其時張淮深等人當是被草草掩埋甚或拋尸荒野(也不太可能有墓志銘隨其一起下葬),以致后來張球追記其事時,出于不忍等原因,不得不用“并連墳一塋”來進行掩飾。
既然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件《張淮深墓志銘》系應用于二次葬儀,按理說,遷葬改葬時撰寫的銘文該對遷葬改葬的原因、過程等等有所交代,但是,這篇銘文中卻沒有本不應缺少的相關說明。何以至此呢?這應與這篇銘文撰作的時間與背景密切相關。
可以撰文紀念張淮深,說明其時的形勢已比張淮深被殺時舒緩,但銘文對張淮深的死因欲言又止、含糊其辭,又表明政治環境并未發生徹底轉變,張淮深及其諸子的被害仍是敏感話題,不得不觸碰時需要拿捏分寸,把握力度。
上一節我們已通過對年號使用情況的分析揣測了《張淮深墓志銘》產生的時間上限,那么其下限呢?其時的政治環境又如何呢?
綜合考慮9世紀最后10年敦煌的政治形勢,殺淮深而自立的張淮鼎掌權時恐怕不會允許重葬淮深并于墓志銘中書寫“堅(豎)牛作孽,君主見欺”,“政不遇期”,“殞不以道”之類的話,是知這篇銘文不會作于張淮鼎掌權時期。
據原本立于莫高窟第148窟的《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中“于是兄亡弟喪,社稷傾淪,假手托孤,幾辛勤于茍免。所賴太保神靈,辜恩剿斃,重光嗣子,再整遺孫”,嫁給李明振的張議潮第十四女與張淮鼎的政治態度是一致的,因為碑文中的兄弟當是指其親兄弟張淮詮與張淮鼎{2}而不是堂兄弟張淮深。因而《張淮深墓志銘》也不可能撰寫于索勛被殺后的李氏實際當政時期。
而索勛接替張淮鼎執掌政權時卻會有些不同。一方面,在張議潮子女與張議潭后人的爭斗中,身為議潮女婿的索勛必然隸屬于議潮一系,并因此而得以在議潮二子和原本頗有資歷與實力的女婿李明振死去之后接掌政權。但另一方面,在這類骨肉相殘的政治較量中,作為張家女婿的索勛多少會有自己的想法,未必像張淮鼎與李氏那樣決絕,更重要的是,當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必然要具體考慮當時的政治態勢,采取靈活務實的方式處理與淮深遺留的政治勢力之間的關系,以鞏固自己的地位,而未獲安葬的張淮深等人的遷改葬正具有象征意義,可以給張淮深的昔日親知些許安慰,是拉攏淮深舊屬的必要手段,精明的政客不會不就此做些文章。其時敦煌的政治形勢應該比較微妙:張淮鼎雖逝,李氏的權勢卻仍然強大。這樣,索勛的態度也不便太過明朗,做不到隆重禮葬張淮深及其諸子,也不太可能將他們遷往節度使家族墓地{1}。換言之,“政不遇期”“殞不以道”的張淮深的二次葬儀的規格也高不到哪里去,對其葬身之處稍事修整并補刻增埋一方墓志,恐怕是比較合時宜的折中辦法,而墓志銘中又沒有太多可說和敢說的,難怪作者張球慨嘆“哀哉運戲(嚱)”“天胡鑒知”,并為“千古之后,世復何之”而憂心忡忡。
總之,筆者贊同《張淮深墓志銘》成文于索勛時期的觀點,再考以敦煌市博物館藏《大唐河西道歸義軍節度索公紀德之碑》所署“節度判官權掌書記朝議郎兼御□(史)中丞賜緋魚袋南陽張景俅撰”、“于時景福元祀白藏無射之末”,而《張淮深墓志銘》則署“節度掌書記兼御史中丞柱國賜緋魚袋張景球撰”,后者的撰作時間當略晚于景福元年(892)秋冬,或許當在其后的景福二年左右。
三 “兼夫人穎(潁)川郡陳氏六子”逗斷不同新解與張氏內部矛盾推論
上節引用的筆者關于《張淮深墓志銘》中的那段錄文與學界流行的錄文之間有一處明顯差異,即筆者將“陳氏”視為“六子”的修飾詞,沒有逗斷,而以前相關學者一般均在“陳氏”之后逗斷句,進而認為陳氏也同時被殺。
筆者認為,以前的逗斷既與古漢語語法不合,讀起來很不順暢,又與史實不符。因為如按傳統逗斷計算,同葬的應為張淮深夫婦及其六子,共八人,而筆者新發現的一條相關材料明確記同葬者共為七人,即張淮深和他的六個兒子。
考敦煌文書中非常著名的《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學界習稱《張淮深碑》)抄件的背面抄存了大量詩文{2},但因書寫較為零亂潦草、涂改增補之處與訛文錯字頗多,及漫漶破損嚴重,不少字跡已模糊難辨等原因,迄今沒能引起學界的重視。筆者在研讀《張淮深碑》的過程中注意到這些詩文,并進行了校注整理{3},亦提出并論證了詩文作者為當時擔任節度判官掌書記的張球{4}。在這些詩文中,第十三首詩相當特殊,不但僅寫了三句而未完成(筆者認為這是作者有意為之,其原因很可能是其心中的那一句太過敏感,不便訴諸文字),還于詩題下以雙行小字加了一段注。該詩,特別是詩題和詩題之下的雙行小字均極難辨識。其文曰:
憑□后感懷龍紀二年二月廿二日未□□□時,并身七人列州郊
運偶中興國祚昌,六人□征(?)在敦煌。鵲印已皈逐相路,
注文中的時間與《張淮深墓志銘》所記淮深被害時間完全一致,而注文明確講被“列州郊”(實際上乃是被棄葬荒郊)的為包括張淮深本人在內的共七人。至于詩歌中的“六人”則僅指張淮深與陳氏夫人的六個兒子,之所以沒再提張淮深,是因為詩歌是對張淮深被殺諸子來生前程的祝愿。
陳氏是否死于此難看似是血腥政變中的細節,但是,這個細節卻會促使我們重新考慮張淮深的死因。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陳氏為何沒有死于此難(或許她在890年二月之前就已去世,亦或許其時她雖在世,卻因是女流等原因而沒被殺害,據P.3556《周故南陽郡娘子張氏墓志銘并序》,張淮深的一個女兒即幸存于世,后來嫁入索家),而在于銘文作者特意說明了被害六子均為陳氏所生。
早在1986年,敦煌研究院的李永寧先生即刊發了《豎牛作孽 君主見欺——談張淮深之死及唐末歸義軍執政者之更迭》一文[4],指出:“顯然‘豎牛作孽應為不肖之子造作事端,殘害兄弟,禍亂家室之意。筆者推測,張景球撰寫《張淮深墓志銘》引用此典,顯然不是隨手拈來,無所實指,而是內抑激憤,煞費苦心,采用了一個非常恰當的典故,隱喻殺淮深一家者,并非外人,而是自家兄弟——張淮鼎。”“看來,中央受蒙騙不授淮深旌節,淮鼎以突襲手段殺淮深一家奪取瓜沙歸義大權,就是《墓志銘》‘豎牛作孽,君主見欺的真實含義。”稍后,鄧文寬先生繼而發表《也談張淮深之死》[5],據S.5630《張淮深造窟記》考出張淮深至少還有兩個兒子張延興{1}、張延嗣并未死于政變,進而推論二人為張淮深庶子,并比照《左傳·昭公四年》所記豎牛典故中的人物關系,認為是庶子延興、延嗣等殺了父親張淮深和陳氏生的六個嫡子,然后立淮深的庶母弟張淮鼎為節度使。
關于上述李先生和鄧先生的觀點,筆者認為其中一些具體結論尚可商榷,如稱張淮鼎為張淮深自家兄弟或庶母弟等即與史實不符,但兩位先生對豎牛典故的解讀及分析問題的思路確實值得高度重視。
由于目前已知的相關史料還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筆者對張淮深并非死于此難的其他兒子在事變中的作用地位、自身結局等尚不敢遽斷,但認為他們定然是十分特殊的參與者,心思縝密的張球選取豎牛故事來半揭半掩事件真相的確用心良苦,為千年后的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研究線索。
四 張球與張淮深一家的情誼及張球行文意圖略析
關于《張淮深墓志銘》的作者張球與張淮深一家的關系,我們可以用“異常深厚”來形容,其原因與表現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張球官職的迅速提升主要發生于張淮深時期,張淮深對張球有知遇之恩。根據敦煌文書中保留的張球為當地名人名僧撰作的傳贊碑銘中的作者署銜,可知張議潮當政期間張球一直任歸義軍軍事判官{2},而約在張淮深執政的乾符年間(874—879),張球漸升為節度判官{3},至光啟三年(887)年底之前還兼任了掌書記{4}。如所周知,在唐代藩鎮中,節度判官、掌書記是僅次于副使、行軍司馬等的樞要之職{5},為節度使的心腹喉舌。張球一身兼二職,更加重了文秘之權,在張淮深統領的歸義軍政權和敦煌社會上地位之高不言而喻,對張淮深的萬般感念自然可想而知。
二、張球與張淮深家人也往來密切,相處融洽。法藏敦煌文書P.2568《南陽張延綬別傳》的作者題署為“河西節度判官權掌書記朝議郎兼御史中丞柱國賜緋魚袋張俅撰”,“張俅”乃是張球在敦煌文書和敦煌碑銘中的另一署名,故該傳亦為張球所撰,而傳主正是張淮深之子,即前引《張淮深墓志銘》中提及的與張淮深同葬州郊的張延壽,此傳足證張球與張淮深之子十分親密。更為重要的是,前面引錄的《張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第十三首詩《憑□后感懷》是張球專為張淮深諸子撰作的。從詩題和題下注文看,作者是在憑吊張淮深等逝者之后寫的該詩,注文追憶了張淮深被殺的時間、與六子被棄尸荒郊的慘狀。詩中“運偶中興國祚昌”一句顯示當時的政局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以致作者有了“中興”之嘆。而此時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紀念和祝禱罹難的張淮深諸子,祝愿他們來世再降生敦煌并得掌鵲印(即獲得高官顯位),其情意異常誠摯深沉。
三、在張淮深及其諸子被害后,張球悲痛異常,難以自持。這在《張淮深碑》抄件卷背保存的詩文中多有表露,除剛剛提及的《憑□后感懷》一詩外,該卷背抄存的兩行雜記尤堪關注。這兩行雜記書寫于第九首詩之后,筆跡、墨色等均與全卷一致。第一行雜記自卷子中部寫起,謂:
龍紀二年二月十九日也,心中。
下一行則為倒書:
不可忍,冷氣不下食。
筆者認為這兩行字所表達的文意相聯,應是出于某種特殊情況或特殊考慮而將后半句話倒書。于此我們應認真分析一下雜記的內容。有兩點需特別注意。其一是“龍紀二年二月十九日”,該日距張淮深被殺僅三天。顛覆歸義軍政局的政變的發生應有一個過程,十九日時敦煌的政治天空已不可能風和日麗,而應處于事變高危期,那一天一定發生了某種令張球非常哀痛驚懼的事(或許張淮深夫人陳氏所生的六個兒子是先于張淮深被殺的,其死期正為十九日),以致事后追記時仍不敢明言。其二是“冷氣”一詞,古時該詞系指因哀痛過甚而致的氣逆之癥,如《梁書·孝行傳·褚修》即謂:“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是知張球用此詞隱含了極為深切的感情。關于這兩行雜記的書寫時間,由于今知藏經洞中所存最早的大順紀年文書為S.3880V,題“大順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張一。”{1}故可推知這兩行沿用過時年號的雜記當寫于890年二月至十一月之間。其時掌權者為張淮深的政敵張淮鼎,書寫與張淮深及其諸子被害事有關的文字必然多有顧忌,而在這種情況下張球還能冒險抒懷,其情感之強烈不能不令人喟嘆。
四、作為張淮深曾經的心腹僚佐,張球努力在用自己的詩文記述張淮深的功績,以期傳諸后世。《張淮深墓志銘》中即明確稱撰作該銘文的目的,是要將張淮深的功德“銘于旌表”。但是,在當時還不能暢所欲言的政治環境中,這篇銘文的撰寫難度很大,哪些不該說,哪些該說,哪些不可說,哪些可說,說到什么程度等,都是必須仔細推敲的,作者既要表達個人的真實想法,為與自己情深意厚的上司昭雪,又不能為自己招禍,為此,張球可說是用盡了心思。比如,銘文中一再強調張淮深的正統地位,“乾符之政,以功再建節髦。時降皇華,親臨紫塞。中使曰宋光廷”等語是說張淮深確實得到了唐廷任命,特意提到送旌節官的名字是為了加強真實性,可見張球用心之深。這里的“乾符之政”是說張淮深憑靠乾符年間取得的政績獲得了節度使任命(并非指張淮深是在乾符年間得到旌節的),意在說他得任節度使是當之無愧的,而之所以特意指出是乾符年間取得的政績,自有深意,因為張淮深一生中最可稱道的業績正是達成于乾符時期,并且那段時間張議潮二子尚在京城,敦煌的政績與他們沒有關系,撰碑時只提乾符也安全得多。自張淮深執政后期,歸義軍政權內部矛盾迭起,留給后人的記錄卻撲朔迷離。作為一位長期生活于敦煌、有機會參與見證歸義軍政權諸多樞要之事的外來文士,張球以他獨特的視角與方式對那段歷史進行了頗為隱晦卻十分重要的記述,為千年后的我們留下了異常珍貴的研究線索。
以上筆者通過對《張淮深墓志銘》部分語句的重新解讀和對《張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部分詩文的分析,探討了兩件文書本身及其反映的張淮深遇害事件的一些具體問題。透過這些小問題,我們可以對當時敦煌地區政治形勢的總體情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比如,關于張淮深被殺前后敦煌地區的政治格局,即可據此梳理出其時存在著至少三大政治集團:以張淮深為中心的在政爭中最先失敗的一方;以張淮鼎、李明振夫妻及李氏諸子為中心的先后挫敗張淮深、索勛的一方;以索勛為中心的先接替張淮鼎,后又被張議潮十四女及李氏諸子擊敗的一方。這三大集團之間,前兩者的關系是你死我活,后兩者則是先聯手合作而后針鋒相對。三大集團共同敘寫了那一時段錯綜復雜、糾結纏繞的敦煌歷史,故類似背景認知自當有助于對相關歸義軍史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87.
[2]李麗.關于《張淮深墓志銘》的兩個問題[J].敦煌學輯刊,1998(1).
[3]譚蟬雪.敦煌民俗[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344.
[4]李永寧.豎牛作孽 君主見欺——談張淮深之死及唐末歸義軍執政者之更迭[J].敦煌研究,1986(2).
[5]鄧文寬.也談張淮深之死[J].敦煌研究,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