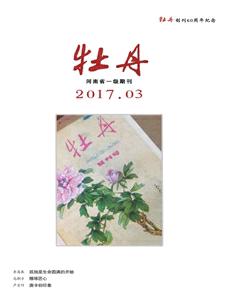從燭光看《拜堂》的藝術特色
王燕顏
燭光這個意象既表現了小說主題的沖突,與主人公的心理活動相映成趣,又展現了《拜堂》的獨特藝術。
臺靜農是新文學鄉土文學的代表,其代表作是小說集《地之子》。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鄉村社會底層人物,主要是抨擊黑暗的現實,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對這些小人物的同情。魯迅對《地之子》評價很高,也有人說:“《地之子》表明了臺靜農的小說創作走向成熟。它奠定了臺靜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臺靜農出生于安徽省霍邱縣的葉家集。葉家集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小鎮,在史河的東岸。因靠著史河,葉家集商業曾一度繁榮。但在近代,這里的經濟式微,民生艱難,民風既淳樸卻又麻木。“在黑暗的野蠻的丘垅上吹送著習習的文明之風,從而構成了如一幅復雜的風俗畫般的時代背景。”臺靜農生于斯、長于斯,這樣的背景也是他小說集《地之子》的背景。
《拜堂》是《地之子》中的一篇短篇小說。故事雖短,卻有自己的藝術表現力。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藝術成就進行深入的研究。有人從地方語言藝術的角度研究《拜堂》,認為《拜堂》運用了許多地方方言,以人物對話表現人物心理活動;有人從表象手法研究《拜堂》,認為這篇小說是“以樂景寫哀景”;有人從小說的題材和敘事方式研究小說的表達藝術,認為《拜堂》不同于《地之子》中其他慘烈的題材,拜堂是好事,同時認為《拜堂》的敘事方式是全知視角加旁知視角的模式,以此來凸顯汪大嫂既有主張又彷徨不安的徘徊形象。
筆者認為,《拜堂》雖然是一篇短篇小說,其藝術成就卻不簡單。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拜堂》的藝術成就,人們會有不同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思考。《拜堂》中人物的矛盾心理,不僅僅是通過語言來實現,小說主題的沖突也不僅僅是通過題材和敘事方式得以展現。小說中頻頻出現的一個意象“燭光”,也可以體現小說的底層人物追求幸福生活與倫理道德的沖突,也可以體現人物矛盾心理沖突。
《拜堂》講述的是一個叔娶嫂的故事。拜堂是民間結婚時的風俗,拜堂結婚當是人生大事、喜慶之事,但臺靜農筆下的拜堂則難令人感受到喜慶之意,反倒令人感到難受、壓抑,甚至是戰栗。因為臺靜農筆下描寫的拜堂不是正常的拜堂,而是汪二以叔叔身份娶寡嫂的拜堂,這有違倫理。嫁娶本是未婚男女的正常追求,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使然,但叔叔娶嫂嫂卻有違倫理,臺靜農通過《拜堂》表達的正是這種人性與倫理的沖突。
《拜堂》通過燭光這一意象將這種沖突以及這種沖突下人的壓抑表現得淋漓盡致。燭光給人溫暖,給人希望之感,但《拜堂》里的燭光不盡然如此,它與小說人物懷有希望卻又不安然的心理活動交相呼應,緊緊扣著小說主題。小說共出現了四次燭光,每次出現都有其特殊的意義。
第一次出現的燭光是小燈籠的燭光。汪二和汪大嫂決定在夜里成親,二更天之后,汪大嫂提了篾編的小燈籠,悄然往田大嫂家去,請田大嫂到家里牽親。在去田大娘家的路上,小說中是這樣描寫的:
“這深夜的靜寂的帷幕,將大地緊緊地包圍著,人們都酣臥在夢鄉里,誰也不知道大地上有這么兩個女人,依著這個小小的燈籠的微光,在這漆黑的帷幕中走動。”
夜本是黑色,黑得無邊際,而這微弱的燭光,紅黃色的燭光,卻是唯一的色彩,它此時給人以希望之感。但較之夜的黑和大,它卻是只是大片黑中的一點。汪二、汪大嫂他們生活在農村,生活困難。汪大嫂喪夫,家里也沒錢給汪二說親成親,汪父卻是一個不事生產的酒鬼。汪大嫂和汪二走在了一起,也許他們有感情基礎,也許他們只是為了能過活下去,他們決定沖破倫理道德,拜堂成親。在苦難的生活中,結婚是喜悅的、溫暖的,但這在強大的倫理道德中,他們這種出于人性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又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那微弱的燭光——它本該是溫暖的,但卻又微不足道。
第二次出現的燭光依然是小燈籠的燭光。這次是從田大娘家回自家的路上。小說是這樣描寫的:
“少傾,她們三個一起在這黑的路上緩緩走著了,燈籠殘燭的微光,更加黯弱。柳條迎著夜風搖擺,狄柴莎莎地響,好像幽靈出現在黑夜中的一種陰森的可怕,頓時使得這三個女人不禁地感覺著恐怖的侵襲。”
第一次出現的燭光是安靜的,而這次的燭光被夜風吹動著,這樣以烘托汪大嫂心中的不安。因為離家越近、離拜堂越近,她與汪二的結合將不被世俗所接受。
第三次出現的燭光是準備拜堂時的燭光。小說是這樣描寫的:
“燭光映著陳舊褪色的天地牌,兩人恭敬地站在席上,頓時顯出莊嚴和寂靜。”
紅黃的燭光映著褪色的天地牌上,顯得肅靜,這是拜堂時該有的氛圍。但拜堂除了該有莊嚴,應該還透露著喜慶,因為拜堂時總會有人聲、總會有人走動,汪二和汪大嫂的拜堂卻是肅靜——沒有賓客,不被祝福。他們的結合有違倫常。
第四次出現的燭光是拜完天地時,汪大嫂讓汪二給他死去的大哥磕頭。小說中寫道:
“全室中的情調,頓成了陰森慘淡。雙燭的光輝,竟黯了下去,大家都張皇失措。”
此處是正篇小說的高潮,也是人性與倫理沖突的高潮。汪二娶妻,是人之常情,但汪二娶大嫂,是愧對死去的大哥的;汪大嫂,寡婦改嫁,是人之常情,但卻不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更何況她是改嫁給亡夫的弟弟?這個“黯了下去”的燭光,正是這種沖突的顯現,又是汪二、汪大嫂此時心中不安、慚愧、戰栗的心理表現。本來就微弱的燭光在這黑夜中暗了下去,那更是微弱不堪。但即使是微弱不堪,它也依然沒有熄滅。這樣的燭光恰恰表現了汪二、汪大嫂他們過活的艱苦卻又堅忍不拔,兩人結合使生活有了盼頭,但這樣的結合又不被世人所祝福。
燭光這一意象的描寫與小說人物主人公的心理活動相映成趣,同時也表現了小說主題的沖突。汪大嫂,是一個有主見的人。她主張牽親,認為要在一起就應該正式在一起,于是她主動去找田大嫂她們作為婚禮見證人。
臺靜農對他們充滿了同情,正如他在《地之子》文末中寫道:“人間的酸辛,我耳邊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
《拜堂》是五四時期的鄉土小說,有其自己的藝術特色。小說借助燭光這一意象,含蓄地表達了人性與倫理沖突的主題,也含蓄地反映了人物內心世界。這樣的藝術表達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知趣,使得《拜堂》有別于一般的鄉土小說。
(廣東信息工程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