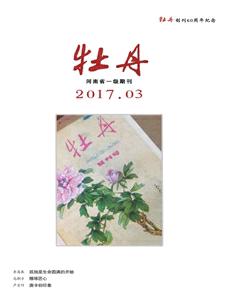從反烏托邦文學的角度分析《白銀時代》
張聰
本文試從反烏托邦文學的角度對王小波的《白銀時代》進行文本細讀,從寫作公司對寫作和斃稿的要求、權力機構對反抗者的懲罰和規訓以及對個體生活的監視與控制等方面,分析白銀時代人們荒謬的生活、個體存在價值和自由意志的喪失。
“烏托邦”(Utopia)一詞源出希臘語,意為“實際上不存在的地方”“烏有之鄉”。該詞被世人所知得益于16世紀英國人托馬斯·莫爾(St. Thomas More)出版的《烏托邦》,此后類似的著作層出不窮。但是,烏托邦思想來源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神話時代。因為從本質上講,它是人類本能的一種心理意識,烏托邦是人的本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是沒有不行的,它表現了人的本質和人生存的深層目的。烏托邦小說大多描寫了諸如理想國(The Repubic)中的政治體制和神話故事中和諧的田園生活方式,表達了人們對理想社會秩序的向往與期待。
反烏托邦文學與烏托邦文學的關系就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而并不是通常認為的作為其對立面出現。如果說在每一個烏托邦的背后有一個反烏托邦,即烏托邦者眼中的現實世界,那么在諸多反烏托邦的背后也存在一個隱秘的烏托邦。反烏托邦文學所描繪的那種整齊劃一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高度集權的基礎上的,在統一的意識形態中,個人沒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它展示的是一個看似完美卻處處充滿危機的世界,在那里物質資源極大豐富,科技文明高度發達,似乎充滿了烏托邦要素,但是個人的主體性和精神自由在絕對權力的控制之下喪失殆盡。
筆者認為王小波的《白銀時代》就屬于反烏托邦文學作品,本文圍繞熱力學課堂上老師的謎語展開:“世界是銀子的。”這句謎語反復出現,意味深長又讓人無限壓抑,“我”最終揭曉答案:在熱寂之后,整個宇宙會同此涼熱,就如一個銀元寶。眾所周知,銀是導熱最好的物質,在一塊銀子上,絕不會有一塊地方比另一塊更熱。而“我”所在的2020年就是這樣沒一個沒有差別、和諧統一的世界,一切看似完美無缺。物質充裕,科技發達,秩序井然。但是,這個未來世界在權力的統一下又充滿了丑陋與殘缺,目之所及盡是沉悶暗淡,陰影時時逼近,個體失去自由,人被無限弱化和壓抑。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詳細論述:
一、審查稿件
在2020年,極權國家雖然已經模糊了,但依然存在權力高度集中并且控制嚴格的機構。人們深受其害,那只無形的權力之手無時無刻不在扼住每一個人的咽喉,個人思想被鉗制,“到處都不是發愣的地方”,自由喪失,只能將時間和精力消磨在打毛衣、做習題集諸如此類無聊且不需要動腦思考的事情上。相對于這些單調機械的事情,寫作可以稱得上是最具創造力的一項工作了。但是,人在公司里只有兩件事可做:槍斃別人的稿子或者寫出自己的稿子供別人槍斃。所以,寫作公司表面的規范與整齊是以犧牲意義為代價的,在機械重復之中日漸消磨人的積極性、創造力和個體性。“我”在寫作公司具有些許權力,除了不斷地寫小說,還要審查下級所寫的小說,監督下級的生活,但是同時又要受到上級“克”的監督與審查。“我”的稿件經常被斃,他人亦是如此,被斃是因為“脫離生活”。在不斷的寫作、被斃、修改中,寫作的人逐漸喪失了描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的激情,只能按照上級的要求在所允許的范圍內不斷修改寫,不能寫“真正的小說”。所有的小說只能依據生活,上級不停地逼問創作者的生活依據是什么,但“什么是生活,什么不是生活,我說了不算:這就是說,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一旦領導覺得小說內容不符合白銀時代中真實的生活就會遭到槍斃。他們也總是槍斃一切有趣的東西,因為越是有趣,越是包含惡毒的寓意。凡是能引起興趣、引人思考的東西都會引起白銀世界的崩潰,必須棄之不理。最可怕之處在于:“它不僅不許你表達——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規定你應該怎么思想……它盡可能地把你與外面的世界隔絕開來,它把你關在一個人造的宇宙里,你沒有比較的標準。”
二、監視私人生活
在審稿制度的運作下,寫作公司職員的思想被牢牢地控制住了。但是,白銀世界對人們的掌控不止于此,上級也會通過吃飯來顯示自己所擁有的權力。“當人們想找一種最管用的方法確認自己的權力,想說清楚這種弄權力的大小、多寡和由來時,吃就成了最重要的歷史記錄。”所以,吃飯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控制手段。不論是“我”陪同上級“克”去吃飯,還是辦公室的小職員陪同我去吃飯,身處下級的人都認為是一種折磨,他們沒有權力拒絕這種要求,必須前往;在菜品上也沒有選擇權,“我”只能忍受冷蘆筍,就像我的下級必須吃下饸烙面和鹵煮火燒。在這里,吃飯雖然不同于純粹的政治生活,人們似乎擺脫了平常所屬的群體和類別,是以個體的狀態參與其中。但是,實際情況是吃飯這種個體的交際方式也被深深地納入權力的管轄之下。
當然,這相比于《白銀時代》中對性生活的監視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白銀時代》中,夫妻生活被描述為成年力量間的交媾,成為會議的一項內容,人們像完成任務一樣參與其中,畢竟“對寫作也有好處”。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件事情還需要在考勤表上打勾,以便匯報。夫妻間的情感交流、兩顆心靈的碰撞成為一項冷冰冰的要求,長此以往,夫妻生活變得越來越簡約,敷衍了事。國家機器對個體生活的控制不僅限于公共空間,連最私密的個人生活空間也處在被人觀察和監控之下。無論是監督者還是被監督者,都像是冷靜、理智、客觀的機器人,沒有絲毫情感的投入。在這個世界里,個體徹底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樂趣,個人的自由喪失殆盡。
“我”和老師的戀愛不同于成年力量間的交媾,是真正情感的交流和心靈的慰藉。但作為學生的“我”和老師在這個時代是不同級的,老師在學校充當的是牢頭的角色,“我”是被教育、被管制的下級。所以“我”寫作的這本小說是對這個世界的挑戰和反抗,它能夠被寫出來究其原因是老師的簽字。但是,小說中不符合規范和要求的部分仍然不斷被斃,并且批上一句“脫離生活”。“我”只好反復修改,刪除描寫性愛的段落。個人的生活被全方位地監控,表達的自由也被強制剝奪,被迫成為體制內了無生機的一員。
三、馴服反抗者
在一切同一的白銀時代中,并非沒有人試圖反抗。雖然“在劇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銀世界里好的多”,但領導總會用最殘酷的痛苦,讓人鮮血淋漓地回到白銀世界里來。最初,“我”寫作《師生戀》時也是滿懷激動,以飽滿的感情去創作,在日復一日的被槍斃中,“我”只能依據領導所要求的生活木然地進行寫作和修改。“棕色的”是“我”辦公室里的女同事,她想要寫一部按照自己意愿創作的小說,寫真正的而且是不被允許的小說。“我”得知這個事情就睡不著覺,只能寄希望于她只是隨便說說。這個極具反抗性的女同事在大家眼中是缺心眼的傻瓜,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她不同于那些滿臉倦容、神情呆滯的同事,也因此受到規訓與懲罰。做不被允許的事情就要受到懲罰,“棕色的”被關到竹籠里,手腳被拴住,嘴也被栓住,“這樣她就不能講出大逆不道的語言”。她還曾被送到鄉下去體驗對寫作大有好處的生活,被人輪奸兩次。她在談論自己被輪奸的感受時受到了有關部門的警告,“不要用自己不幸的狹隘經驗給大好形勢抹黑”。權力機構利用暴力手段來懲罰和規訓“棕色的”,通過控制和摧殘她的身體,進而使她難以表達自己,個人意志不斷受限。盡管“棕色的”還是很想寫真正的小說,但是她在這種重壓和控制下感受到了恐懼,只能目光呆滯地面對著電腦屏幕發呆。后來,她將自己的聰明才智耗費在做無休無止的習題集上,成為一個“吃掉大量習題的母蝗蟲”。
四、所謂“生活”
《白銀時代》一文講述了在寫作公司工作的“我”的日常生活以及“我”所創作的《師生戀》的內容。按照規定,“我”只能描寫真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而無任何虛構。在閱讀到“我”與老師之間那種不同于夫妻之間敷衍冷淡的感情之后,“我”突然間宣布:“如你所知,我們所寫的一切都必須有‘生活作為依據。我所依據的‘生活就是老師的簽字——這些簽字使她走進了我的故事。”也就是說,“我“并沒有與老師戀愛過,這里產生了極大的荒謬。由于老師一遍遍的簽字,假的戀愛故事變成了真實,寫作所依據的真實是虛假的真實,“依據生活”不過是這個世界規范和束縛知識分子思想與自由的一種手段,最終消磨掉他們創作的想象和欲望。在這樣荒誕又充滿諷刺的故事中,王小波表達了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和知識分子生存境遇的擔憂與焦慮。
在希臘神話中,白銀時代的人蒙神恩寵,終身不會衰老,也不會為生計所困。他們沒有痛苦,沒有憂慮,一直到死,相貌和心靈都像兒童。死掉以后,他們的幽靈還會在塵世上游蕩。神話里的人物不必回答什么是真正的小說,而活生生的人卻不可能永遠無憂無慮,活在白銀時代的人看似無憂,實際是他們的生活和思想被監視和控制,失去了思考自身境遇的可能。在這個一環扣一環、和諧運轉的白銀世界,一切都受到精確規劃,人們的思想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規定,一旦出現毛病,要么被消滅、要么被改造。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們最大的感受就是晦暗,毫無希望。“我”所見到的是霧蒙蒙的天氣,停車場的柏油又黑又亮,葉子黑得像深秋的腐葉,保安人員的雨衣也是黑亮的,在這樣暗沉的世界中,“我”常常發愣,木然地看著周圍,失去了生命的欲望,整個世界是抑郁的、沉悶的、了無生趣的。《白銀時代》構造了一個秩序井然、整齊劃一的世界,這個世界里看似一切完美,統一和諧。但是,它限制著人們的行動,鉗制思想,阻止人們追求愛情,無趣乏味,人們喪失了主體性,沒有自由和價值可言。
前面已經說過,反烏托邦文學并不是和烏托邦文學截然對立的,它本身就含有諸多烏托邦因素,就其目的而言,是為了加深對烏托邦的認識與理解,不斷探索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王小波的《白銀時代》也是如此,以幽默諷刺的筆法描寫知識分子在未來世界中的境遇,這是對現實世界的影射和關照。但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批判,而是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避免和抗拒人性的失落和自由的淪喪。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