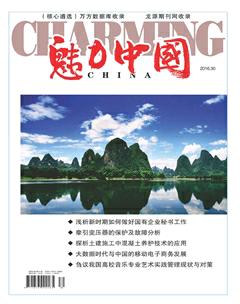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的內(nèi)涵價(jià)值以及意義
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伴隨著近代科學(xué)的誕生而誕生,它是在繼承人類先前思想遺產(chǎn)的基礎(chǔ)之上,逐漸發(fā)展起來的科學(xué)理念和科學(xué)傳統(tǒng)的積淀。“關(guān)乎天文以察時(shí)變,關(guān)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易篆辭》中最早提出的“人文”概念,人文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文化現(xiàn)象和精神世界,其立足點(diǎn)就是“以人為本”。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是科學(xué)文化深層結(jié)構(gòu)中蘊(yùn)含的價(jià)值和規(guī)范的綜合。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發(fā)端于科學(xué)信念,通過科學(xué)思想與獨(dú)特的科學(xué)知識(shí)表現(xiàn)出來,并且在一系列的科學(xué)活動(dòng)中得到實(shí)踐,在實(shí)踐的過程中使得其影響不斷擴(kuò)大。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是科學(xué)精神的一個(gè)重要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把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稱之為科學(xué)本性的流露和延伸。只有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才能夠體現(xiàn)科學(xué)的哲學(xué)和文化意蘊(yùn),也只有它才是科學(xué)的根本、真諦和靈魂。科學(xué)精神不是一個(gè)封閉的體系,它的本性決定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不斷傳播,通過與外界的接觸進(jìn)行持續(xù)不斷的學(xué)習(xí)、訓(xùn)練以及深入研究的過程。科學(xué)精神之所以能夠稱之為精神就是因?yàn)樗軌騼?nèi)化為人的主觀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們科學(xué)的心智框架、習(xí)慣、思維方式的運(yùn)行。它最終內(nèi)化為主體的科學(xué)良心,并且通過人的感官為媒介外化為人的科學(xué)態(tài)度、科學(xué)道德。科學(xué)的人文精神作為科學(xué)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徹底貫徹了科學(xué)精神的一切優(yōu)點(diǎn)。這主要包括科學(xué)精神通過人表現(xiàn)出來的自主意識(shí)、價(jià)值取向、精神氣質(zhì)、認(rèn)知模式、道德律令和行為準(zhǔn)則。通過查閱過去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我們往往會(huì)發(fā)現(xiàn)人們?cè)谶^去對(duì)科學(xué)的精神存在著一個(gè)顯著的誤解—認(rèn)為科學(xué)沒有人性,因?yàn)榭茖W(xué)沒有人性,所以科學(xué)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文精神。最先對(duì)這一觀點(diǎn)提出挑戰(zhàn)的就是R. H. 布朗,他注意到的社會(huì)現(xiàn)象以及所產(chǎn)生的思想思潮“在過去,傳統(tǒng)的世界中科學(xué)一直遭到這樣的佶難,原因在于科學(xué)所注重的因果律,把世界的運(yùn)行僅僅只是看作一臺(tái)依照科學(xué)規(guī)律而有條不紊運(yùn)行的機(jī)械,世界變得極為單調(diào),人們也在這種客觀的世界中失去了創(chuàng)造的活力。這樣的世界是缺乏想象力的世界,此時(shí)的世界是黑白的二分的世界。1帕斯莫爾也在他的著作中揭示出反科學(xué)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他說:科學(xué)不僅僅摧毀客體世界的工具,通過科學(xué)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生產(chǎn)成果固然對(duì)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與此同時(shí),科學(xué)在創(chuàng)造物質(zhì)成果的同時(shí)也不斷改變著人們的心智,改變著人性。2歷史上各個(gè)時(shí)期對(duì)科學(xué)與人文精神的錯(cuò)誤認(rèn)識(shí),這突出表現(xiàn)在后現(xiàn)代主義者通過對(duì)科學(xué)的反對(duì),他們認(rèn)為科學(xué)中沒有人文精神,甚至科學(xué)中壓根就沒有什么精神。他們的這種激進(jìn)的觀點(diǎn)反映出當(dāng)今社會(huì)科學(xué)與人文精神割裂的重要事實(shí)。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科學(xué)與人文精神的關(guān)系,重新闡釋科學(xué)中包含的人文精神的因素,從而論述科學(xué)的與人性珠聯(lián)璧合的途徑。
1、從西方文化的歷史發(fā)展看科學(xué)與信仰的辯證關(guān)系
我們知道理性精神、科學(xué)精神在西方的文化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現(xiàn),本通過把科學(xué)與信仰的辯證關(guān)系鑲?cè)胛鞣轿幕D清晰的展現(xiàn)科學(xué)和信仰的獨(dú)特關(guān)系。在西方文化中,科學(xué)與信仰的關(guān)系并非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模式,而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不斷調(diào)整、變化的辯證關(guān)系。在西方文化的搖籃時(shí)代—希臘城邦時(shí)代,科學(xué)與信仰是一種水乳交融的同一關(guān)系,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界限。在中世紀(jì)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一度攫取了絕對(duì)的專治權(quán)利,而這時(shí)科學(xué)與哲學(xué)只能夠仰承宗教的鼻息,完全不具有獨(dú)立的地位。隨著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學(xué)開始逐漸擺脫宗教的影響,二者發(fā)生了根本性的逆轉(zhuǎn),這時(shí)一種以科學(xué)為主導(dǎo)的新的人文精神重新產(chǎn)生出來,科學(xué)與信仰的關(guān)系變成一種共生互補(bǔ)的新關(guān)系模式,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
1.1對(duì)科學(xué)與人文信仰進(jìn)行重新反思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對(duì)科學(xué)與信仰,尤其是信仰中包含的宗教精神抱著一種過分簡單的看法。一般認(rèn)為信仰在過去科學(xué)技術(shù)水平低下的情況下占主導(dǎo)地位,是因?yàn)榭茖W(xué)理性精神的不發(fā)達(dá),因此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理性精神的壯大,信仰也會(huì)被科學(xué)所控制。然而面對(duì)科學(xué)技術(shù)高度發(fā)達(dá)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這種科學(xué)與信仰之關(guān)系的傳統(tǒng)觀點(diǎn)正在日益受到嚴(yán)峻的挑戰(zhàn)。當(dāng)今美國在科學(xué)技術(shù)方面無可爭議地處在世界領(lǐng)先地位,但是美國的文化以及精神在世界上占有非常強(qiáng)勢的地位。今天的中國比起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在科學(xué)技術(shù)方面無疑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中國人對(duì)于人文精神的需求也越來越明顯。面對(duì)科學(xué)與信仰同步發(fā)展而非此消彼長的新現(xiàn)象,我們有必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科學(xué)與人文精神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而不應(yīng)該采取一種無視現(xiàn)實(shí)的自欺欺人的蒙昧態(tài)度。
自從儒家思想在漢代取得獨(dú)尊低位以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儒家精英知識(shí)分子的文化在本質(zhì)上就采取一種擁有人文精神、人文關(guān)懷的文化傾向。這里的人文精神、人文關(guān)懷表現(xiàn)為一種道德教化。中國人從來未真正經(jīng)歷過宗教的暴虐和理性精神的跋扈這兩種相反的極端形式。也正是因?yàn)槿绱耍覀儗?duì)于科學(xué)理性與人文精神之間的關(guān)系往往采取的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學(xué)的,即簡單的把二者看作是一種水火不容的對(duì)立關(guān)系。
毋庸置疑,科學(xué)與宗教在西方曾一度處于水火不容的對(duì)立關(guān)系之中,但是正如他們?cè)?jīng)也在其他的歷史階段中呈現(xiàn)為一種水乳交融的統(tǒng)一關(guān)系一樣。在西方歷史長河中,科學(xué)與宗教的關(guān)系是一種動(dòng)態(tài)的、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而不斷調(diào)整和變化的關(guān)系,我們只有用這種辯證的眼光看待二者之間關(guān)系,才能真正理解科學(xué)理性與人本主義信仰之間表現(xiàn)出來的微妙的共生關(guān)系。
1.2西方文化中科學(xué)與人文信仰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關(guān)系
在西方文化搖籃時(shí)期的希臘時(shí)代,科學(xué)與信仰二者之間是難分彼此的。希臘的最早一批科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節(jié)。例如被我們稱為第一個(gè)唯心主義者的畢達(dá)哥拉斯,他既是一個(gè)偉大哲學(xué)家,又是一個(gè)杰出的數(shù)學(xué)家,更為奇怪的是他還是一個(gè)奇怪的宗教團(tuán)體的創(chuàng)始人。畢達(dá)哥拉斯在哲學(xué)上提出了數(shù)本源說,由此奠定西方形而上學(xué)之根基。在希臘的數(shù)學(xué)知識(shí)中,幾何學(xué)是從埃及人那里學(xué)來的,而代數(shù)則是希臘人的創(chuàng)造。幾何與代數(shù)的區(qū)別在于形與數(shù)的區(qū)別,形是具體的,數(shù)卻是抽象的。古代埃及由于丈量土地的需要很早就發(fā)明了幾何學(xué),但是埃及人的抽象思維能力遠(yuǎn)遠(yuǎn)比不上希臘人,因此古代埃及人沒有從幾何學(xué)里抽象出代數(shù)定律。沒有完成幾何學(xué)到代數(shù)學(xué)的跨越。但是畢達(dá)哥拉斯定律創(chuàng)立不久就引起了西方數(shù)學(xué)史的第一次危機(jī),即無理數(shù)的危機(jī),這種危機(jī)導(dǎo)致數(shù)與形一直處在彼此分離的狀態(tài),直到17世紀(jì)笛卡爾創(chuàng)立了解析幾何學(xué),才在數(shù)與形之間重新建立起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在漫長的分離過程中,形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數(shù)則發(fā)展演變成為形式化的邏輯系統(tǒng),成為西方哲學(xué)和神學(xué)的根基。看中思維而輕視感覺、重邏輯而輕經(jīng)驗(yàn)、重本質(zhì)而輕現(xiàn)象的傾向是古希臘數(shù)學(xué)思想發(fā)展的結(jié)果,也與當(dāng)時(shí)的宗教觀念、特別是希臘宗教中的命運(yùn)觀念密切相關(guān)。在柏拉圖的哲學(xué)中,對(duì)理性知識(shí)的強(qiáng)調(diào)是與靈魂不朽的信仰密不可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即使是亞里士多德的審慎的理性主義,其形式與質(zhì)料的理論最終也引出了作為“不動(dòng)的推動(dòng)者”和一切存在的終極目的神。由此可見,在希臘時(shí)期無論是柏拉圖所代表的神秘主義,還是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義,都并未在科學(xué)與信仰之間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甚至截然對(duì)立的界限。在古希臘文化中,正如現(xiàn)實(shí)與理想、人間與天國都處在一種相互融通的狀態(tài)中一樣,科學(xué)理性與宗教信仰也仍然是一種原始的同一關(guān)系。
到了中世紀(jì),基督教信仰成為凌駕于西歐社會(huì)之上的唯一的意識(shí)形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神學(xué)成為至高無上的學(xué)術(shù),而科學(xué)和哲學(xué)都成為神學(xué)的奴婢。古典文化將科學(xué)理性和人文精神融為一體,中世紀(jì)基督教文化則極力用宗教信仰貶抑科學(xué)理性。在中世紀(jì),科學(xué)被當(dāng)作巫術(shù)和邪教一類的東西,完全沒有獨(dú)立的地位,必須仰承宗教信仰之碧璽,從而被扭曲的面目全非。比如說中世紀(jì)的宇宙論主張“地心說”,其原因固然有希臘化時(shí)期天文學(xué)家托勒密的影響,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卻是《圣經(jīng)》的說法。在《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jì)》中,上帝創(chuàng)造了宇宙萬物,最后以自己的形象為模型創(chuàng)造了人,并且將人置于宇宙的中心,讓他管理宇宙萬物。這種宗教信條成為中世紀(jì)科學(xué)必須遵循的準(zhǔn)則。在這種情況下,科學(xué)完全把經(jīng)驗(yàn)拋在一邊,僅僅依靠神學(xué)教條和邏輯推理作為依據(jù)。科學(xué)成為徒有虛名的東西,其發(fā)展水平及其慘淡可憐,自然也不會(huì)產(chǎn)生出以科學(xué)為中心的人文精神來。中世紀(jì)堅(jiān)持用信仰反對(duì)理性,而信仰卻是理性無法理解的東西,因此神秘主義構(gòu)成了中世紀(jì)基督教文化對(duì)于科學(xué)理性與宗教信仰之關(guān)系的基本觀點(diǎn)。眾所周知,科學(xué)技術(shù)是建立在經(jīng)驗(yàn)和理性的基礎(chǔ)之上的,而經(jīng)驗(yàn)和理性恰恰是與奇跡相對(duì)立的。中世紀(jì)的基督教信仰把奇跡置于理性和經(jīng)驗(yàn)之上,奇跡的根據(jù)是上帝的啟示,這些啟示分明地記載在《圣經(jīng)》之中。因此,如果理性和《圣經(jīng)》相違背,那么錯(cuò)誤的肯定是理性,而《圣經(jīng)》是絕對(duì)不會(huì)出錯(cuò)的,因?yàn)槟鞘巧系鄣恼Z言,上帝的語言怎么可能錯(cuò)誤呢?在這樣一種觀念的絕對(duì)支配之下,中世紀(jì)歐洲的基督教文化確實(shí)是非常愚蠢的,而科學(xué)則完全處于宗教信仰的壓抑之下,處于奄奄一息的狀態(tài)。
從15—16世紀(jì)開始,隨著文藝復(fù)興和宗教改革等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開展,以及航海活動(dòng)的蓬勃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的重大變化,在仍然被基督教信仰所籠罩的西歐社會(huì)內(nèi)部,科學(xué)理性精神開始逐漸崛起。但是直到17世紀(jì),雖然科學(xué)理性在懷疑主義和經(jīng)驗(yàn)主義的保駕護(hù)航之下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但是基督教信仰在歐洲畢竟有著一千多年的歷史傳統(tǒng),它的影響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是根深蒂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xué)最初只能采取一種妥協(xié)的方式來謀求自身的發(fā)展,而不可能公然地與宗教信仰相對(duì)抗。誠如著名科學(xué)史家丹皮爾所言:“17世紀(jì)中葉所有的合格的科學(xué)家與差不多所有的哲學(xué)家,都是從基督教的觀點(diǎn)去觀察世界。宗教與科學(xué)互相敵對(duì)的觀念是后來才有的。”3后來的自然神論產(chǎn)生和發(fā)展,成為科學(xué)與宗教保持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的重要媒介。自然神論的核心思想說到底就是要突出理性至高無上的意義,認(rèn)為連上帝也要服從理性的法則。上帝按照理性法則創(chuàng)造了世界,然后他就不再干預(yù)世界,讓世界按照自然規(guī)律(即理性法則)來運(yùn)行。這樣科學(xué)家們就有事干了,他們就可以大膽研究自然規(guī)律了。這一套理論一方面證明了上帝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另一方面卻把上帝束之高閣,趕出自然之外,讓他再也不能隨心所欲的在自然界中產(chǎn)生奇跡。自然神論理論體系發(fā)展的結(jié)果就是后來的泛神論,泛神論把上帝等同于自然,自然萬物中都顯示出上帝的神性,這神性就是自然規(guī)律。這樣就把上帝和自然完全等同起來了。在經(jīng)歷了這兩個(gè)環(huán)節(jié)以后,到了18世紀(jì)后半葉,法國啟蒙運(yùn)動(dòng)中涌現(xiàn)出一批無神論者,即百科全書派思想家。他們公然宣稱:只有自然,沒有上帝;只有理性,沒有啟示和奇跡,主張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審判。在這方面,法國啟蒙運(yùn)動(dòng)陣營中的一匹黑馬-盧梭代表了平民的態(tài)度。他認(rèn)為道德良心是上帝真正的殿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盧梭開啟了科學(xué)人文精神的先河。
1.3以科學(xué)為基礎(chǔ)的人文精神的產(chǎn)生
法國啟蒙運(yùn)動(dòng)標(biāo)志著科學(xué)理性在經(jīng)歷了長期的委屈求全之后,終于開始揚(yáng)眉吐氣地對(duì)宗教信仰進(jìn)行全面的清算。科學(xué)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為生活的主宰,然而科學(xué)不是萬能的,長期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中的西方人迫切需要建立一種以科學(xué)為基礎(chǔ)人文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康德作為科學(xué)與宗教之間關(guān)系的一個(gè)調(diào)節(jié)者應(yīng)運(yùn)而生。
眾所周知,康德無疑是西方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指向一個(gè)終極目標(biāo)-自由,而自由,而自由只有在科學(xué)與宗教的調(diào)節(jié)中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康德曾經(jīng)說過,在他一生有兩個(gè)人對(duì)他影響最大;牛頓讓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規(guī)律,而盧梭讓他看到了人心深處的道德良心,這便是后來稱之為科學(xué)人文精神的雛形。大家都非常熟悉康德的一句名言:有兩樣?xùn)|西讓我感動(dòng),那就是頭頂?shù)男强蘸托闹械牡赖侣伞?档潞肋~地宣稱:人給自然立法。同樣的,人也給自己立法,這就是我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承認(rèn),正是盧梭使他學(xué)會(huì)了尊重人,而尊重人說到底就是要尊重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律。雖然康德在性格情操、生活方式和行為準(zhǔn)則等方面都與盧梭大相徑庭,但是他們兩個(gè)人的思想?yún)s非常一致,都強(qiáng)調(diào)良知和道德律強(qiáng)調(diào)行為的善良動(dòng)機(jī)。康德既是一個(gè)偉大的科學(xué)家和理性主義者,同時(shí)又具有虔敬主義的宗教底蘊(yùn)。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調(diào)解認(rèn)識(shí)與實(shí)踐、科學(xué)與宗教之間的矛盾。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最大的貢獻(xiàn)就是把上帝從自然界中徹底驅(qū)逐出去,自然界中只有科學(xué)頒布的自然規(guī)則,沒有上帝的立錐之地。因而,科學(xué)家就可以心無旁騖、高枕無憂地直接面對(duì)大自然,而無需考慮與上帝有關(guān)的問題但是,康德讓科學(xué)在宗教面前獲得獨(dú)立地位的條件是為宗教也保留了獨(dú)立的地盤,他把自然界交給了科學(xué),卻在人的內(nèi)心世界中為宗教信仰留下了場所。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里,康德從道德的角度把上帝重新確立起來。他認(rèn)為,我們每個(gè)人都有內(nèi)在的道德律,都可以做到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但是這種道德律只是一種應(yīng)然狀態(tài)的法則,人追求道德完善的過程是一個(gè)極其漫長的的過程。而且道德與幸福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也往往處于相互分離的狀態(tài)之中。因此,康德就在自由意志的根據(jù)之上作了兩點(diǎn)假設(shè):第一,人追求道德完善的過程不是此生此世可以完成的,必須設(shè)定靈魂不死;第二,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幸福與道德相分離的狀況在未來的理想世界中可以通過德福配位的方式得到解決,在那里,一個(gè)人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越高,他就會(huì)享受到越多的幸福。康德在調(diào)節(jié)科學(xué)與宗教之間的關(guān)系客觀的說,還是把科學(xué)和宗教對(duì)立開來,認(rèn)為它們分屬于人類活動(dòng)的不同領(lǐng)域,沒有建立起以科學(xué)理性為基礎(chǔ)的人文精神,但是這一理論在當(dāng)時(shí)還是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無疑都具有重要意義。現(xiàn)當(dāng)代社會(huì),科學(xué)無疑占據(jù)這主導(dǎo)地位,科學(xué)人文精神一方面要求我們需要能動(dòng)的運(yùn)用科學(xué)造福自己,有要求我們不被科學(xué)所奴役成為科學(xué)技術(shù)的奴隸。科學(xué)不僅僅只是一種手段和工具,它在讓你們生活中的地位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和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樹立科學(xué)的人文意識(shí),就需要清楚科學(xué)中擁有的人文要素。
作者簡介
陳琦(1996.04- ),男,河南鄭州人,武漢理工大學(xué)汽車工程學(xué)院2014級(jí)本科生,研究方向:汽車服務(wù)工程專業(yè)。
注
1布朗: 《科學(xué)的智慧—它與文化和宗教的關(guān)聯(lián)》,李醒民譯,沈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77頁
2 J. Passmore, Science and Its Critics, Duckwort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8 pp. 45,69 - 70.
3 W.C丹皮爾《科學(xué)史-及其與哲學(xué)和宗教的關(guān)系》李銜譯,商務(wù)印書館1975年版,第2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