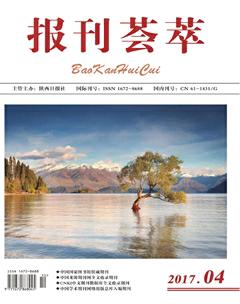班級管理中,請慎用懲罰
朱永斌
摘要:中國有古訓:“嚴師出高徒”,所以不少班主任總是以自己的嚴苛為豪。本文試圖從:“班主任的懲罰是否真的對被懲罰者有效;班主任的懲罰最終是和班主任自己,還是與學生的不良行為聯系在一起;班主任的懲罰的時機和方式是否確當。”等三個層面探討體罰教育的危害和懲罰時的注意事項。
關鍵詞:斯金納;懲罰;不良行為;時機;方式
美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新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操作性條件反射理論的奠基者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通過系統的實驗觀察得出了一條重要結論:懲罰就是企圖呈現消極強化物或排除積極強化物去刺激某個反應,僅是一種治標的方法,它對被懲罰者和懲罰者都是不利的。斯金納對懲罰的科學研究,對改變當時美國和歐洲盛行的體罰教育起了一定作用。
中國有句古訓:“嚴師出高徒”。于是,不少班主任片面理解了這句古訓的含義,在平時的教育工作中,一味地強調嚴格,甚至達到了苛刻的程度,而忽略了懲罰的尺度、時機和方式,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
下面,本人就結合平時的日常生活和班主任工作中遇到的鮮活的事例,做些反思。
反思一:我們的懲罰真的對被懲罰者有效嗎?
讓我們先來看一則身邊的教育故事。
隔壁班級的一位成績不理想的男生李志,原本就看不慣班上的一位成績優秀的男生趙鳴的傲氣。天氣冷的時候,李志轉到了靠教室門口的位置,一天趙鳴進教室后沒有隨手關門,李志就讓他回來把門關上。礙于面子,趙鳴拒絕了。李志不僅惡語相向,還在全班同學面前秀了一把腳法,踹倒了趙鳴,好在其他同學及時阻攔,并立即報告了班主任,事態得以控制。班主任十分氣憤,怒斥了一番李志,覺得還不解氣,電話通知家長:李志家長向趙鳴賠款道歉、李志停課反省一周。
李志勉強認錯、認罰。沒多久,一個周日下午,李志先進教室后故意把前后門都關上,不讓趙鳴進來。趙鳴氣急了,便罵了李志幾句。李志終于找到了借口,摔倒趙鳴,并騎在趙鳴身上暴打,邊打還邊叫囂:這次準備多賠點錢。
結果,當然是趙鳴住進了醫院,家長吵到了學校。經過學校協調,李志的家長負擔所有醫藥費、營養費和誤工費;李志繼續停課一個月……
我認為,雖說懲罰會導致反應的減少,但它只是間接地起作用的,它只是抑制而不是消除這種行為;而與此同時,懲罰可能會引起負效應,如攻擊性行為。
對于同學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我的預防措施是,在班級組建之初,我就強調:我把每位同學都當自己的孩子,那么,你們所有同學相互間就是兄弟姐妹,如手足,手足當然不能相殘!同學之間鬧矛盾,尤其是惡性斗毆是我治班的三大高壓線之一。所以,在我15年的班主任經歷中,班上的同學之間從未發生過打架之類的惡性事件。
反思二、我們的懲罰最終是和自己,還是與學生不良行為聯系在一起了?
家中的教育故事。
我女兒今年高三了,記得她剛剛考上高一,但沒有分班前,十分向往能分到她現在的班主任(以鐵腕治班著稱)的班上。結果由于她們學校嚴格按照中考成績分了個競賽班,而她的分數不夠,未能成為她尊敬得有點崇拜的班主任的學生。為此,我女兒還失望了好一陣子呢。后來,總算利用高二分科的機會,如愿擠進了競賽班。剛開始,我女兒還能夠適應,成績進步很快。可慢慢地,由于她自己的散漫習慣,總是受到懲罰:不是遲到被罰站到教師辦公室一天,就是聽寫不過關被罰抄。我女兒不僅不能反思自己的錯誤,反而總是抱怨班主任過于嚴苛。我作為一名老班主任,耐心做了女兒多次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導,但無奈效果不佳。高三的一天,當我女兒再次聽寫沒過關,被罰抄20個單元內容5遍,她負氣且任性地從晚上10:30一直抄到第二天凌晨4:30,然后5:30又起床準備上學。中午放學后,她終于爆發了:不僅對班主任滿腹怨氣,而且要到我們學校,我帶的班上上學。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影響,我只能狠心拒絕了她的要求。經過近一周的反復勸導,她總算十二分不情愿地留下了,但學習的質態下滑明顯。
要知道,懲罰常常會導致一種消極的情緒狀態。同時,這種消極的情緒狀態(根據鄰近的原理)往往是與實施懲罰者,而不是不良行為聯系在一起。
在處理學生上學遲到時,我會首先仔細了解遲到的原因,然后做有針對性的交流、批評教育,不搞“一刀切”,這樣既可以避免學生由于受委屈而產生抵觸情緒,又可以減少學生由于受罰而不能上課受損。結果,我班上的學生漸漸地“不好意思”遲到了。
在遇到學生不能及時完成學習任務或者作業、考試經常犯類似的低級錯誤時,我總是先分析學生究竟是基礎和能力問題,還是態度問題;然后,讓基礎和能力欠缺的學生進行帶有一定懲罰性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補習,對態度較差的學生則要求他們加做不同類別的練習;最后,我還要求這些學生都必須做好相關的錯題集,并接受我額外的不定期檢查。這樣,學生都能理解和執行。
反思三、我們的懲罰的時機和方式是否確當?
自己班上的教育故事。
一段時間,我發現班上的不少學生在早讀課、晚讀課包括部分教師的課堂上,打瞌睡現象比較嚴重,而且,班上的某個區域特別嚴重。
首先,我設身處地地從學生角度思考,覺得作為高三學生普遍早起晚睡,肯定比較疲勞;其次,不排除部分學生有惰性;最后,我推測打瞌睡也有一定的“傳染性”。
為此,我通過班會課和全體同學商量:把當周定為掃除瞌睡蟲“活動周”,并及時制定了大家認可的懲戒措施。比如,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設立專座,供連續三次以上打瞌睡的同學暫時站著讀書、聽課,一旦自己覺得能夠打敗瞌睡蟲時,就可以自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同時,我用心準備了《為什么一定要考大學》、《不讀書、不吃苦,你要青春干嘛》、《怎樣鍛煉自己的意志力》、《高三的最后時刻,別輸給不能堅持的自己》系列主題班會,幫學生勵志。此外,我還適時進行了位置微調,切斷了“傳染源”。
漸漸地,班上經常打瞌睡的同學,由開始時的被動、勉強罰站,發展為:主動到自來水旁沖把臉、自覺站到教室后排的專座旁聽會課……
畢竟,我也認可,懲罰至少在抑制不良行為方面是非常有效的,而且,當懲罰看來是減輕不良反應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時,懲罰的害處可能要比讓學生自身發展下去的后果要小一些。
即便如此,我依然堅持:在非得給予懲罰時,也要注意三點:第一,要注意利用懲罰后的反應抑制期。也就是說,要盡可能通過強化,來加強其它的行為反應。第二,懲罰一定要在不良反應發生后立即給予,延遲的懲罰可能是無效的。第三,盡可能采用一種被稱為“暫停程序”的懲罰辦法,即不是通過給予厭惡刺激來懲罰,而是讓學習者離開一種有可能會得到強化的環境來懲罰。
所以,我一方面不贊成簡單粗暴的懲罰方式,另一方面也不否認必要、適當的懲罰在矯正不良行為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
備注:該論文是,揚州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新課程背景下高中教師教育教學反思的研究》的研究成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