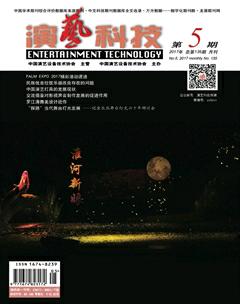重塑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倫理精神
宋晶
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催生了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同時又使其陷入一個倫理困境。現(xiàn)代化追逐利益,推崇工具理性,自然資源成為人類發(fā)展工業(yè)肆意掠奪的對象,人本身也異化為物質(zhì)欲望的工具和“機(jī)器運(yùn)行的鏈條”。當(dāng)代教育哲學(xué)家努斯鮑姆認(rèn)為職業(yè)教育在為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的逐利目標(biāo)服務(wù),它的功能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家利益,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輸送人力資源;一個是個人利益,向個體販賣知識技能,提供“飯碗”。這個定位并沒有錯,但是作為直接面向經(jīng)濟(jì)社會的一種基本的教育類型,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不僅能培養(yǎng)從事各種職業(yè)的人員,更重要的是,職業(yè)教育要培養(yǎng)使自己的生活有意義的人。
倫理學(xué)本來是關(guān)于人的學(xué)問,其研究對象涉及人與人的倫理關(guān)系、人與自我的關(guān)系及探究人如何生活得更美好的終極目的和行為準(zhǔn)則。隨著生態(tài)危機(jī)出現(xiàn),它的研究視閾擴(kuò)大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guān)系,關(guān)注人對非人類物種及自然世界應(yīng)有的生態(tài)道德責(zé)任。從倫理的視角看,職業(yè)教育培養(yǎng)的應(yīng)該是完全意義上的職業(yè)人——合格的國家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他們能夠獨(dú)立、批判性地思考,有創(chuàng)新精神,對他人、社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負(fù)有責(zé)任感和同情心,能理解弱勢群體的苦難和自己工作成就的意義。這些價值觀念在理論和實踐領(lǐng)域中也通常被認(rèn)為是有益的,但職業(yè)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卻極少思考一個問題:要將這些價值觀傳給下一代并有效地影響其思想和行為,職業(yè)教育需要做什么?逐利的目標(biāo)分散了教育者的注意力,在降低成本的壓力下,我們剪除的恰恰是對維持健康社會至關(guān)重要的那部分教育工作。若任由這種傾向發(fā)展下去,職業(yè)教育培養(yǎng)出的各行各業(yè)的從業(yè)者都無法從工作中找到意義,不顧及自身生產(chǎn)行為對生態(tài)圈帶來的后果。最終,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無存,人自身的幸福也就無從談起,這樣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帶來的只能是災(zāi)難性的結(jié)局。這就是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面臨的現(xiàn)實倫理困境。
在社會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中,職業(yè)教育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工具理性的沖擊。技術(shù)人才的培養(yǎng)日趨符號化、物化,職業(yè)教育培養(yǎng)目標(biāo)逐漸偏離“人”的方向,職業(yè)教育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自反性”或“人性物化”的問題。職業(yè)教育重視能力本位,多關(guān)注教育的方法方式問題,重點(diǎn)集中在專業(yè)課程的開發(fā),對于職業(yè)能力能否使學(xué)習(xí)者幸福,能否為學(xué)習(xí)者創(chuàng)造追求幸福生活的內(nèi)在條件等根本性價值問題,卻未予以足夠重視。職業(yè)教育的根本價值問題非技術(shù)知識、能力所能解決,在職業(yè)教育的根本價值未得以確證之前,在缺乏倫理的價值預(yù)設(shè)的情況下,職業(yè)教育傳授給學(xué)習(xí)者的技術(shù)知識,形成的職業(yè)能力可能會作為工具理性而成為奴役人及其環(huán)境的工具。職業(yè)教育“為誰”與“為何”問題是職業(yè)教育的倫理精神及其意義問題。從倫理價值視角看,單純追求“何為”職業(yè)教育非但沒有價值,反而可能成為一種負(fù)面價值。工具理性的蔓延使教育領(lǐng)域出現(xiàn)“倫理的真空”,它已經(jīng)清楚地表現(xiàn)出來。第一,工具理性是“一種計算最經(jīng)濟(jì)地將手段應(yīng)用于目的時所憑靠的合理性”(泰勒語),它強(qiáng)調(diào)手段以及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功利關(guān)聯(lián),雖然推動了科技進(jìn)步和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但其技術(shù)理性神話的造就卻以犧牲人類生存權(quán)利和存在的意義為代價,導(dǎo)致了人文精神的顛覆。第二,對短期效益的追求導(dǎo)致教育在價值本原迷茫,價值取向上偏離了“育人”的方向,教育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諸多“倫理的真空”,并由此誘發(fā)了種種“短視”的教育舉措。講求效率的職業(yè)教育在片面的追求培養(yǎng)能創(chuàng)造利益的人,培養(yǎng)確定規(guī)格的勞動“工具”,而忽視作為人性的教育要求,單純追求現(xiàn)實的利益、直接的利益和物質(zhì)利益的實現(xiàn)。第三,工具理性已成為阻礙其健康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痼疾。從倫理的視角審視職業(yè)教育,分析問題的著眼點(diǎn)不應(yīng)只是職業(yè)教育領(lǐng)域的“物”,而應(yīng)是整個社會領(lǐng)域中的“人”,解決問題的著力點(diǎn)不應(yīng)只傾力追求體制的完善,而應(yīng)力促實現(xiàn)價值取向上的正確性。在我國當(dāng)前以發(fā)展為主旨的工業(yè)化中期,我們有必要對培養(yǎng)職業(yè)人的職業(yè)教育進(jìn)行冷靜的倫理反思,在大力發(fā)展職業(yè)教育的同時嘗試著探討職業(yè)教育應(yīng)如何規(guī)避現(xiàn)代化帶來的工具理性。我們的職業(yè)教育要培養(yǎng)出“完全意義上的人”,而非產(chǎn)出“一代代有用的機(jī)器”和“沒有人性的技術(shù)專家”。
摒棄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功利性與工具理性,回歸其教育的倫理本性,是全球職業(yè)教育的共同追求。對此,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一系列文件,呼吁教育的核心問題就是要關(guān)注人的潛能的發(fā)揮、素質(zhì)的提高。《學(xué)會生存》中提出“四個支柱”是指導(dǎo)國際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綱領(lǐng)性文件。國際技術(shù)與職業(yè)教育大會從終身教育的角度對職業(yè)教育定義:“普通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終身學(xué)習(xí)的一個方面”以及“成為負(fù)責(zé)任的公民的一種準(zhǔn)備有利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種手段”等。職業(yè)教育作為教育的一種類型,不能喪失其根本的教育性,“職業(yè)教育的定義應(yīng)當(dāng)以促進(jìn)人的發(fā)展的視角來確定,不能也不應(yīng)該如以往片面從教育的經(jīng)濟(jì)功能角度加以限定,我們應(yīng)對其持有一種更開闊的視野。”
責(zé)任編輯 秦紅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