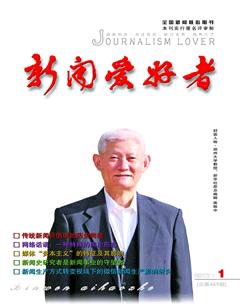幕末時期日本報紙的發(fā)展特點與現(xiàn)實動因分析
孟林山
【摘要】19世紀初至19世紀60年代既是日本幕府統(tǒng)治末期,也是日本報紙發(fā)展的萌芽階段。這一時期的日本報紙發(fā)展,同日本即將步入近現(xiàn)代發(fā)展的歷程時所受到的影響是高度一致的——國內(nèi)矛盾日漸升級、外國勢力不斷入侵以及資本主義經(jīng)濟對封建經(jīng)濟逐步瓦解。日本近代報紙以“自上而下”的“逆發(fā)展”方式不斷成長,并且同政治運動緊密相聯(lián)。日荷兩國的特殊外交關(guān)系對此后日本包括報紙在內(nèi)的近代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關(guān)鍵詞】幕府末期;日本報紙;發(fā)展歷程;發(fā)展特點;發(fā)展原因
報紙作為近現(xiàn)代社會思想上層建筑的重要載體,往往與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與社會發(fā)展緊密相聯(lián),幕末時期的日本報紙發(fā)展亦是如此。作為變革時代的見證者與推動力,以及當時政治宣傳最為有力的工具之一,日本幕末時期的報紙經(jīng)過多年的發(fā)展,從由他國進獻報紙到自主收集、翻譯海外報紙,從翻譯外文報紙到自主創(chuàng)辦日文報紙,從過去的“消息報”逐漸轉(zhuǎn)為帶有政論觀點的“政治報”。伴隨著幕末時期的多次政治動蕩,日本的報紙逐漸向近代報刊發(fā)展。
一、幕末時期日本報紙的發(fā)展歷程
(一)“黑船事件”之前的日本報紙——《荷蘭傳聞書》(19世紀初至1854年)
隨著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西班牙、葡萄牙等最早一批的歐洲商人與傳教士,在“商教一體”政策的支持下,在整個亞洲地區(qū)進行大范圍的商業(yè)貿(mào)易與宗教傳播。雖然德川幕府在前期對這些來自歐洲各地的商人與傳教士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tài)度,但宗教及貿(mào)易活動卻不斷威脅德川幕府的統(tǒng)治以及整個日本地區(qū)的獨立自主性,因此,德川幕府便斷斷續(xù)續(xù)地實行了近300年的“海禁”政策。荷蘭作為當時同日本進行有限交流的少數(shù)西方國家,早期的西方文化科學知識主要是由在印尼的荷蘭人傳播至日本,被稱為“蘭學”。趁著“蘭學”在日本的傳播,《荷蘭傳聞書》也在這個時期傳入了日本,使得“幕府要員通過荷蘭的《荷蘭傳聞書》了解海外情況”。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荷蘭傳聞書》在當時并未公開,只有幕府大臣才有資格閱讀。“但是,(‘黑船事件后)與各國簽訂條約的結(jié)果,《荷蘭傳聞書》也不得不公開化了。”[1]而幕末時期報紙的“公開化”,其實質(zhì)是將報紙的閱讀權(quán)限從幕府要員擴大至各藩的上層人物,并非現(xiàn)代意義上以大眾為基礎(chǔ)的全社會公開化,這是由當時的封建等級制度以及封建統(tǒng)治制度所決定的。
(二)幕府官版報紙的出現(xiàn)與消亡(1862年至1863年)
幕末時期官版報紙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同當時日本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和“蕃書調(diào)所”的成立有關(guān)。1854年,日本被迫打開國門,同美國簽訂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而與此同時,《荷蘭傳聞書》的閱讀權(quán)限也從幕府降到了地方“大名”一級。同年,荷蘭政府決定直接向日本政府提供報紙,因此政府要員們也不再閱讀《荷蘭傳聞書》。
此時,在日本國內(nèi),“開國論”與“攘夷論”正在進行激烈的斗爭,國內(nèi)的輿論尚未完全統(tǒng)一。鑒于西方列強的外在壓力,幕府不得不將“開國論”作為一種權(quán)宜之計。為了宣傳“開國論”,統(tǒng)一國內(nèi)的輿論,幕府當中的開明人士也決定要將報紙公開化。安政三年(1856年),為了迎合“開國論”以及翻譯西方著作的需求,德川幕府設(shè)立了“蕃書調(diào)所”①。“蕃書調(diào)所”成立后,將荷蘭政府所提供的報紙進行翻譯,以日文報紙供政府要員閱讀。日本同西方五國簽訂《安政五國條約》后,進一步擴大了開放程度,“蕃書調(diào)所”也擴大了報紙翻譯的來源,從過去單一翻譯刻印荷蘭的報紙擴大到“翻刻了歐美人在中國的香港、寧波、上海等地出版的報紙和雜志”[2]。當時主要發(fā)行的官版報紙有:《官版巴達維亞新聞》《官版海外新聞》《官版海外新聞別集》《官版中外新報》《官版香港新聞》《官版六合叢談》《官版中外樵志》和《遐邇貫珍》。官報的出現(xiàn),雖然在幕府的“開國政策”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開化、宣傳作用,但隨著“攘夷論”逐漸在日本國內(nèi)輿論中占據(jù)上風,官報最終不得不停刊。
(三)外文報紙的影響——手抄報與外國人經(jīng)營的日文報紙的出現(xiàn)(1863年至1868年)
1.手抄報的出現(xiàn)——幕府了解海外情報的新手段
外文報紙的出現(xiàn)早于官版報紙。在《官版巴達維亞新聞》發(fā)行的半年之前,約在1861年7月②,留日英國人漢薩德(A.W.Hansard)就已在日本長崎發(fā)行了《長崎航運及廣告報》,并于同年11月移居橫濱,創(chuàng)辦了《日本先驅(qū)報》。這兩張報紙的創(chuàng)刊及發(fā)行,開了外國人在日本本土發(fā)行外文報紙的先河。之后,十幾種外文報紙陸續(xù)在幕末時期創(chuàng)刊發(fā)行。
失去了海外情報工具的幕府要員,并沒有因官版報紙的停刊而坐以待斃,他們退而求其次,命令原屬“蕃書調(diào)所”的學者組建“會澤社”,以非官方的形式翻譯外國僑民所發(fā)行的報紙,以手抄方式發(fā)行供幕府要員閱讀的手抄報。這一時期“會澤社”主要翻譯發(fā)行的手抄報為《橫濱新聞》《日本每日新聞報》《日本新聞》《日本特別新聞》《中外新聞紙》。這些手抄報發(fā)行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幫助幕府要員了解新近的海外情報,但是隨著手抄報的發(fā)展,之后“愿意看的人也可以購閱”[3]。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購閱范圍也僅僅限制在日本上層人士,平民尚無權(quán)利與能力購買閱讀。
2.外國人經(jīng)營的日文報紙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對日本報紙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的,便是“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在日本相應開放港口的執(zhí)行。依據(jù)這一特權(quán),外文報紙在日本的發(fā)行較為順利。這些外文報紙最初無外乎是以全體外國僑民為發(fā)行對象,由于不受幕府的制約,這些外文報紙也能夠大膽地對幕府進行政治批判,不僅對幕府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對發(fā)行區(qū)域的那些最早修習西學的下級武士的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隨著外文報紙影響力的增大,一些外國人也嘗試在日本創(chuàng)辦日文報紙,《海外新聞》《萬國新聞紙》《倫敦新聞紙》以及《各國新聞紙》這四種報紙是這些報紙中較有影響力的。
從過去“蕃書調(diào)所”和“會澤社”的翻譯人員參與外文報紙的翻譯,到成為記者或報社經(jīng)營人員進行新聞活動、參與報紙經(jīng)營,在西方資本主義對日本封建制度的沖擊和瓦解的這一大時代背景之下,日本近代的新聞業(yè)也在這股強大的時代變革潮流中逐漸孕育出萌芽,為此后日本新聞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二、幕末時期日本報紙的發(fā)展特點分析
(一)“自上而下”的發(fā)展模式
同西方近代報刊“自下而上”的“自然”發(fā)展模式不同,日本近代報紙的發(fā)展可謂同之后的“明治維新”一般,以“自上而下”的“逆發(fā)展”方式不斷成長。造成這種發(fā)展方式的原因,在筆者看來,有如下兩點:
第一,幕末時期的日本尚未出現(xiàn)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日本這一時期的經(jīng)濟模式依舊是以土地與農(nóng)作物(尤其是稻米)為主要財富形式的封建經(jīng)濟制度。而近代報刊作為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其產(chǎn)生的自然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以及頻繁的經(jīng)濟活動,這使得資產(chǎn)階級對各地市場信息的迫切需求也在與日俱增。因此,為資產(chǎn)階級提供必要的商業(yè)信息服務也就成為一件順應發(fā)展且必須的舉措。由于此時日本尚未出現(xiàn)資本主義經(jīng)濟土壤,那么近代報紙這棵孕育在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土壤中的小樹苗,則不會在此“自下而上”地“自然”發(fā)展。
第二,幕府面對近代報紙所采取的積極態(tài)度。與同一時期的中國對西方近代報紙采取被動消極態(tài)度所不同,幕府對報紙則采取了較為積極主動的態(tài)度。因此,《荷蘭傳聞書》成為幕府要員們了解世界的一個重要手段。此后,無論是“開國論”還是“攘夷論”在社會中成為主流并占據(jù)上風,幕府都從未停止過對近代報紙的渴求。統(tǒng)治階級之所以如此渴求報紙,是由于幕府時期日本政府同荷蘭特殊的外交關(guān)系所致。雖然幕府一直在執(zhí)行“鎖國”與“海禁”的政策,但出人意料的是,荷蘭并未受到日本“鎖國”與“海禁”政策的過多影響,反而領(lǐng)先歐洲諸國,成為幕府時期日本政府長期唯一的來自歐洲地區(qū)的貿(mào)易伙伴。
經(jīng)濟活動的頻繁,必然會帶來更加深刻的交流。因此,在日荷蘭商館成為日本文化與歐洲文化交流之地。作為附屬國,荷蘭必然要定期覲見宗主國最高統(tǒng)治者。“參拜者居住在江戶本石町的長崎屋,則成了日本蘭學者們獲取西方知識的唯一來源地。短短的兩三周滯留時間里,這里成了展開科學探討的中心。”[5]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的統(tǒng)治階級中出現(xiàn)了熱衷于修習蘭學的有識之士。無論是幕府還是各藩,這些有識之士通過荷蘭商館了解世界,這一思維慣性隨著日荷兩國的“偶然性”外交而不斷發(fā)展與深化,“蘭學為日本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培育了日本近代化的社會思想基礎(chǔ)”[6]。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幕府從沒有停止過對近代報紙的渴求。
(二)報紙發(fā)展同政治運動緊密相聯(lián)
日本同荷蘭的特殊外交關(guān)系,使得《荷蘭傳聞書》能夠在幕府要員中廣為傳播。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日本的國內(nèi)矛盾陡然升級。在這一時期,“開國論”和“攘夷論”相繼成為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流輿論。伴隨著“開國論”的提出,幕府首先將獨占的海外情報分享出來,將之前的閱讀權(quán)限由“幕府”降至“大名”一級。為了統(tǒng)一國內(nèi)的政治輿論,幕府成立了“蕃書調(diào)所”,將外國的報紙翻譯后以官版報紙的形式進行發(fā)行,以報紙為載體,進行“開國論”的政治宣傳。
隨后,由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及幕府與各藩的矛盾日益激烈,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作為一種權(quán)宜之計的“開國論”,也不得不在日趨強烈的“攘夷論”的政治輿論與政治運動面前沉寂下去。各藩雖名為力行“攘夷論”、為其搖旗助威,實則是以此為突破口,欲推翻幕府統(tǒng)治,實現(xiàn)“大政奉還”和“王政復古”。此時,日本出現(xiàn)了兩大政治陣營——佐幕派和尊王派。在隨后的倒幕運動中,除了歷史上著名的鳥羽、伏見之戰(zhàn)外,兩大政治陣營對輿論高地的爭奪,也是非常激烈的。在這一時期,各派涌現(xiàn)出眾多報紙,佐幕派發(fā)行的有《中外新聞》《日日新聞》等;尊王派發(fā)行的報紙有《太政官日志》《各國新聞紙》《內(nèi)外新聞》《都鄙新聞》。
三、幕末時期日本報紙發(fā)展的現(xiàn)實動因分析
(一)日荷兩國特殊的外交關(guān)系
第一,從兩國關(guān)系的淵源上來看,三浦按針曾說服德川家康同意對荷進行經(jīng)濟往來,開啟了兩國的貿(mào)易通商大門。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航海長的英國人威廉·亞當姆斯,由于海上遇險,其船隊被迫駛往日本進行避難。機緣巧合之下,威廉·亞當姆斯被德川家康任命為自己的通商顧問并授予封地,改名為三浦按針。此后,在其斡旋下,德川家康同意與荷蘭進行通商,開展經(jīng)濟貿(mào)易合作,成功開啟了日荷兩國近300年的通商貿(mào)易大門,為日后日荷兩國的外交奠定了基礎(chǔ)。
第二,荷蘭對日所采取的貿(mào)易政策與外交手段。為了追逐自身經(jīng)濟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維護在整個亞洲地區(qū)的經(jīng)濟勢力,荷蘭對亞洲地區(qū)不同國家采取了靈活多變的貿(mào)易政策與外交手段。荷蘭在制定對日貿(mào)易政策時,有意將對宗教隨商業(yè)活動進行傳播這一傳統(tǒng)徹底摒棄,以此來博得日本的好感。此外,荷蘭還以附屬國身份向日本稱臣,以外交上的臣服換取在日的經(jīng)濟特權(quán),更加鞏固了荷蘭同日本的外交關(guān)系。這為荷蘭獲得在日本的經(jīng)濟特權(quán)奠定了基礎(chǔ)。
荷蘭靈活的對日外交政策,使得其在日本的經(jīng)濟活動以絕對優(yōu)勢領(lǐng)先于西歐諸國,并為歐洲了解日本提供了最具優(yōu)勢的第一手材料。同樣,由于日本同荷蘭的這種“專一”的對外關(guān)系,荷蘭也就成為日本了解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作為具有近代報紙性質(zhì)的《荷蘭傳聞書》,也是隨著日荷外交的這股東風,吹進了封建時代的日本,為日本此后了解和接受作為新興事物的報紙奠定了基礎(chǔ)。
(二)“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的確立與日本部分主權(quán)的喪失
自“黑船事件”始,幕府時期的日本主權(quán)不斷受到西方勢力的挑戰(zhàn)和侵蝕。1854年,日本同美國簽訂《神奈川條約》。1858年,江戶幕府先后同美國、荷蘭、俄國、英國以及法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史稱《安政五國條約》。除此之外,“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的確立,造成日本部分主權(quán)的喪失。在“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的影響下,幕府日本無權(quán)對外國人在日本領(lǐng)土內(nèi)的一切行為進行管轄與法律制裁。同樣,對于外國人此時在日本創(chuàng)辦發(fā)行報紙,幕府亦無權(quán)管轄。這也就是為什么留日英國人漢薩德能夠在日本發(fā)行官報之前就在長崎發(fā)行《長崎航運及廣告報》的原因。正是在這一不平等特權(quán)的庇護下,外文報紙以及由外國人創(chuàng)辦的日本報紙能夠如雨后春筍般在日本順利成長。主權(quán)在開放港口的喪失,客觀上促進了近代報紙在日本的生根發(fā)芽。由于保守與專制的封建幕府無權(quán)對這一在開放港口發(fā)展的新興事物予以任何制裁,這為報紙在日本的發(fā)展與傳播提供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
四、結(jié)語
本文通過對日本幕末時期報紙的歷史發(fā)展脈絡的梳理,發(fā)現(xiàn)在這一時期中,日荷兩國的特殊外交關(guān)系對后來日本包括報紙在內(nèi)的近代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本文雖沒有涉及中國近代報業(yè)的發(fā)展,但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在同一個時間維度下,日本對新興事物采取了同清末中國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日本明治維新能夠在短時間內(nèi)成功地將日本塑造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
注 釋:
①后改為“洋書調(diào)所”,是進行西學教育、翻譯西方著作、檢查進口書籍的機構(gòu),也稱為“開成所”。
②《長崎航運及廣告報》的創(chuàng)刊日期,是根據(jù)山本文雄的《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史》中“在《官版巴達維亞新聞》創(chuàng)刊半年之前,《長崎航運及廣告報》就出版了”所推斷而來的。
參考文獻:
[1]山本文雄,山田實,時野谷浩.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史[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1—5.
[2]山本文雄,山田實,時野谷浩.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史[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2.
[3]山本文雄,山田實,時野谷浩.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史[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5.
[4]諾曼.日本維新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14.
[5]高淑娟,馮斌.中日對外經(jīng)濟政策比較史綱——以封建末期貿(mào)易政策為中心[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275.
[6]高淑娟,馮斌.中日對外經(jīng)濟政策比較史綱——以封建末期貿(mào)易政策為中心[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275.
(作者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