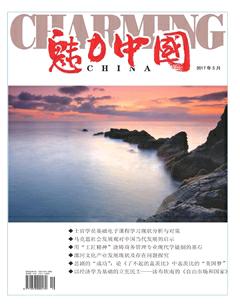悲劇的“成功”:論《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蓋茨比的“美國夢”
張子恒++徐忠明
摘要:《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扛鼎之作,作者使用獨特的敘事與象征手法,描述了二十世紀現代化的美國社會的浮世繪。本文結合美國歷史分析作品的時代背景,解讀故事情節,同時,筆者從批評的視角分析這一作品的主人公的悲劇化的“成功”和“美國夢”的破滅成因, 探究其中所隱含的深刻含義。
關鍵詞:《了不起的蓋茨比》;時代背景;成功;美國夢
一、引言
(一)作品影響。
《了不起的蓋茨比》問世已經有九十余載,該作品甫一出版就迎來文藝評論界的如潮好評。在《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十周年之際,美國蘭登書屋就決定將此小說收錄進“現代叢書”榜列之首。至今,《了不起的蓋茨比》已經被公認為美國現代小說中的優秀小說之最。同時,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因此榮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文學“編年史家”及“桂冠詩人”的稱號,成為美國“爵士時代(Jazz Age)”和“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 文學的代表作家,與同時代的海明威、德萊賽、凱瑟齊名,以美國文學四駕馬車載入史冊。
(二)時代背景。
一九二二年七月,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手醞釀此部小說。歷史上的美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正在進行著原始農業社會的逐步瓦解,并且,美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勢野蠻侵襲這人們的方方面面:原始田園風光逐步地消失殆盡;工業化的批量生產形成滯脹窘況;城市化建設的突飛猛進造成資源短缺;更為致命的是,社會轉型的驟變使人們的古樸民風與淳樸情懷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心態浮躁、消費主義盛行、狂歡化甚囂塵上。簡言之,“爵士時代”的負面作用滲透到人們的生活表層及思想深處。
從十八世紀就倡導的“美國夢”歷經弗朗克林、杰斐遜、卡內基等美國社會先鋒的描繪,畫面無限優美:人們奢望這在美國這塊充滿機會與財富的豐茂土地上,只要遵守現存的社會體制與社會準則,就會獲得社會地位的認可與物質財富的成功。然而,時過境遷,曾經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的如此美好的“美國夢”發生了變化,“美國夢”開始逐漸地變成了頹廢、腐朽的代名詞,人們也不再把最初的“自由、平等、民主”奉為神明。人們最初的艱苦工作、生活的節儉等價值觀念逐漸變得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出現的享樂主義。無情的現實擊碎了這樣的美國大眾美幻之夢,無法面對的骨感現實是這樣的:傳統信念道德淪喪,拼命工作卻朝不保夕,即將席卷全國的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把大眾推到生存的生死邊緣。
(三)故事梗概。
菲茨杰拉德在這部小說中運用了獨特的敘事手法和猶如挽歌式的敘事基調,創設了尼克·卡拉韋這個“身兼兩職”的人物--既身在故事之中有身在故事之外:一九二二年的春天,作家尼克滿懷“美國夢”離開位于美國中西部的家鄉,夾裹于淘金熱的大潮之中來到了當時的新興城市紐約,彼時的紐約爵士樂流行,股票飛漲,但是貧富差距嚴重的兩極分化,富人沉淪在紙醉金迷當中。綜合而言,菲茨杰拉德“一方面書寫著重建信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揭露了重建信仰的不可能。”[1] ( p .75)尼克為了“美國夢”的實現,放棄寫作而進入了證券市場,供職于“誠記信托公司”,并搬入位于紐約附近的海灣區域埃格(egg)村居住,毗鄰于神秘富豪蓋茨比。而在海灣對岸住著尼克的表妹黛西以及她的貴族丈夫湯姆·布坎南一家。浸淫于蓋茨比、黛西、湯姆的復雜關系之間,尼克漸漸地迷失在這個充滿魅力、愛、抱負、謊言的世界中。尼克常常被邀請參加蓋茨比豪宅中的盛大狂歡晚會,意外發現了蓋茨比心中的秘密,原來,他一直深愛著已嫁人的黛西,但是,戰爭的造化弄人,黛西沒等到他戰后載譽歸來,卻迫于形勢嫁給富豪湯姆·布坎南,蓋茨比一直深信他和黛西的愛情歷久彌堅、矢志不渝。而尼克作為蓋茨比與黛西、黛西與湯姆之間亦真亦假的愛情見證者,最終在歷經蓋茨比被謀殺及謀殺之一場凄清的葬禮,蓋茨比的人生畫上了悲劇式“成功”的句號。尼克看盡了這個時期上流社會的糜爛混亂及人與人之間的虛情假意、人間冷暖與居心叵測,幡然醒悟到美國夢的國家化破滅,隨后離開這個喧囂、虛假、浮夸的大都市,黯然回到了自己的中西部故鄉。
二、美國夢破滅陰影下的悲劇式“成功”及成因分析
(一)紙醉金迷的美國淘金熱與覆滅的先兆。
美國的20世紀20年代是處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特殊歷史時期。這期間,美國經濟經歷了從戰后的迅猛發展, 到 1929 年紐約股市崩潰后十年經濟蕭條這一戲劇性的兩極變化。一戰后的富足、安逸的生活使人們在混亂與喧囂中頭暈目眩;而與此同時, 美國的知識分子卻紛紛出走, 進行文化的自我流放, 他們在痛苦和迷惘中度過自己孤獨的青春。這是個充滿運動、變革、反叛的時代,年輕一代發誓走上與傳統決裂的不歸路。蓋茨比身處如此的洪流之中,注定了他的迷惘、孤獨與毀滅。
這部小說的主題旨在追問一個問題:“到底美國夢是什么?”,主角蓋茨比無疑是代表了那個時代大宗最直接的精神訴求:我不斷努力賺到更多的金錢,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利,通過自己的努力,盡可能快得從一個無名小卒(nobody)變為叱咤風云的大人物(somebody),然后帶著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去追回過去,追回那些當年自己拿不到的一切。當時“享樂主義”腐蝕人們價值觀、人生觀,數年后,他自己豪宅里所有的樂隊、盛宴、舞會、美酒,就是為了追回五年前失去的一切的有力證明,然而,當時美國證券市場的暴跌大局和大蕭條的出路端倪鑄就了蓋茨比這種“成功”的悲劇。
(二)黛西(Daisy)的秉性加劇了蓋茨比“美國夢”的破滅。
蓋茨比癲狂的執著于實現自己五年前的遠大抱負,即他的宏偉“美國夢”,但他將這一“成功”假托于擁有若即若離的黛西,在蓋茨比的混沌意識中“她是他所認識的第一個‘大家閨秀”[2] ( p.125) ,事實上,黛西根本無力承擔起這樣的角色。黛西僅僅是一個委身于以享樂為人生終極目標的資產階級體制下的蛇蝎女人,她沒有情操,沒有思想,沒有真愛;她只是徒有華麗外表,而內心淺薄虛偽、冷酷無情、水性楊花。嫁給湯姆·布坎南是因為當時湯姆的財富使然,在當時的窘況時候,她感到“他的身材和身價都很有分量”[3] ( p .122);與蓋茨比重敘舊情是因為蓋茨比向她虛構的奢華與富貴使然,蓋茨比把黛西當作了“他的理想和人生目標”[4] (p .92),蓋茨比一方面利用他那虛幻的百萬家財給黛西造成一種安全感,“讓他相信他來自跟她同一個社會階層--相信他完全有能力照顧她。”[2] (p.125),黛西的秉性決定她絕不可能為實現蓋茨比的“美國夢”與成功而犧牲她自己的既得利益。
三、結語
在美國那樣的商業時代,人們在物質上追求奢華高調從而變得越來越拜金,精神上的越發荒涼和物質上的豐盈出現劇烈的反差之后,整個人自然就會越來越像遵守叢林法則的動物,人們為了達到人人私利而不擇手段,蓋茨比與黛西各為了實現他們“偉大”的成功與美國夢而無法做出精神和情感犧牲的決心。消費主義盛行的洪流中和“迷惘的一代”背景下“似乎只有蓋茨比懷有夢想并苦苦的追尋夢想”[5](p .193)。此悲劇的“成功”投射出的是當時年代與體制下人們精神的悲涼和思想的貧瘠。
參考文獻:
[1]徐娟,任龍.《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神秘意象再探析[J]. 世界文學評論,2015(5)
[2]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 姚乃強 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3]蘇煌. 夢里不知身是客--《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悲劇意識探析[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8)
[4]王丹紅.蓋茨比悲劇的必然性分析[J]. 世紀橋,2010(1)
[5]王洪欣. 論《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蓋茨比的孤獨[J]. 海外英語,2012(6)
作者簡介:張子恒(1996- )男,嘉興學院南湖學院2015級本科生;
指導老師: 徐忠明(1969- )男,講師,研究方向: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