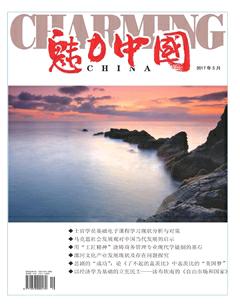試論楷書入唐至巔之原因
呂杰
摘要:楷書源于魏晉,發展于南北朝,至唐逐漸發展成熟。“楷書”從字面上來理解,具有兩層含義:“楷”,在古詞典《廣雅》上注有法式,典范。楷,法也。所以凡遵循法度之書,皆可稱為“楷書”。二、狹義上的楷書是與篆書、隸書、草書及行書相對的點畫工整、結構堅穩的書體,典型的例子如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唐楷”。
關鍵詞:唐代;楷書;科舉;抄錄;石刻
李唐三百年,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文化進入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李唐初立,統治階級為了安定民心,重新穩定社會秩序,儒家重新占據了統治地位。至太宗“崇王”書風演為書學正統,重視書法,科舉考試要求“楷法遒美”,“皆得正詳”,形成初唐時期的書法風潮,但“王政統治”的潛意識是無法規避的,使得書法成為“禮法”之下的藝術。
第一、科舉制度的刺激
唐代沿襲隋代創立的科舉制度,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在科舉考試當中,所有的內容都需要通過文字來表達。所以天下考生都把文字書寫當做科舉考試中頗為重要的一環。當時東西兩京的國子監,各設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
除書學科的學生外,其他諸學如國子、太學、四門的學生,也規定“學書,日紙一副”。至于弘文、崇文兩館的學生,也必須“楷書字體,皆得正樣”。地方上的府學、州學雖然沒有明文記載,但從貢舉得科目設置上看,書法也與中央一級的學校列為重要的教學內容。唐代科舉,設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明書即書學,考察學生對各種書體的掌握程度。
唐代還有一種考核六品以下官員的制度——銓選,銓選的考核依輔四條基本準則,即所謂的“四才”。身、言、書、判,銓選一年一選,全部合格者授予官職。而書寫水平即文字的易識程度直接影響判案時訴訟的公文質量,因此“書”其實是“四才”的重中之重。
第二、玄學的式微與儒術的發展
玄學的式微,儒術作為唐太宗政治教化、重拾人心的思想武器,雖然不再是秦皇式的“獨尊”地位,但也是有唐一代學術思想中最為重要的一元,唐王朝大力提倡儒學,兼及佛道,著述典藏蔚然成風,“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抄書”成為了一種“工作”,“經典”最重要的功能是教化育人,而教化育人的前提是“經典”要能夠讓普通“白丁”看的懂。
朱長文《續書斷》云:“唐世寫經類可嘉,紹宗者猶屈為僧書,則寫經者亦多士人筆爾。”這類作品書寫者的書寫目的,與官楷的書寫者“干祿”的目的類似,通過抄經獲得政府的津貼或寺院、地府富商的接濟,維系生活。
因此,北碑這種或長或短,或正或斜的形式不見了;此前用筆的忽提忽按,忽偏忽正的隨意性也不見了,“皆得正詳”的楷書正具有這種特點。
第三、豎石立碑的盛行
石碑的風行也在客觀上推動了書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只要立碑就要有書法,碑石刻字,當然楷書最宜。再加上唐代風行立碑,凡立碑大都是為碑主歌功頌德。要刻鐫、立碑需要物質條件的支撐,如書丹、石料的選擇,聘請技術精湛的石刻匠等,其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并不是普通平民百姓所能夠承受的起的。而達官貴人一旦參與進來,就像以書取士以書試吏一樣,又必然是個文化層次的規定。
第四、文房用具的發展
書家所用筆、墨、紙、硯,雖有歐陽詢、虞世南不擇紙筆,但也因人而異,各有所宜。如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至晚唐柳公權要求就更加精細。
宣紙源自東漢,唐書論家張彥遠所著之《歷代名畫記》云:“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這說明唐代已把宣紙用于書畫了。
朝廷用紙,全部出自各地雜貢,《唐六典》卷二十記:“杭、婺、忂、越等州之上細黃白狀紙,均州之大模紙,宣、忂等州之案紙、次紙,蒲州之百日油細薄白紙,河南府、許、衛、懷、汝、澤、潞等州之兔皮。”[2]而其中宣城郡紙最為精美,可見宣紙在當時已冠于各地。
李唐用紙,開始區分“生”“熟”,“熟者妍妙輝光,生者不經洸治,粗澀礙指,非喪中不敢用”[3]。
唐代各級政府公文用紙也十分講究,葉夢得《石林燕語》中記載“唐中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為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日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貞觀間。
唐代制筆較于前代也有較大發展。至唐武宗,江西散卓筆,一改兼毫樣式,冠以純羊毛,吸收創新,為時人所贊。后世書家黃庭堅在其《山谷題跋》中記“老羝拔穎,霜竹斬竿。雙鉤虛指,八法回腕。張子束筆,無心為樸”[4]。當時風靡的有陳氏筆、諸葛筆、宮廷筆等等。
在古代,墨分為石墨、松煙兩種。自魏晉以來,崇尚松煙,唐時以不見石墨。唐代在易州設有墨官。陸友《墨史》記:“祖敏,本易定水人,唐時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為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于天下。”
除卻官墨,唐代文人制墨之風也很繁盛。李陽冰曾制墨至于長安相國寺。
硯為終身享有,雖未四寶之首。文人玩硯,追求的是文化隨時間在硯臺中留下的歷史積淀,而不是追逐新穎,所以,在唐代硯更多的是因時、因地、因人而各不相同,沒有商品化的集中出現。
筆墨紙硯的不斷發展與品類的不斷細分,對于書家的藝術創作,對于書法的廣泛傳播,對于藝術品德長期保存乃至流傳后世,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楷書之所以在唐代發展至巔峰,與唐代的社會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隨著唐代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逐步制度化,楷書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楷書也隨著社會需要的背景和自身的發展規律逐步地法備體嚴,成為唐朝社會應用最廣泛的字體之一,因而文人士子必須掌握楷書的書寫技藝。隋唐時期出現的知名楷書家有智永、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人,他們留給后人的豐碑巨制,堪為后代楷書的典范之作,也正是他們的實踐鑄就了中國楷書發展的巔峰。
參考文獻:
[1]陸心源.《唐文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
[2]張說、張九齡等.《唐六典》.中華書局.
[3]李日華.《六研齋筆記》.鳳凰出版社.
[4]黃庭堅.《山谷題跋》.上海遠東出版社.
[5]朱關田;《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蘇教育出版社.
[6]周倜.《中國歷代書法鑒賞大辭典》【M】.北京燕山出版社.
[7]喬志強.《中國古代書法理論解讀》【M】.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8]邵軍.唐代書畫理論及其審美觀研究【J】.美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