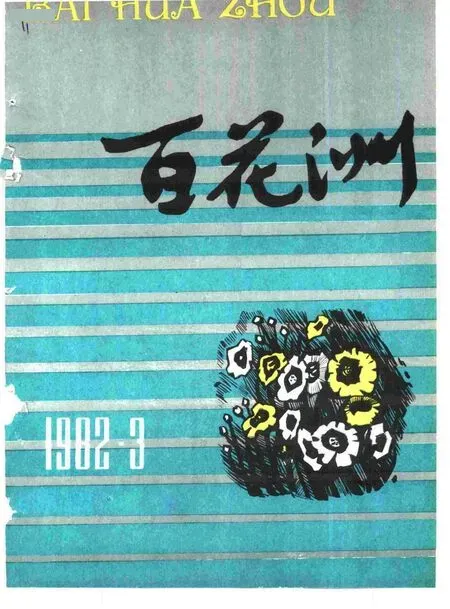一幅沒有歸還的畫
杜璞君
一
劉早的眼睛與那幅叫《凝》的油畫中的女人成了一直線,畫中的女人好像也正凝視著他。
劉早搬來碉廬街,租下這座叫六乾居廬和鼎坤別墅的雙子樓住下,周圍很靜,空寂得甚至讓人嗅出死亡的氣味,一根針掉地上,都恍若炸雷,除了他剛才翻動書頁發出輕微的響動外,屋里再沒有動靜。他很快將目光從這幅畫上移開,把滑落下來的天鵝絨重新蓋上。
我和幾位朋友到劉早那兒做客。老葛頗有興致欣賞著劉早租下的這座雜糅了西洋建筑風格的民國老宅。他指著窗戶柵欄說,當時我們中國沒有這么好的冶煉技術,這些鋼材是英國造的,不過式樣滲入了傳統元素,你們看這上面的福字圖案。在衣帽間,他忽然喊道:“你們快過來,老宅藏著一幅百年油畫。”我們聞聲跑進衣帽間,油畫里的女子一下把我們“吸”住了,色彩有點龜裂,女人站在鐵軌上,望著蜿蜒通向遠方的軌道,神情寫滿渴望。雪山作背景,人物與景色都流露過去的時代特征,但顯然并非什么百年油畫。
當我想留意這幅畫的作者是誰時,劉早在我們身后,陰沉著臉說:“這畫還沒畫好,你們不要動!”我們不知劉早會畫畫,提出要欣賞他的畫作,被一口回絕:“如果你們是廚師,喜歡人家跑進你們的廚房去參觀嗎?畫畫是我的秘密,你們來做客,不是來打探的。”
這幅劉早自稱未完成的作品意外暴露,引起了我極大興趣,我似懂非懂地說:“畫得挺成熟的,劉早。賣了,怎樣?說不定很撈錢呢。”
劉早臉色有點瘀青說:“我操,請你們來,簡直是鬼子進村。”
我們只好收斂住一時間的興奮,提議搓麻將。牌桌上劉早滿腹心事,全不在牌上,輸了好幾千了,忽然像跟我們說,又像自言自語:“其實畫是否畫完不重要,如果可以賣掉,錢多錢少無所謂,這秘密你們發現了,我就講一下這畫的故事吧。”
廣州火車站站臺鑼鼓喧天,高音喇叭不斷播放著:毛主席教導我們,世界是我們的,更是你們的,知識青年應到廣闊的農村天地去。我們廣大的知識青年應當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每個年輕人都熱血沸騰地積極投身到這項運動。丁柳強忍淚水,不時向人群張望,但是在人群眾中,她沒有發現劉早。
丁柳住在劉早對面,因家庭成分出身不好,丁柳上山下鄉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劉早因是家中獨子,父母又是工人,就得以留在城市。不過,劉早一家都是工人,所以,丁柳兩家人很少來往。那時劉早已經愛亡畫畫,有一次給丁柳畫了一幅速寫,丁柳發現了,很喜歡,覺得他繪畫悟性很高,就瞞著父母,暗中輔導劉早,劉早很快打下了堅實的繪畫基礎。
劉早望著火車駛離站臺,駛出很遠了,他站在站臺上向遠去的列車揮手。望著火車駛離后的鐵軌,剛才遠去的火車還留下那么一聲長鳴,持續而又低緩。現在就剩下一條空寂的軌道。劉早說,從那時候起,我就懂孤獨是個什么滋味。
劉早曾偷偷想到深圳寶安看望下鄉的丁柳,卻給父母發現了,將他從車站強行拉回家。劉早的父母一邊哭一邊罵,你不知道她父親被查出是個“反革命”,由下放勞動改成關進監獄。她父親剛抓了進去,難道你想我們整個家都牽扯進去,跟著這家人葬送了我們全家才甘心嗎?
劉早與丁柳曾經偷偷通過信,但后來被發現,從此丁柳杳無音信。丁柳來信中有一句話劉早至今沒有忘:沿著鐵路,我可以回家。
劉早說完他的故事,一片菩提樹葉從書頁夾縫里掉到地上。他撿起這片菩提葉,掏空曬干后的葉片剩下清晰的葉脈。劉早端詳那些縱橫交錯的葉脈,指著自己的心說,掏空了。丁柳走后,這都掏空了。
劉早跟大家談起這段經歷時,我確實被感動過,而且跟隨他的講述,想象《凝》里面的女子,沿著鐵路,又跳又笑,有時惦著腳尖在鋼軌上行走,有時單腿跳著向前,而她的目的地就是家。我仿佛感覺到一個女子在那個年代,沒有情欲的啟蒙,由身體散發出來的一種純真而又不失浪漫的色彩。
我想起有一次陪劉早到廣州最大的一座寺廟光孝寺。去的時候將近黃昏,斜陽從一棵枝葉茂盛的菩提樹的枝叢間漏下,夕照從葉子邊緣散射出光芒,秋風中菩提葉紛紛飄然而下。我們嗅著秋天氣息中送來的一陣熟悉的香氣,那是浮蕩在秋日的黃昏中白蘭花的香氣。這淡淡清香不期而至,他深吸了一口氣,努力捕捉這香氣來自何處。他對我說:“我是不是很傻,我忽然想會不會是丁柳就在寺廟的某個角落,捻著一串佛珠,跟隨著寺里的暮鼓,嘴唇翕動誦經。”
我們在菩提樹下走了一圈,尋覓香氣是否與這棵菩提樹有關。腳踩在飄落地上的菩提葉,發出輕微的脆薄聲響,讓我們感到親切而又熟悉的白蘭花香氣,總是若隱若現地飄過來。他告訴我,這么多年過去了,丁柳長什么樣,都有點模糊,但屬于丁柳身上獨有的氣息從來沒有忘記,丁柳很喜歡白蘭花清新的香氣。
他再努力吸了一口氣,秋天清爽的氣息,很沁人。這時候一位僧人,敲著棒子,從大雄寶殿經過,催促僧眾上晚課。夕照掛在大雄寶殿黃色琉璃瓦的一角,整座寺院在黃昏的光影下,端嚴肅穆。大雄寶殿傳來有節奏的鼓聲,使得周圍更顯得寧靜,但那淡淡的白蘭花的香味,依然繚繞著。
距大雄寶殿不遠,定然法師的僧舍門開著。我們走了進去。定然法師身穿褐色的僧袍,盤腿端坐在一張盤龍酸枝椅子上。他嘴唇輕微地翕動,手上一串念珠在指間滾動。有一婦人,向定然法師叩拜后,向法師稟告:“師傅我這段時間覺得心里鬧得慌,很不舒服。”定然法師,略睜雙目,只回答了三個字:“看醫生。”就繼續微閉雙目念經。婦人轉身走了。
定然法師的回答有點出乎我們意料,他不打妄語,很簡潔地導引婦人沿正途尋醫問藥。
劉早上前叩拜定然法師,說:“師傅,我與一女子有一段情緣,不知是否可以再續。自知根器淺,情欲的種子根深蒂固,我鐘情于她,但不知她身在何處。”
定然法師手中的念珠,仍然在指尖一顆又一顆滑過去。劉早將沉積于心中的相思一股腦兒端到法師面前,定然法師像回答那婦人一樣,很簡短地回答了劉早三個字:“多念佛。”
夜色已溜了進來,定然法師的僧袍罩上了黃昏的暗影。法師微閉的雙目下,嘴唇翕動,他指尖滾動的念珠的輕微的摩擦聲也融入這黃昏。我與劉早放輕腳步退出僧舍,回頭看了一眼定然法師手上那串佛珠。
寺院上空是一片歸巢鳥兒的鳴叫,它們在斗拱瓦檐間呼朋喚友。幾聲鐘磬之聲傳來,那白蘭花的香味依舊在我們鼻翼間徘徊,但劉早尋不到這神秘的香氣來自哪里。
二
劉早在不同場合反復講述他與丁柳的故事,我覺得奇怪,難道他想把自己裝扮成情圣嗎?我與劉早認識是在西藏的雪域高原。那年我在網上約了幾位驢友到西藏。我在拉薩跟著藏民沿著大昭寺,順時針轉經。八廓街上一個背有點駝的藏族老阿媽,吸引了我的目光。那老阿媽搖動著經筒,繞著大昭寺來來回回。我跟在老阿媽背后,轉了幾圈后,我就覺得累,到瑪吉阿米餐廳喝甜茶去了。那老阿媽仍心無旁騖地轉經,她了心中的佛,身邊發生什么,是否有人關注她,老阿媽都沒有去在意。我則凡心未了,經過唐蕃會盟碑外的一段白墻時,想起驢友對這段白墻的另一個稱謂——艷遇墻。
唐蕃會盟碑對面有一片空地,前面就是大昭寺,這里從早到晚聚集了大批藏民,他們不分男女,身邊備一壺酥油茶,向著大昭寺里面供奉著的佛,磕無數個長頭,不管刮風還是下雨,他們無數次地匍匐下去。我無法知悉藏民心中有著怎樣的虔誠,使得任何一種力量都無法摧毀他們心中的信仰。
我在瑪吉阿米餐廳找了個位置,要了杯甜茶。隨手將堆滿架子的留言簿抽了一本出來,寫下一句:“我騎著一匹白馬在措那湖奔馳,雨落在拉薩的時候,你拿傘過來,我在瑪吉阿米等你,楚留香。”
經過十幾天高原跋涉,我瀏覽起相機視窗里拍下這一路來風霜雨雪的收獲,擺弄起手中的“長槍”。我身邊不知什么時候多了一位從北京來的叫包曼的女孩子,她偷眼看了我相機里回放的照片,見她看得眼睛都不眨,問我你都去了哪些地方?我開始講述我旅途的故事,繼續回放相機視窗上的圖片。景色的壯美和鏡頭下的細節,獲得了包曼美女一陣陣的贊嘆。包曼顧盼間,那雙明亮的眼睛,仿佛對我這位網名叫“楚留香”的旅行者,投來了英雄式的回眸。如水的春潮,泛起的漣漪,足讓我臉上平添幾分得意和自信,這時真飄飄然地感到頗有點大俠楚留香之風。
我神秘地對包曼說:“我這次到阿里轉山了。”那神情語調,仿佛要為我講述所經歷的生死劫,做好鋪墊。
“你去阿里了?”
“對,阿里。”
“進入無人區,見到藏羚羊了嗎?”
“那是小意思,我每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行走,藏族人一生的理想是到布達拉朝圣,此外就是到阿里轉山。我從早上9點鐘出發,開始轉山,到深夜12點多回到宿營地,腿都不會走路了。不過當我向神山拋撒經幡時,我就感到了了一段宿世因緣,哪怕我死在轉山路上,我也不后悔。”
“你怎么這樣說呢?”
“對于藏族朝圣者來說,能死在轉山路上,是有福的。山上拋擲了很多亡者的衣物,走在我前面的一個印度香客,我追上他時,他躺在山路上,我用英語問他的同伴:‘他累了吧?他的同伴用英語回答我:‘他魂歸天路了。”
“天呀,你還要繼續轉下去。”
“這是信念,只要你心中有信仰。”
我再次收獲了這女孩一個很甜的笑作為回報。
與我們一起的驢友劉早,他一臉的絡腮胡子,看上去比較像個搞藝術的,又有點滄桑感。我對他說,您這種波西米亞氣質,對女人是見一個殺一個,沒有不主動投懷送抱的。劉早在一旁看著我身上的荷爾蒙燃點起陌生女孩的雌性激素,弄得《家女孩臉上撲閃撲閃的,他卻一直保持沉默。有時為避免讓人有拒人千里之感,就偶爾笑笑作為回應。聽他說這次來西藏是應出版社之邀,到西藏尋訪倉央嘉措的足跡,拍下圖片供出版社使用。他身上那種酷勁兒好像是來西藏修行的。
我們話題自然就扯到倉央嘉措上。劉早終于開口,他好像對這位雪域圣者特別崇拜,他說倉央嘉措離開昏暗的布達拉宮,內心所經受的煉獄般情感的煎熬,不是我們這些匆匆過客所能領悟的。他踏著雪痕,在俗世的歡愉和情欲中,徹悟色空。劉早說著說著亢奮得喝起酒來,還興之所至吟詠起:“在那東方高高的山尖,每當升起那明月,瑪吉阿米醉人的笑臉就冉冉浮現在我心田。”他向我們解釋,這首詩是圣者倉央嘉措,轉山轉水,修來世,與其心中瑪吉阿米相遇后所寫下的第一首詩。“這次到西藏四處尋覓倉央嘉措的蹤跡,卻遍尋不遇,但我覺得他其實已經在我的心里了,見與不見,他都在那里。”他說完目光移向蒼藍的天空,陽光從大昭寺上的大金剛輪投射在圣城上,我往窗外的八廓街看了看,那搖動經筒的老阿媽,仍在繞著大昭寺轉經。
劉早憑酒借意,大發的這通倉央嘉措的高論,三兩下就將我的風頭蓋了過去,我擔心他搶了我在包曼心中的地位,卻不料包曼眼里裝的只有我一個人。我心里暗自得意,后來從包曼口中獲得了更加充盈起虛榮的解釋。她告訴我,怎么看都覺得劉早這人很愛裝,而且他越顯擺得像個詩人,我就越看他像個瘋子,一會兒冷一會兒熱,神叨叨,隱隱還覺得他這人身上有股煞氣,有點怕他。
劉早帶我們住進一間叫修來世的旅館。修來世的老板把我們叫了過去,招呼我們:“畫家,來喝杯我泡的茶,泡這茶的水,可不一般,是大昭寺的圣水。”我這時候才知道劉早還有一個身份是畫家。老板泡茶的茶葉說不上好,但喝進口里的茶,卻特別的甘甜。
我說:“真是好茶,哎,對了,剛才有位女房客,穿著好看的藏袍,住幾號房間?”
老板自以為看穿我的心思,似有所指地說:“來拉薩的人,都想有一場艷遇。不過客人的隱私,我們不方便透露。”
“那倒不一定,畢竟在高原旅游,若可以同行,不妨搭個伙,有個照應。”
老板見我有點懊惱,就笑呵呵地打圓場:“凡事都講一個緣字。”不失時機地叫人擺開文房四寶,討好地對劉早說,聽說畫家寫得一手好書法,既然我們這么有緣,就留下一幅墨寶吧。老板的盛情劉早不好推辭,更何況老板表示要減免我們的房費,劉早就乘興在案頭寫了幅“因緣隨駐”相贈。
夜里聽到有人在唱歌。修來世是座有百年歷史的藏族民居改建的旅社。墻身有一米多厚,但那女子的歌聲依然穿透墻身傳了過來。那歌聲沒有伴奏,全是清唱,高亢嘹亮。先是一個算不上專業的男人在唱,我一聽是劉早的歌聲。不久女聲和應了上去。我被這女子的歌聲吸引,循歌聲走到劉早的房間,里頭坐著的,除了修來世的老板,還有一位我早留意到的穿著藏袍的女子,她是我想讓修來世老板引薦卻被婉拒的那個女人。這女人用婉轉的歌聲為劉早伴唱。從修來世旅館的老板口中得知,她是來自四川的一位歌手。當一首曲子唱完后,女子對劉早說,劉老師,我愿意跟你走,哪怕你到天涯。
我們馬上起哄,劉早只是很含蓄地說:“我們喝酒吧。”他將一杯酒一飲而盡說:“我忽然覺得丁柳就在這間修來世旅館。”
八廓街傳來了雨聲,仍有藏族人冒雨繞著大昭寺轉經。
三
劉早心里牽掛著在鐵路消失的丁柳,我與包曼卻早打得火熱,床是上了,但沒想過要跟她結婚。包曼把我拉到北京,軟泡硬磨讓我留在北京。說有辦法幫我安排工作住宿,甚至戶口遷進北京都不是問題。我以父母年邁需要照顧為由,婉拒了她的好意,但沒想到她亮出了皇城根兒女人的霸氣,先把我留在一個刊物編輯部里,硬塞一個主編給我做,后出動父母要挾,我這才知道他父母在北京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混,我是大氣不敢出,但這皇城根長大的女子真有點辦法,我生活上很多事情不用操心,就水到渠成地辦成了。不過這對于我這個本身就是草根階層,又習慣了南方潮濕溫潤的天氣的人來說,北方的凜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我想著法子逃離包曼的控制,我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離開這座被霧霾和交通困擾的北京,另一個原因就是劉早。我忽然對劉早與丁柳的愛情來了興趣,想探究他們背后的故事,以他們的愛情為背景寫部小說什么的。我要在時間的碎片中,重新將一位神秘失蹤的女人打撈起來,尤其是《凝》那幅油畫,雖然無法弄清,這畫的真正作者是否是劉早,但將《凝》跟劉早與丁柳的愛情故事結合起來,是很可以炒作的賣點。我覺得非要借助北京這個文化中心的優勢不可。
我對劉早談了設想,根據他和丁柳的故事,圍繞這幅油畫《凝》做文章,一試市場的水溫,若能打響,再把他手頭的畫推出去。《凝》背后那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愛情故事,本身就很具有吸引眼球的市場向心力,而劉早之于這幅叫《凝》的畫,就成了難以消減一個女人之于一個男人,滅裂而后已的明證。
劉早是無可無不可,他不積極不反對的態度,促使我在798幫他舉行了一個畫展。我們事先談妥,若畫展上畫能大賣,我們就五五分成,條件很苛刻,沒想到劉早竟答應了。
展廳有三個,我在第一展廳逛了一圈,當看到一位皮膚白皙,顯得清爽潔凈的女畫家的身影出現在第二展廳時,我就有意過去搭訕。女畫家不算漂亮,但她似乎懂得自己的缺點在哪,她略施淡妝加以修飾。在這種藝術場合,對我這樣一個有過不止一次女人經歷的男人來說,一個女人的長相如何是其次的。何況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幾乎是大腕明星的集散地,各種明星用盡各種表情,眼神、臉蛋、身材甚至一雙長腿,隊各個角度,吆喝般向你甩賣。讓你直覺得只有這些美女經濟消費到極致才算活得實在。不過,電腦、手機的隨意鏈接中,那明眸皓齒下的明星八卦,無不誘惑著大眾的窺私欲,不知哪一天出其不意地,隱藏在他們西裝裙子背后的丑態,曝出狗血,令人作嘔,也是產能過剩后,可供玩賞的剩余。
女畫家其實非常明白別人對她的贊賞背后的含義,她有意無意保持著適度的距離,短短回答一句“謝謝!”,然后很溫和地笑一笑。
她在那幅叫《凝》的女人肖像前駐足良久。劉早剛好在她身邊經過,她待劉早差不多要走過去,準備跟其他相熟的朋友握手交談時,忽然說:“這肖像上的女人我好像認識。她跟我認識的一位女孩很像。”
“你見過我畫中的女人?”
“是很像,很像我的一位朋友,尤其畫中她挎在肩上的綠色帆布挎包。我那朋友也很喜歡挎這種老式的帆布包包。不過,說不準,畢竟畫是藝術創作,于某個人有相似不奇怪。”女畫家用不置可否的笑容,抹掉了劉早顯得不安的神情。她補充說:“這個朋友很神秘,我見過她一次后,她再沒有出現。我想要找到她時,比如現在,她又出現在我面前。”她笑著指著畫中的女子,“這畫中女人估計埋藏在你心里已經很久了。你這畫是哪一年創作的?”
劉早臉色有異,他狐疑地望著女畫家說:“是嗎?”不過,他很快就找到一個理由抽身離開,“我還要招呼一下朋友,你先慢慢欣賞,回頭我們再聊。”
女畫家轉身往第三展廳走去,似乎對剛才她撩起的話題不再感興趣了,獨自繼續欣賞其他的畫作。我一直以為劉早對俘獲一位女人的芳心是很自信的。我揣度女畫家在魚缸里游來游去,誘惑著我們這些追逐者。劉早果斷終止與女畫家的交流,將失落甩給她,等時機廣到再燃起她心中那把火。這女畫家心底的火是否會熄滅,就看誰來點燃了。
我給劉早在798策劃的畫展非常成功,劉早的愛情故事不但成為最有力的助推器,而且使《凝》成為畫壇頗受矚目的一幅新油畫,各大媒體紛紛予以了報道,有了媒體的推波助瀾,畫展還沒結束,劉早所藏的多幅畫作就已大賣。頭炮算打響了,唯獨有人出價二十萬要買走《凝》,好說歹說,劉早就是不賣。我以為他是嫌賣家出價低了。他卻說:“我沒找到丁柳前,若把這幅畫賣了,那等于我失去了丁柳,我忽然間覺得這畫是我的守護神。”
四
劉早是不是情種,我根本沒興趣。眼看二十萬泡湯,吸金無望,心里比火燒還難受。我看出劉早在設法轉移我的視線,我從其他途徑收到風,《凝》這幅油畫,有可能在某某拍賣會出現,卻總是猶抱琵琶,千呼萬喚不出現,吊足了買家的胃口。《凝》簡直就成了劉早一個符號,讓他在當代畫壇有了立足之地,攢足人氣和市場號召力。我提出要到六乾居廬拍一部關于他和《凝》的專題片,他一口拒絕,而且不知把《凝》藏到六乾居廬哪個角落了。
我不想在北京待下去了,霧霾實在嚴重,每天總感到喉嚨發癢,我下定決心,搭乘高鐵回廣州。這個包曼,我說她是一條美女蛇,給她纏住了就沒法脫身。她不僅跟著我回了廣州,還冷不丁在我不留神時,抖出些很吊我胃口的線索。她偷偷跟我說:“老葛似乎知道劉早一些過去的事情,好像不像他說的那么浪漫,你不是想了解《凝》畫中的女子是誰嗎?說不定老葛手中有你知道的東西,他答應到時拿給我看。”
這天,劉早、包曼、老葛、陳超和我,圍在一起玩殺人游戲。
包曼稍稍動了一下,她面前幾個人都裝得很老練,不動聲色,老葛打牌時,上身不自覺往前傾。這時他可能感到有點累了,稍稍挺了一下腰桿。包曼像條蛇一樣,但仍盡量蜷縮,她打出了一張牌:黑桃K。
我一直覺得包曼這個女人天生的第六感比其他女人強,除了能迅速嗅出哪一個男人,即將與她石榴裙簽約外,且能瞬間感知危險的來襲,更換妝容的速度,不比一條變色龍慢半拍。她現在好像對老葛有意思了,但我心里比誰都清楚,她是欲擒故縱,讓我上鉤。
有一次我與老葛到包曼珠江新城3X酒吧喝酒,老葛借著一點酒意,不時向包曼所在的位置溜過去,包曼后面不長眼睛,恐咱都能感到她那頭披肩的長發,都快成一把燃燒的火焰了。包曼穿著一雙限天高,慵懶地走過來,跟我們聊上兩句,又蓮步輕搖地走開。老葛低頭打火點煙,眼尾就差沒長鉤,將這條游來游去的魚兒約上來。包曼走開時,有意無意將高跟鞋磕得像小錘,將一縷似不經意投到自己身上的眼尾余光,饑渴地殘留在她橐橐足音下。
這時牌局上,包曼的高跟鞋不知什么時候從腳踝亡滑了下來,半吊在腳指頭上。老葛上身動了一下,包曼似很無意,吊掛在腳指頭上的高跟鞋輕輕晃了晃,幾乎不易察覺。其他幾個人盯著手中的牌,盡量表現出一種鎮靜,掩藏著內心的意圖。或許包曼離老葛最近,晃了一下的高跟鞋,是那么無心地碰了一下老葛。
牌局產生了微妙變化。老葛偷偷充當了包曼的保護者,且誘惑我,而劉早似乎等候著與我的一筆交易,鬼使神差地與我站隊,最后將陳超斃掉出局。不過牌局上帶有叛徒嫌疑的老葛,能控制一場牌局的走向和命運,但對自己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卻茫然無知,這命運真是誰說得清楚呢?
牌局上的變化讓我始料不及,而包曼突然爆料,無疑辟出了一條岔道。
包曼問我拿了一支煙,吐了幾個煙圈,很詭異地笑笑說:“你是不是老在琢磨,我跟老葛是不是有過一腿,給你戴了綠帽。”
我拿起茶幾上的中華,點了一根,往沙發一靠:“誰稀罕你們的破事。”
包曼不惱:“是嗎?我不是仿哪杯茶,不像丁柳,像一股煙,飄呀飄,還有一絲好聞的白蘭花香,如果我現在能帶給你有可能與丁柳前世今生有關的線索,”她頓了頓,看一下我,又說,“姑目稱為線索吧。”
包曼一劍封喉,我馬上來神,屏息凝神想探個究竟。
包曼卻不再說下去,站起來:“走,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你帶我去哪?”
“墳墓?”
“對呀,就是一個墓。”
“我操,你帶我到那些地方干嗎?”
“不去是嗎?我就知道你的德行,整天窩在家瞎想瞎編,難怪讀者不喜歡你的東西。什么叫現場,什么叫田野調查?這個不知來歷的女人,你想窩在這里,抽幾根煙就搞定,那你自搞好了。”
“什么自搞?”
“就是用手握住自己的把,搞唄。”
我忍不住笑了:“你這個陰性動物,究竟搞什么鬼?”
包曼說:“你不是一直想多了解些劉早和丁柳的故事嗎?”
“是,沒錯。”
“你有沒想過那姓劉的抖給你聽的都是些大路貨。”
“不過這跟丁柳有什么關系呢?”
“所以嘛。”嘩啦一下,她從那個LV包里拿出一件東西。
“這是什么?”我說。包曼從LV包里拿出的這個東西真夠寒磣的,一個上個世紀80年代滿大街都是的軍用帆布挎包,真虧包曼當寶一樣,放進她的LV包里。但包曼從挎包里拿出的一沓材料,我還真奉若至寶。其中有一段文字:
丁石,1942年5月16日生。1956年考進北大物理系。在北大物理系就學期間,學習成績優異。準備公派留學蘇聯,但政審時,有人揭發他隱瞞父親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少將軍銜等歷史問題。由于丁石同學的家庭出身存在較多的歷史問題,他最終在北大物理系肄業。
在這份丁石的檔案材料里,曾提到學校黨委關于丁石父親歷史問題的調查報告。而這份報告在包曼提供的這份檔案中并沒有找到,且這份檔案材料頗多缺失,并不完整。
但這已經足夠包曼得意的。她望著我,“作家,虧你還是作家。這叫檔案,第一手的材料呢!”
我眼前一亮。
包曼見我興趣上來了,更得意地說:“這丁石就是丁柳的父親。老葛跟我說,最好能找到當時丁石案的當事人。其中他已經接觸過一個在六乾居廬給丁石家煮飯的邢師傅,他提供了一些線索,說丁石是被人告發的,至于為什么告發他,這人是誰,現在還沒有新的線索。”
我陷入了新的迷茫,丁石是丁柳的父親,丁石是給誰告發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情,沒逃得過包曼的眼睛。
她說:“我給你看這些材料,是提醒你,宅在家里是沒什么用的。最關鍵是這些材料,你為什么不問我從哪里得來的。”
“是,”我立即想起什么忙追問,“你從哪里搞到這些東西?”
包曼說:“我在珠江新城的3X酒吧,來的都是些衣冠楚楚的家伙,但這年頭說不定就是衣冠禽獸。不說這個,有位客人突然有天問我有沒要辦法弄到蛇酒,我原想回絕,但這客人億萬身家,我破了例,經老葛介紹,找到邢師傅。他家里有好幾瓶蛇酒。這是收獲之一,更意外的收獲……”
包曼不說下去了,欲知后事如何,請跟我來。包曼說的這番話,我將信將疑。
五
我和包曼出發到開平百足山。途中不時見到碉樓的身影,是上世紀漂洋過海的華僑,捐資回家鄉建起來的。我們住在一座叫泰安樓的碉樓里,這碉樓是一位姓關的華僑留下的。潭江貫穿而過,沿江兩岸騎樓林立。這碉樓丟空多年,估計這姓關的主人將來都不會回到這里落葉歸根,而他們和后代都基本在海外謀生。整座村子除了一兩戶有老人和孩子留守外,幾乎十室九空。
天人黑包曼就害怕了,死往我懷里鉆。有一個秘密我從沒有與任何人透露過,我第一次在六乾居廬看到那幅《凝》后,《凝》中的女人竟然在夢中出現了。萬籟俱靜,夢里忽然聽到有女人在哭,我坐起來,卻聽不到什么聲音。我重新睡下,那女人的哭聲又傳來,是悲泣。我忍不住,起來透過碉樓狹小、窄長的窗戶眺望,除了四野的蟲鳴,并沒有其他聲響。我實在困了,合上眼蒙頭大睡。夢中碉樓飄進一股風,一道粉紅色的光泄了進來,吻了我一下,我想抓住那東光,但光很柔軟。它飄起來,又舔了我一下,我好像咬住了一個人的嘴唇。對于這個夢,我沒敢多想。
我和包曼爬到蜈蚣嶺的半山腰,就下起雨來,伴隨著閃電和雷鳴。包曼說:“不用往前走了,這雨下起來沒完。我們先找一個地方躲一下雨。”
我有點生氣了,早不上山,遲不上山,卻挑這么個天氣帶我上山,我沒好氣地對包曼說:“你就愛瞎鼓搗,回去。”
包曼說:“你先別慪氣嘛,你跟我來,準沒錯。”
雨下得越來越大,我沒轍,只好跟著包曼走向山路的另一條岔道。這條路真不好走,沒走多遠,路就沒了。我氣得冒煙,包曼卻拉著我,用棍子撥弄草叢。
我說:“先別忙著打草驚蛇,下著雨,蛇都躲到洞里,我們卻連躲的地方都沒有。”
在雜草叢生和樹林間,穿過一條勉強叫作林間小道的山間小徑。包曼帶著我到了一座村落。這里清一色青磚瓦頂的老宅,井然有序,老宅蓋得非常結實,雖歷經百年,卻沒有傾圮的跡象,不過整座村落空無一人,我們在寂靜的巷子里穿行。
包曼帶我走到一間叫指月廬的老宅前停下,門沒有鎖,門上的鐵栓銹跡斑斑。我和包曼推門進去,吱呀一聲,雨聲中鐵門發出了異樣的聲響。這間老宅周圍比較開闊,距這不遠就是稻田,遠處散落著幾座碉樓。
屋子比較昏暗,我慢慢適宜了屋子里的光線,發現里頭堆滿了柴草。我一時間不敢靠近那堆柴草和雜物,怕有蛇躲在里頭。
包曼點燃了一盞煤油燈,就著光線,包曼詭秘地向我笑了笑,說:“我帶你到這來,你覺得是個謎,我就再給你一個謎。”
“你怎么整天跟我兜圈子呢?”
“我學你們作家的手法,鋪墊鋪墊,好,不兜圈了,我告訴你第一個謎。邢師傅跟老葛透露,劉早曾經來過這個村子。”
“劉早?”
包曼很有意味地點了點頭,又看了我一眼說:“怎么,有興趣嗎?”
“劉早難道認識邢師傅,他什么時候來過?”
包曼說:“另一個秘密藏在山上。”
雨終于停了。
我按捺不住好奇說:“走,上山去。”
“山上路滑。”包曼說。
我一拍胸脯說:“有我在,沒意外。”
我攙扶著包曼,一腳泥一腳水地重新登上蜈蚣嶺,并提醒包曼,蛇這時候會出來活動,大家都要小心。我用棍子敲打著草叢,她做向導,我們走近了一座墳冢。
墓碑前放著一束馬蹄蓮,風雨過后,馬蹄蓮花辦有些掉落在泥濘中。顯然有人來過。墓碑很粗糙,碑文看得出當初是草草刻上去的,經過風雨的沖刷,碑上“丁柳之墓”等幾個字依然清晰可辨,至于何入所立,墓碑上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我狐疑地望著包曼,她得意地看著我吃驚的神情。我圍繞墓碑轉了一圈,反復辨認墓碑上的字,毫無頭緒。
我們重新回到指月廬。天色沒先前那么暗了。包曼打開一個滿是灰塵的藤箱子,她讓我翻檢箱子里的東西,箱子里裝著一些舊衣物。我們發現了一些“文革”時候留下的報紙,還有一箱尚待翻檢的書籍。我們將一大捆竹子和幾把割草用的鐮刀搬開后,著手清理堆雜物后面的柴草。我和包曼互相看了一眼,都明白對方的意思,是否有蛇?
我拿起一根竹子,往柴草堆捅了幾下,柴草散落了一地。
并沒有蛇,但掀開柴草后,一幅油畫赫然在目。
我和包曼拿著煤油燈靠近這幅油畫,包曼說:“這畫里的不就是邢師傅嗎?”我聽包曼這樣說,立即仔細端詳起來,畫上的油彩褪了不少,上面還有不少霉點和塵土。包曼說的邢師傅是老農打扮,手里拿著一根煙,編織著籮筐,背景墻上掛著毛主席像,這幅畫有一種與那個時代迥異的生活氣息。我端詳這幅油畫良久,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馬上留意這幅油畫上的簽名,油畫的右下角可以清晰地看到“丁柳”的簽名。
我站起來,在堆滿雜物的屋子里走了一圈。
包曼看著我,見我一聲不吭,說:“怎么,有發現嗎?”
我沒有直接回答她的問題,只是說:“我們再翻檢一下這里的東西。剛才不是有一箱書嗎?我們怎么能放過呢?”
這箱書看不出什么特別,五卷奉的《毛澤東選集》、艾思奇的《唯物辯證法》、《馬克思選集》、《列寧選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這間堆放雜物的房子,被我們兩個不速之客倒騰一番后,更顯凌亂。
包曼提議,把東西歸類,擺放好,這才便于翻檢。我同意了。搬動一些衣物的時候,從包曼手上掉下一個包裹得很嚴實的包袱,打開表面一大捆破布包,發現是一個鐵盒,包曼說:“如果是珍珠項鏈之類的,你怎么處理?”
我說:“我們運氣還不至于好得像阿里巴巴,說一聲芝麻開門,就有大把的金銀財寶。”
鐵盒打開了,里頭裝著的并不是什么寶貝,而是一本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封皮已經破損。我隨意翻了翻,書頁邊起毛,顯然這本書的主人是經常翻看的。有一張夾在書頁里的書簽掉了下來,包曼撿起來。嚴格地說,這不是書簽,而是一張小型的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的宣傳畫報。
我翻開了那本《安娜·卡列尼娜》,書的主人在那句扉頁上引用《圣經·新約羅馬書》第十二章十九節里的話:“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上面用波浪紋,打上了重點記號。下面有一個字跡模糊,但仍能勉強辨認出所簽的名是:“丁石”。
我沉吟了良久。包曼走過來跟我一起看這幅畫,隨口說:“這種懷舊的油畫,掛我的酒吧,挺有味道的。”過多的酒精和色欲,對于藝術欣賞總是一種傷害。她的審美情趣始終只停留在一種裝飾上,何況我的心思也不在欣賞這幅畫的藝術水準上。
包曼身上的香水味,混合了雨水和塵土味,對蚊蟲的叮咬起不了保護作用,卻對我敏感的神經造成刺激。我不想再猜謎了。我對包曼說:“走吧。這地方不是你待的。”
回去時,我們特別小心,雨后蛇會出來,我和包曼都怕踩到蛇了。
六
從蜈蚣嶺回來,我就開始籌備劉早的畫展宣傳策劃推廣拍賣等事情,為這些事我直接找到拍賣行的總經理陳超。陳超在文德路廣宇軒寬敞的辦公室里接待了我。
我進去時,秘書已經做了通報,陳超裝大牌,蹺著二郎腿,打著電話。我不看他那副嘴臉。坐下,等他電話講完了,沒繞彎直接跟他說了我的意圖。
陳超點上煙,吐了口煙霧才說:“你的意思,弄些八卦,用一個流浪畫家和一個謎一樣的女人,編一個對至愛生死相隨的故事,配以‘文革的悲情,給劉早包裝,我們一起將他的畫炒熱?”
我說:“不要把我們說成跟娛樂小報的記者一樣的貨色,我們是在搞藝術。”
陳超哈哈大笑:“好,好,搞藝術,我們在被藝術搞呢!”
“不過。”我說:“我有點疑慮,劉早畫的畫,最近聽到一些傳聞,似乎不是他畫的,來路可能不正。我們有沒有必要先起一下他的底。”
陳超掠過一絲輕蔑說:“你指的是那幅叫《凝》的油畫,你當時發現那幅畫的時候,沒有看作者是誰嗎?”
我犯困地說:“我們以為發現了一幅百年前的油畫,光顧著瞎起哄,哪顧得上看什么署名。”
陳超馬上打消了我的疑慮:“你不要再查戶口似的了,這不是捉蟲進屁股嗎?若一個漂亮女人,僅剩一副骨架,你有性欲嗎?這年頭,要包裝,就要抓眼球。你管姓劉的畫是真品還是贗品,是他本人所畫還是剽竊偷來的。他手頭的畫被炒熱了,大賣了,這才是硬道理。劉早這^是有點裝,至于他是否真具備扎實的美術功底,根本不重要。我要寄托的不是他,而是你的生花妙筆,你盡管當吹鼓手,劉早與一位神秘女子的愛情故事,你繼續包裝炒作。不過,千萬不要再把劉早寫成什么當代情圣,那沒人信。你筆下的劉早,要跟我們老百姓一樣,吃喝拉撒,也有鬧心的時候。總之,是寫一個普通人,他的成功,是靠實實在在的打拼,他的畫作是經歷了一番肝腸寸斷的愛情后的結晶,這才是賣點所在。他在前臺風騷,我們在后面擂鼓,一唱一和,施展,及金魔法。兄弟,很快,我們就等著數錢吧。”
陳超說完靠在沙發上,手指輕輕敲打著扶手。
我們為劉早舉辦了一場“尋找愛情的回歸”為主題的慈善拍賣活動。我和陳超共同在幕后協助和策劃了這場慈善籌款晚宴。
陳超在籌款晚宴上致辭。這種類似慈善秀的東西,除了是另一個商業平臺外,也是一個企業樹立公眾形象的公關。我們并沒將太多注意力放在這個籌款晚宴上。陳超的致辭,使大家的興趣迅速轉移到劉早和丁柳的愛情故事上。大家對丁柳這個女孩是生是死,她現在究竟在哪里發生了興趣。輪到劉早發言時,他坦言,他所有的畫作,都是畫心中的一個女人,那是他全部的愛的寄托。他重復這個讓我耳朵起趼子的故事時,我又想起與包曼一起上蜈蚣嶺看到的那塊刻著丁柳名字的墓碑。
慈善籌款晚宴上,我們互加微信,舉著香檳,互致問候,但眉宇間卻是在攀比,比衣著,比身份,比地位。這種衣香鬢影的場合,我嗅著女^飄過的陣陣香氣,有點迷醉了。女士們為參加這個晚宴,都精心做了打扮,著力將自己打扮得珠光寶氣,更裝得像位淑女,男士不管是否原來出身土豪,也都裝得比紳士還要紳士,看上去儼然一副偽貴族的派頭。劉早修理了一下他的絡腮胡子,仍是那么一副酷勁兒,有人走過去對他的畫作恭維一番時,很自然就向他打聽《凝》這幅油畫為什么沒有拿來展出,他一概露出他含蓄的微笑,更讓他和他的畫作顯得神秘。
想在顯得很有文化的圈子里混,若不裝出一副飽讀詩書的樣子,身上底層的烙印,稍不留神就會露餡。我以畫家劉早傳記作者的身份與這些城中名人交談,這個包裝,讓我終不至于淪落為搞文學的邊緣人物。那些女士們,知道我是作家,都表現出應有的涵養和禮貌,久仰幾聲。同時,為了不顯出他們對文學的無知,順帶問一句,你在北京待過,有沒有見過獲得諾貝爾獎的莫言?他的紅……紅什么……就是張藝謀導演的那部電影。我很適時地給他們續上《紅高粱》。
“對,對,對,《紅高粱》,你看過吧。什么時候叫莫言兄給咱們簽售一本,我們買他的書不差錢。”
我哈哈大笑附和著這些女人說:“對,對。”然后領略她們的香風和很有風度的華麗轉身。
在這個慈善籌款晚宴上,劉早的《凝》,又一次進入上流人物的視野。劉早對每位追問《凝》創作動機和模特原型的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講他與丁柳的故事。丁柳不僅成了劉早摯愛的女人,而且很快成為這個有品位的階層追慕的對象。
劉早擁有充滿磁性的男中音,這是他另一個殺傷力所在,他簡短卻頗有魅力地重復著一個答案:“現在我不知丁柳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等到她回來,但我總記得她跟我說過:沿著鐵路,我可以回家。”
七
劉早一再拿他的情史炒作,卻換不來我所渴望得到的第一桶金,我耿耿于懷,就在他忙著用藝術和愛情來包裝自己時,老葛在我背后來了一刀。他人模狗樣地在情人節跑到包曼的酒吧,送她99朵玫瑰。在燭光下,包曼笑得花枝亂顫,但眼尾的余光卻不斷輻射過來。我像個老僧,心里明了這種女人可以與她上無數次床,但用一紙婚書扯一塊生火煮飯,是必須“戒、定、慧”,放棄這杯水,而去找真正那杯茶的。不過,女人想搞定男人,總有她的辦法。
包曼有一天神秘兮兮地跟我透露,老葛又給他爆料了。丁柳是非正常死亡。我原賭氣想不再與劉早合作,就讓他和那幅《凝》朽爛算了。我忽然覺得若包曼真查出點什么,不妨借此敲劉早一筆。包曼告訴我,老葛最近老覺得有人跟蹤他,他家里安裝了攝像頭,幾次看到劉早在他家附近出現。所以,她就色誘老葛。她說:“放心,沒給你戴綠帽,我賣笑不賣身,想在他身上多挖點料,不過每次追問他,他都擠牙膏似的,老說別再逼了,實在沒什么可挖的了。”
我感到接下來所面臨的雖然很大程度上是與死人對話,但死^說不定是通往秘密的捷徑。這次我沒有帶上包曼,而是獨自一人到指月廬搜尋有用的線索。忽然身后出現了一個人,嚇了我一跳。這人顯然不怎么喜歡我這個不速之客,他搖了搖那道生銹的鐵鎖說:“我這沒上鎖,但也不是隨便讓人進來的。”
我猜他就是包曼說的邢師傅,他沒有下逐客令,顯然留了余地。
邢師傅說:“你和那女人來過,招呼不打就把我這搞得亂七八糟,別以為這里是沒有主人的。”
看得出他是在試探,他有意想與我交流。我先跟他道了個歉,就說:“你是邢師傅吧,這房子是你在住嗎?”
“是的,我姓邢,這不是我的房子。”
“那指月廬的主人,你認識嗎?”
“怎么不認識,這是以前接濟過我的恩人丁石的老家,這里的東西是當年丁石讓女兒和一個陌生男人,從廣州六乾居廬連夜搬來的。”
我趕緊追問:“丁石究竟讓你藏些什么東西在這里?”
“都是他家里的字畫。”
“很多嗎?”
“很多。”
一條重要線索出現了,我馬上順藤摸瓜讓邢師傅講述更多情況,就說:“當時與丁石女兒一起回來的人你認識嗎,他們為什么要連夜趕回這里?”
“那男人我也不大清楚他的底細。”邢師傅說,“那時正值1966年,六乾居廬所在的碉廬街,開始傳聞有人被抄家了,而目街上不時傳來游街示眾的敲鑼聲。丁石似乎感到大事不妙,就讓女兒把藏在六乾居廬的字畫轉移到這里。我猜想丁石這么做,是想著祖居周邊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解放前海外華僑寄錢回來蓋的,房子主人大多在美國、加拿大謀生,解放后就沒回來過。在村里長大的,也大多遷到廣州和其他地方了。指月廬和村里的那些舊宅,很多年前就沒有人住了,所以,丁石就來了這么一招暗度陳倉。”
“那個陌生的男人,我也是那時候見過一次。后來聽丁柳說起,是她在深圳寶安當知青時認識的,好像叫劉早。她一個女孩家到農村插隊,與當地農民一起勞動,耕田、插秧、收割,尤其是到收割甘蔗時,十幾根甘蔗扎成一捆,扛到肩膀上,稍不留神就會被甘蔗葉割出一道口子,最難受的是甘蔗葉上的絨毛,扎進肉里,奇癢難熬,特別是夏天的時候,越撓越癢。丁柳就學當地農民的辦法,將扎進皮肉里的絨毛用火去烤。大隊有一個叫劉早的,見丁柳累得不行,每逢割甘蔗的時候,就去幫丁柳。”
我根本沒有心思打聽丁柳和劉早怎么扯上關系的,只想盡快讓邢師傅直奔我的主題:“那現在那批畫呢?”
“唉,人算不如天算,丁石以為寶貝藏身于老家,就萬無一失。說來都是我不好,搬回來的東西被我藏在神樓上。”他指了指屋頂一座像閣樓一樣的神龕,上面灰塵滿布,蛛絲縱橫,非常破敗。邢師傅繼續說:“我還事先堆好了柴草作為掩護。那時候我聽到外面抄家抄得很厲害,之所以冒險幫丁石,也是為了報答他。說來奇怪,雖然藏好那些東西后,我一直沒敢再去指月廬看看動靜,但有一天,我見到一個陌生人出現在我們這個沒多少人住的村子,待我想看清是誰時,那人又不見了。后來我壯著膽子偷偷溜進指月廬查看,沒想到我幫丁石藏在指月廬神樓里的東西,尤其是那些畫,全都不翼而飛了,就剩下一幅畫擱在柴草堆下面。”
“你指的就是覆蓋在柴草堆里的那幅畫嗎,畫的是你嗎,誰畫的?”
“是丁柳給我畫的。我對她說,你會畫畫,能不能幫我畫一張,等我死了之后,也讓人家知道我長什么樣。說來丁柳真是一個很乖的孩子。‘文革后,我曾去六乾居廬找過丁石,但人去樓空。聽碉廬街的街坊說,丁石給人告發私藏大量封資修的東西,被斗得半死,關進了牢里,他老婆跳了樓。”
邢師傅忽然靠近我很神秘地說:“那個偷偷溜進我們村,差點讓我發現的陌生男人,我懷疑就是劉早。”他再看了一下左右說,“有人說丁柳其實是被人害的,是有人從她背后將她推到鐵軌上的。你說這兇手,會不會是那個劉早。我聽碉廬街的人說,丁石的黑材料,就是這個劉早給送上去的。”
我不置可否地說:“或許,這不過是捕風捉影。”
我提出想在指月廬住幾天,邢師傅顯得很不自在,狐疑地盯著我說:“這山上怪異的事情很多,你住在這里,會有危險的。”他最后非常詭異地說了一句,“晚上會有蛇的。”
他是想讓我知難而退,但拗不過我的堅持。這天晚上,我留在指月廬,翻查丁石留下的書籍和物品。半夜,地底下有隆隆的聲響傳來。我打開門,外面靜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月色,不見有什么動靜,反而是那鐵門砰砰作響,讓我感到隨時都會有人在背后偷襲。
我借著昏暗的燈火,翻看那本《安娜·卡列尼娜》,琢磨著扉頁上那句“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丁石為什么在這句話下面畫上波浪線呢?突然,燈不停搖晃,一陣風從外面刮進來,幾乎要把煤油燈吹滅。我毛孔倒豎,給包曼發了個短信:樹動,風搖,燈幾近熄滅,似鬼至。我覺得有人跟蹤。
包曼回一句:速回,老葛出事。
我回來時得到一個消息,沒有在殺人牌局上出局的老葛,最終難以逃離命運的安排,徹底人間蒸發,他再不可能給我們提供新的線索。
在東方賓館舉辦的春季拍賣會上,陳超趕來告訴我,那幅期盼已久、一直沒再出現的《凝》,終于出現在拍品的目錄上,而且是作為重要的拍品進入前五位。我沒辦法及時聯系到劉早。他繞開了我。而且能說動他將《凝》拿出來拍賣的人,能量不小。
競價從一開始就進入白熱化。《凝》從一萬開始起拍,轉眼間就競價到十萬。我緊張得心吊嗓眼上。有人舉牌二十萬,拍賣師在臺上開始造勢:二十萬第一次,有沒有人再多叫一口。好,左排第六位先生競價三十萬。又有人舉牌,是鯤鵬公司,競價四十萬。拍賣師繼續做推手,四十萬第一次,有再叫一口的嗎?四十萬第二次,再叫一口,有嗎?好,競拍師顯得很興奮,舉手示意前方說,右邊穿紅衣服的女士競價五十萬,五十萬第一次,有比這個價更高的嗎?五十萬第二次,全場靜默。我恨不得也舉牌子,將《凝》搶到手。眼巴巴看著《凝》的銀碼直線攀升,我知道我的借雞生蛋的機會在破滅。我咬著牙,仿佛看到劉早數錢時,狂笑不已的樣子。
不再叫一口嗎?五十萬第二次。拍賣師掃了一下全場。忽然一位穿著一襲水藍色長裙,得體考究的女人,舉起了牌子。拍賣師異常激動,最后一排,穿藍色裙子的這位女士競價六十萬。拍賣師連續兩次叫價,都沒有人應價了。
全場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她皮膚白皙,淡定自信,尤其是一頭及腰的長發,讓她與眾不同的藝術氣質呼之欲出。這時候好像有一陣白蘭花香氣飄了過來,我驚異地發現,這個舉牌競價的女人與油畫中的女孩,樣子是那么相似。
就在拍賣師準備落槌喊第三次時,劉早突然臉色滲白地宣布,這幅油畫的拍賣,可以停止了。
他轉頭望著這個女人說,丁柳,你……
穿藍色長裙的女人站起來,望著劉早……
我和包曼坐在電影院,看電影《歸來》。我多年不看電影,破例到電影院,還是午夜場。走出電影院,好幾個觀眾都拿出手絹抹眼淚。我旁邊的包曼也不時掏出她的香巾,擦拭淚水。
包曼問我,你哭了嗎?
我說,哭了。
你為什么哭呢?
我操,我都不知道為什么要哭,你哭了嗎?
包曼說,我也哭了,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哭。
她把手伸過來,我挽住她的手,第一次將身邊這個女人的手攥得那么緊,向鐵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