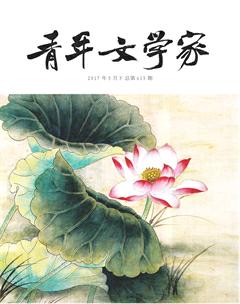詞不被古代文人雅士重視的原因探析
摘 要:詞這種文體自從產生以來,就飽受文人士大夫的爭議,對于詞的文學性定位,歷代各有異議。古代許多文人將詩與詞進行比較,大多文人不喜詞這種文體,甚至鄙夷之詞多于贊賞之詞,細究之,詞不被文人雅士重視的原因主要在于詞的起源、思想內容、藝術風格等方面。
關鍵詞:詞;不受重視;原因
作者簡介:張謙(1992.3-),男,河南永城人,本科就讀于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現沈陽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唐宋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5-0-01
在探討詞不被古代文人雅士重視的原因之前,我們需得弄清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什么是詞?比較簡潔的叫法是詩余,曲子詞,長短句等,趙曼初先生在《論詞體》一文中將詞概括為:“一種興盛于唐宋,以燕樂雜曲小唱為主要音樂載體、雜流體為主流形式、平仄規律為基本格律、婉約抒情為基本風格的歌詞形式。[1]”根據作者對詞體的定義,筆者對詞不被古代文人雅士重視的原因展開探討。詞自從產生之日起,一直都不太受文人雅士所推崇。即使是文人自己所填的詞,也不被自我認可。北宋歐陽修在編著自己的詩文集時,把自己所作的詞,從文稿中刪除。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心底喜好,樂于創作和欣賞,另一方面又表現出道貌岸然的樣子,如北宋的錢惟演即說自己只在廁所中翻閱小詞。魏泰《東軒筆錄》記載,歐陽修常對人說:“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于詩,其為人又次于文。[2]”在古人的傳統觀念中,文是最重要的,詩次之,詞是末位。然而歐陽修在評價晏殊的時候,卻把排列順序整個顛倒過來,表示對晏殊的蔑視。《四庫全書》詞曲類一就說:“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爵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3]”由此可見,詞的名分一直未定,只把詞歸于不倫不類的范疇。沒有真正的文學身份,奇技淫巧以悅婦孺,正是詞這種文體尷尬地位的體現。自從詞出現之后,雖然經過蘇東坡,李清照等人以“自是一家”來正名,但是詞的名分并沒有被當時與后世的人所接受。其中的原因也是非常復雜的。
第一,在詞的起源方面,詩歌的產生與發展有著清晰的源頭和脈絡,《詩經》是詩歌的源頭,四言、五言、七言和古體,律詩,是其基本的體式,詩有定章定法在詩歌內容與體式的不斷發展與革新中已經深入人心。從詞調的起源分析,詞的產生是因為燕樂的傳入,而燕樂是在隋唐時期,“唐玄宗時代,外國樂(胡樂)傳到中國來與中國古代的殘樂相結合,成為一種新的音樂,最初只是用音樂來配合歌辭,因為樂辭難協,后來即倚聲而制辭。這種歌辭是長短句的,是協樂有韻律的——是詞的起源。[4]”這也就是說燕樂是融合了傳統清商音樂,民間音樂,少數民族音樂,外國音樂等多種音樂成分的新樂種,當然這種音樂不是單純的音樂形式,而常常是配上歌詞,與舞蹈一起出現在宴會之上,《舊唐書·音樂志》記載:“自開元以來,歌者多用胡夷里巷之曲。[5]”不難看出,燕樂并不是產生于中國本土的樂種,而是有很大成分的外族音樂。古代中國有著很強烈的民族歧視,“自古皆賤夷狄而貴中華”,所以詞的音樂格律與土生土長的詩韻律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所以古代文人士大夫對根據燕樂填寫的詞也十分鄙夷。
第二,在思想內容方面,因為詞的產生源于燕樂,而燕樂大多是在歌宴酒席等場合由歌女妓女來演唱。詩歌自產生之日起,詞語多是典正文雅之詞,這與儒家的正統思想相符合,而詞因為特定原因,在特定的環境中產生,故而字詞多是與歌舞宴會,青樓紅館有關,其思想內容也多是飲酒作樂,擁娼狎妓之事。即使不是與青樓歌舞有關,也大多都是抒發個人的喜憂悲歡,這與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宗旨也是不相符的。文人在創作詩文的時候,便以是否載道來評判作品的優劣,很顯然,詞這種文體并沒有載天下之道,所以也不被歷代文人所重視。
第三,在藝術風格方面,詞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揚聲于雕欄玉砌之間,寓形于風花雪月之中,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就說:“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懺之玉指,拍案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6]”在唐代,無論是文人寫的詞,或者是民間詞,幾乎都表現出“媚”的特點,這種特征也影響著以后文人士大夫的詞創作,《花間集》更是為后代文人詞提供了借鑒和營養,所以宋一代,“士大夫所作之詞,亦尚婉媚。[7]”至于詩歌,在《尚書·堯典》中就有“詩言志”的說法,孔子更是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8]”所以詩歌的正統地位早已經深入文人士大夫之心,對于抒發柔情蜜意的詞,那些接受正統詩教的文人,自然是不屑一顧。明人李東琪就提出“詩莊詞媚”的說法,這正是對詩與詞不同地位的深刻體現。
通過以上幾點的分析,我們大體可以得知詞不受文人雅士重視的原因,即使經過近千年的發展,到了清代詞這種文體依然被認為樂府之馀音,風人之末派。
參考文獻:
[1]趙曼初,論詞體,《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0年9月第3期.
[2]張惠民《宋代詞學資料匯編》 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版第97頁.
[3]柳燕《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 版第224頁.
[4]胡云翼《宋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89版第6頁.
[5]郭杰 魏強主編 《文學大教室 中國·宋代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2版第95頁.
[6]劉軍政《中國古代詞學批評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版 第118頁.
[7](宋)王灼《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碧雞漫志校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20頁.
[8]劉蘭英等編著 《中國古代文學詞典 第四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