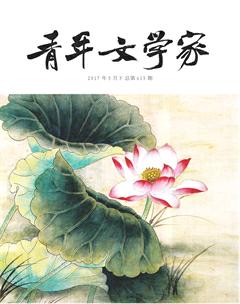《最藍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悲劇命運分析
摘 要:托尼·莫里森在小說《最藍的眼睛》中塑造了數個個性迥異的女性角色,她們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也有著對自己身份不同的態度。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女主角佩科拉的悲劇命運。本文將從家庭影響、內化的種族主義和占據主導地位的白人強勢文化等方面來分析佩科拉的悲劇命運。
關鍵詞:托尼·莫里森;小說《最藍的眼睛》;家庭影響;內化的種族主義;白人強勢文化
作者簡介:侯璐(1993.4-),山西忻州人,陜西師范大學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5-0-02
一、引言
美國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性作家。她的處女作《最藍的眼睛》發表于1970年,講述了1941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黑人女孩佩科拉為追求一雙藍眼睛而經歷的悲慘遭遇。十一歲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深深憎惡著自己黑人的身份,渴望擁有藍色的眼睛。她認為這是擺脫偏見、獲得快樂和幸福的唯一途徑。這樣的想法深植于她的心中。然而不幸的是,隨著她的價值觀的扭曲和異化,她在自己擁有了藍眼睛的幻想中精神失常,走向了毀滅。托尼·莫里森通過這本小說展示了她對黑人悲慘生活的同情、對白人文化侵蝕下逐漸消亡黑人文化的擔憂以及對黑人身份認知困難的反思。
小說讓我們看到了在白人強勢文化影響下深受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壓迫的黑人女性的悲慘命運。我們將從三個方面來說明造成佩科拉悲劇命運的因素,即她家庭的影響力,內化的種族主義和主導的白人強勢文化。
二、家庭的影響:悲劇命運的基礎因素
家庭是人認識世界、形成價值觀的基礎,而父母在塑造人個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小說中佩科拉的父母總是相互爭吵。而由于對自身身份的不認同和自卑,佩科拉總是把她父母間的爭吵歸因于她自己的丑陋。“If she looked different,beautiful, maybe Cholly would be different, and Mrs. Breedlove too.”[1](莫里森,1970)。由此看出,佩科拉十分敏感、自卑,自疑。因此她一直祈禱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周圍的人就會喜歡她、愛她,她可以像秀蘭鄧波兒一樣美麗,并過上幸福的生活。造成佩科拉這樣思想的首要因素就是家庭。
母親保琳由于畸形和黑色,從小就一直面對偏見,她一直過著孤僻的生活。她認為佩科拉非常丑陋,對佩科拉沒有什么愛,她卻把她所有的愛都傾注在一個人身上——她所服務的家庭中的白人女孩。盡管她是白人家庭的仆人,她也很樂意為白人做家務。她母親對白人女孩的偏愛和關心對佩科拉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她越來越執著地想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那樣她就可以得到母親的愛與關心。而父親喬利是一個病態的人,他很小的時候,他就被父母遺棄了,他很少感受到關心和愛。他在童年時期的經歷對他長大后的行為有巨大的影響。他通常是醉醺醺的,甚至還會燃燒自己的房子。他不知道如何照顧他的孩子,并表現出愛,因為他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因此佩科拉從來沒有從父親這里感受到過關心和愛,而是無盡的痛苦和巨大的傷害。
與佩科拉不同,她的朋友弗里達有著不同的生活,她的家庭幸福和諧,她從家庭中感受到了關心和愛。當弗里達被亨利先生騷擾時,她的父母竭盡全力懲罰他,以保護自己的女兒。而保琳和喬利卻對女兒施加消極情緒,對佩科拉造成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料到佩科拉對黑色不可能有積極的態度。所以她否認自己的黑人身份,并瘋狂地執著于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想要以此來改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不幸的是最后走向了毀滅,她的父母有義務對女兒可憐的命運負責。
三、內化的種族主義:悲劇命運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佩科拉生活的環境對她的悲慘命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周圍的人都輕視她,熱衷于開她的玩笑。小說中幾乎所有的黑人都不想被視為黑人。有時黑人的仇恨不是來自白人,它反而來自黑人本身。他們介意被視為黑人,他們拒絕與黑色有關的一切。在小說中,內化的種族主義在黑人中很普遍。皮膚意識日益顯著,有些淺膚色的黑人甚至會鄙視膚色深的黑人。這反映了黑人內心的自我否定、自我憎惡以及根植于心中的“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價值觀。
書中佩科拉的同學莫琳假裝是佩科拉的朋友,但她只打算挑釁佩科拉,表明她是一個優于佩科拉的淺膚色的女孩。在社區,佩科拉因為丑陋經常被同學欺負,老師也很少關注佩科拉。這些言論和行為對佩科拉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她的丑陋被周圍的人加強了,她被排除在外,被迫從她應該高興生活的環境中被除去。因此,她渴望擁有藍色眼睛的愿望越來越強。她認為如果她擁有藍眼睛,她會變得美麗,并被其他人接受。換句話說,她認為她的生活會因藍眼睛而完全不同。
佩科拉的家庭使得她自卑、自棄,是她追求藍色眼睛的起源;而周圍環境及他們內化的種族主義則使這一想法成為執念,占據了大腦,成為生活的唯一目標。內化的種族主義使得黑人在心底接受了“白人至上”的思想和價值觀,而這一觀念也支配了他們的生活,使他們潛移默化地把自己異化,喪失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用白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
四、主導的白人強勢文化:悲劇命運的決定因素
導致佩科拉悲劇的決定性因素是占主導地位的白人強勢文化。“文化的內容豐富,涵蓋宗教觀念、哲學思想、文學藝術、社會心理、價值取向、風俗習慣等。 文化與種族一樣,從本質上說并無優劣貴賤之分,不過,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會背景下相遇時卻可因各自的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差異而形成強勢和弱勢的區別。 強勢文化往往強化現存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并憑借其有利地位,對弱勢文化發起一輪輪沖擊。強勢文化有更多機會向人們證明其合法性,灌輸自己做統治者的天經地義。久而久之,這不平等的現象便會被接受為生活的自然秩序”[4]。美國是一個主要由白人組成的社會,白人堅持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占據了領導和控制的地位。鑒于歷史問題,黑人被主流文化極大地邊緣化[3]。如小說中當佩科拉去商店買糖果時,白人店主不會看這個黑人小女孩,因為他完全忽視她;當店主把糖果交給佩科拉時,他也避免觸摸她的手。佩科拉從這種事中感受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侮辱。
保琳認為白色是真正的美,她只是白人家庭的仆人,但她覺得這份工作很有趣,這是一個天賜,因為她的工作被白人稱贊。因此,在主導的白人強勢文化領導之下,黑人感覺不如白人,他們盡最大努力跟隨和模仿白人在日常生活中做的事情,以擺脫悲劇。莫琳,一個混血兒,像純粹的白人女孩一樣表現自己,在她的腦海里黑色是可恥的。因此圍繞佩科拉生活的整個氛圍充滿了拒絕黑色的言論和行為[2],這也反映出在白人強勢文化影響下,黑人已漸漸丟失了他們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他們一切向白人學習,用白人的標準來衡量黑人,因此更加陷入了自我厭棄、自我否定和自我異化的深淵中。
藍色的眼睛代表白色文化。佩科拉夢想成為一個有藍眼睛的白人女孩,融入白人世界,她從不認同自己的價值和美感。可以看出文化對人意識心靈的侵蝕的可怕性和殘害性,它使人從內心深處否定自己的文化,否定自我。莫里森通過佩科拉扭曲的心靈告訴讀者,以白人強勢文化和生活方式作為價值取向,會使黑人失去自我,陷入身份認知的混亂中。如果放棄黑人自己的文化,陷入白人主導文化的沖擊中,注定會走向悲劇的毀滅。
五、結語
《最藍的眼睛》是一部令人震撼和深思的作品。通過對以女主角佩科拉為代表的黑人女性悲劇命運的探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畸形的家庭背景、根植于心中的內化的種族主義和主導的白人強勢文化是造成她們悲劇命運的主要因素。作者通過這本書表達了黑人只有保留、堅持和弘揚自己的文化,才能抵御白人強勢文化的沖擊和內化,追尋屬于自己的生活和價值觀。
參考文獻:
[1]Morrison T. The Bluest Eye[M].Penguin: New York,1970.
[2]陳晨.評托尼莫里森《最藍的眼睛》中的黑人身份認同[J].異域文苑,2010,(3).
[3]駱洪.文化身份尋蹤:美國黑人作家筆下的話語[J].學術探索,2004,(12).
[4]朱波.白人文化對黑人心靈的沖擊-評托尼·莫里森的小說《最藍的眼睛》[J].濰坊學院學報,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