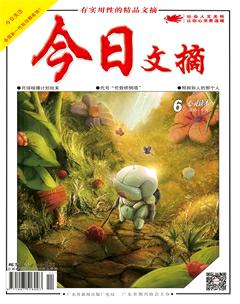多鼓勵別人與多鼓勵自己
朱仲南
我們的教育是很奇怪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不講究鼓勵別人和鼓勵自己,他們信奉棍棒出孝子,責罵出賢孫,不打不成材,不教訓則不明事理,不灌輸、不予以填鴨式的教育則記不牢東西,不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則不能說去污垢,等等。千千萬萬的人都信服,都認為這是世間最好的教育方式方法,而別的教法,則是虛偽的,是假惺惺的。
狂轟濫炸了千年、萬年,把女的搞成一個個裹腳女人,走路像走鋼絲那樣:把男的搞成盤頭長發,一個個賊頭賊腦,一個個不知國是,不明家事,不理俗事,只想一心苦讀圣賢書,有朝一日中狀元。所以,國人肩上的擔子太重了,不懂笑,沒閑工夫笑。對任何人都是充滿了一種期待、一種渴望、一種寄托,他們對任何人都保持一種審視、一種警惕、一種不滿,快馬加鞭,百上加斤,加油!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去鼓勵人,去贊頌別人,去感謝別人,去想一想別人。想想自己都沒有時間,想想自己的事都認為浪費青春、光陰,每個人養成習慣,兩只眼充滿各種渴望的光、獲取的光、占有的光,那五官一湊起來,雖然各有其特點,但那股神態,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外國人覺得中國人都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其實,這個一模一樣指的是他們的“神合”,他們的表情高度的一致。這是共性的結晶。
筆者從小就喜歡聽鼓勵、表揚、肯定,從小就不愛聽指責、埋怨、否定、怪話。那時候有“學生手冊”,往往有一欄是班主任的意見或學校意見,看到班主任的表揚、肯定,會心花怒放,吃飯加多一碗還不飽。看到班主任不客氣的批評、指責,心思全無,食之無味,一夜無眠。這些心態,許多人都是有過的。長大后聽那些什么“多提寶貴意見”“哎呀,請多批評,這是對我的愛”,咱們心里就知道遇上了奇人、怪人、假面人。有誰喜歡批評的呢?有誰會把整天罵他、怨他的人當作知心人呢?虛偽人生,虛假的話張嘴就出,都認為假、大、空是報刊、電臺、電視的事,其實呀,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人人心知肚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歡的事、不接受的事,你就不要用在別人身上,不能強加于人,這是我們都懂的理兒。所以,筆者在高中留校當教工時,在大學當助教時,在廣東省教育學會工作時,從不責怪學生,從不埋怨學生,從不無理批評學生,當一個“沒有威嚴”的教師、一個教育工作者,表面顯得平庸,但心里樂融融。不少學生私下和筆者關系特別好,特別有感情,不同屆的學生、不同班的學生,都樂意和筆者交心,談理想,談學問。這種友誼,保持至今,令不少教育界工作的人嘖嘖稱奇。
奇怪嗎?不奇怪。筆者任何手段都沒有,沒有提干指標,沒有吃吃喝喝,沒有拉幫結派,就憑著對得起教師的稱號,對得起良知,要拉人一把,推人一把,點燃別人的希望,多激勵、多鼓舞,形成正能量,僅此而已。
我們多么希望每個人都醒悟過來,不要以為正能量是校長的事,是市長、省長的事,它同樣是你、我、他的事情,是不可推掉的職責,不應放棄擔當。有的幼兒園老師,孩子一吵、一鬧就大發脾氣,就一腳踢過去,就高聲責罵;有的家長,回家一脫下鞋,就開始罵交通,罵孩子,罵肉菜小販,一直罵到睡覺前還在罵:當領導的罵部下,指責部下,把部下當家丁,當家奴,習慣被罵的,一臉諂媚,不習慣的,回到家里吃安眠藥都睡不了;上街堵車罵加插的人,罵交警,交警聽慣罵了,放一個“雪糕筒”在你面前,不予理睬,等你停止罵了才拿開。一有什么事,人們習慣以追究責任開始,互罵結束,到處如此,尚能靜否?
其實我們都很討厭罵人、指責人、數落人、譏諷人的人。在民政部門工作的朋友告訴筆者,離婚率高低各民族不同,但情緒暴躁,相互不謙讓,互罵、互責、互怨的夫妻,離婚比例是最高的。我們為何不去鼓勵別人昵?我們為何不能鼓勵自己呢?誰都不可能收走你的權利,誰都不可以扭轉你的理念,你為什么不堅持呢?
笑一笑,十年少,人們都懂這句話,但未必都會去實踐。鼓勵別人,不可能有“勝造七級浮屠”那么大的功德,但起碼有造福于人、助人一臂之力的德行啊。要堅定信念,去實施。鼓勵自己,有何不可?天天怪自己,或天天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這都不妥。最好的辦法是鼓勵自己日行善,日作功德,日發一慈善之音,鼓勵自己做下去,即便沒有做事之機,沒有發音之機,也要鼓勵自己持有善意、善念。這樣做人做事,誰可干預,誰可剝奪?沒有,只是悟性不夠而已,擔當精神不足而已。仍需鼓勵。
責人、怨言、非議、排斥如刀如槍,不能說一點好處都沒有,但建議慎用。
鼓勵別人,激勵別人,鼓勵自己,如拉響了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那么悅耳、動聽,這才是人生的樂章。而斥來責去,罵成一團,那是屠場,鬼哭狼嚎,令人畏懼,成何體統?
(馮米倫薦自《品格是你最硬的背景》)
責編: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