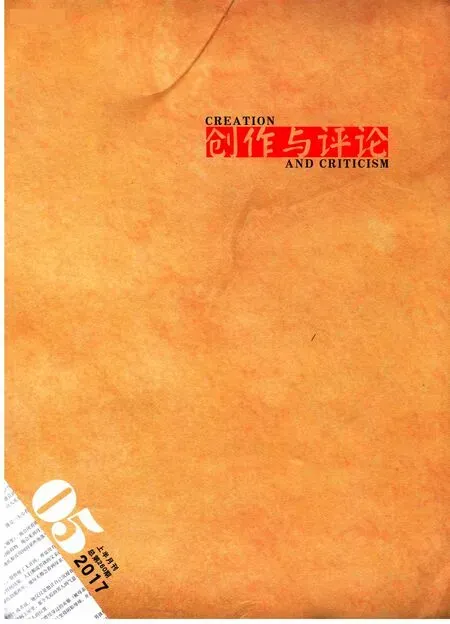布朗運動(短篇小說)
○ 張新科
布朗運動(短篇小說)
○ 張新科


張新科
1966年9月出生,河南上蔡人,留德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徐州工程學院校長,徐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在《當代》《十月》《鐘山》《中國作家》《長江文藝》等文學期刊發表小說220 余萬字。 代表作有《遠東來信》《蒼茫大地》《鰈魚計劃》《天長夜短》《信人》等。 作品多次被《小說月報》《長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選載。
2014 年度《海外文摘》長篇小說獎、第五屆江蘇紫金山文學獎和2017 年江蘇十佳好書得主。《遠東來信》《鰈魚計劃》和《蒼茫大地》被改編成了電視劇和廣播劇。
今年八月,“洋火”死了。
我趕回老家參加了他的追悼會,悼詞念了十幾分鐘,我一句都沒入耳,沒有人比我更熟悉躺在面前的“洋火”。我參加過很多追悼會,看到合眼躺在殯儀館大廳中央之人時,知道此人再也不能站起來,用老家話講,一陣喧囂過后就要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睡大頭覺”。但對“洋火”,我卻沒有一點這種感覺。他這么安安靜靜地躺著,我倒認為他沒死,而是在裝死。
說來話長。
一
認識“洋火”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家住在縣高中家屬院內,有一天,當校長的父親拿回來幾份新進教師的履歷表。
“陳東方、丁學軍、母大海……”我看著表格大聲讀了起來。那年我七歲,剛上小學,酷愛認字。
父親哈哈笑出聲來,說:“你是第三個給人家改姓的人了,‘毋’字讀‘wu’不讀‘母’!”
第一次見到毋大海本人,是在我家里,他來向父親報到。一見其人,我就嚇了一跳。一米八五的個子,長得像一頭犟牛,走起路來屁股上的兩坨肉左右晃蕩,屁股下的藤條椅子吱吱嘎嘎叫個不停。那時候還沒有增肥劑和飼料添加劑,我老家農民娶媳婦要養豬,膘最厚的也就一百六七十斤,我估計他的一身膘肥豬都比不上。嚇著我的不光是毋大海的一身肥膘,還有他的右手。毋大海左手手背長滿密密的黑毛,右手上卻寸毛不生,皮膚紅彤彤、緊繃繃、光溜溜地瘆人。看到他的手,我立刻想起了寓言“火中取栗”中被火燒傷的貓爪。父親問他右手咋個回事,回答說“王八蛋美國佬汽油彈燒的!”父親知曉教師靠手吃飯,接著問礙事不礙事?毋大海回答,除了冬天戴手套老出溜下來,別的屁事沒有。
毋大海走后,父親講,此人是從抗美援越前線負傷歸來的排長,算個英雄,因履歷表中寫有“愛好籃球”四個字,上級便分配來教體育課。那時候,我只聽說過抗美援朝,從來不知道還有抗美援越,就問父親,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還有《英雄兒女》中的王成王芳都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咋沒聽說過抗美援越的英雄,一句話倒把父親問住了,支吾了半天竟沒有了下文。
毋大海第一次亮相籃球場,是他來校三天后的一個晚上,那晚縣高與消防隊舉行一場“毛蛋”比賽。那時候我老家把籃球稱作毛蛋,打籃球也叫打毛蛋。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打籃球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最時興的體育活動。乒乓球、羽毛球需要球臺、球拍、球網,而且參與人數最多四個,所以不受大眾推崇。排球偶爾也玩,但撿球比打球的時間還長,三五次之后也就興趣全無。那個年代在我們縣城從來沒人玩足球,好好的毛蛋不用手打,而是用腳踢來蕩去,不成體統。
那時籃球的風靡程度現在人無法想象,就拿兩個當時的生活現象來說吧——一是媒婆給耐看的大閨女介紹對象時,如果最后加上一句“年青貨打一手好毛蛋哩”,婚事十有八九準成;二是那時我老家放映過一部電影《朝陽溝》,男主角栓保身背籃球的形象深入人心,縣城的年青貨逛街,領頭者一定身背裝籃球的布兜,不管晴天雨天滿街浪。籃球那時奇貴,橡膠的九塊五,牛皮的分兩類,“四塊瓦”(四塊牛皮縫制而成)的十五塊九,“兩塊瓦”的十八塊六。年青貨買不起籃球,買不起籃球的他們買得起布兜,布兜里裝著的圓鼓鼓的東西貌似籃球,其實大多不是,夏天是西瓜,冬天是冬瓜,用現在流行的話說,是籃球的山寨版。
那晚,縣高與消防隊的比賽在縣城東街燈光球場進行。上半場結束時,縣高隊就輸了二十六分,圍觀的幾百名觀眾一邊倒為消防隊喝彩。縣高籃球隊員大部分是學生,偶爾也有老師上場,但都熬不過一刻鐘就氣喘吁吁,不得不換下來休息。學生籃球打得稚嫩,消防隊就不一樣了,救火沒有練球的時間多,運球過人,投籃搶板,所向披靡。
下半場,毋大海出場了。
毋大海上穿白色背心,下著白色短褲,腳蹬學校新配發的白色球鞋,宛如一條白龍閃現在球場上。上場不到十秒鐘,對方主力“消防栓”運球至半場,防守的毋大海從三米開外哧溜一個跨步迅雷般閃來,右手果斷一伸,斷走了籃球。“消防栓”見球被無端截去,懊惱異常,使出渾身蠻力,沖上來阻攔。毋大海早料及他這一手,在“消防栓”沖上來之前,一個背后傳球,籃球一個快速曲線運動,飛向了左邊鋒學生隊員王俊輝。王俊輝得球的同時,只見一道白光閃過,毋大海已飛奔至離籃板幾米處。這時的他并未聲張,而是在空中揚起了右手。毋大海一身白色,只有右手呈紅色,在燈光的照耀下,紅色不但沒有絲毫減弱,反而紅得發紫。王俊輝正在尋找合適的傳球對象,忽然瞥見籃板前不遠處人群頭頂上的一團火紅,立刻明白了一切,“唿”地一聲,籃球以最快的速度直線飛向了“火光”。見毋大海得球,消防隊兩名隊員前后夾擊,封住了他上籃的路線。毋大海并不急于突圍,只見他彎下腰來,把身體重心壓得更低,右手中拍打的籃球離地面更近,近到只有不可思議的五六公分,俟對方兩名隊員站穩后,才迅速運球,一個左躲,再一個右閃。打籃球講究人跟球,消防隊兩名隊員自然知道這一點,兩次左右閃動后,毋大海并未躲開他們,三人和球仍然粘在一起。我和場外的縣高師生都為毋大海捏了一把汗,不知道他能否突破成功。場上的毋大海重新站定,繼續低手啪啪運球,突然,他重復了上次的動作,先是左躲跨步,對方的兩名隊員跟著他向左移動,夾擊沒能被突破。接著,毋大海的頭和上身開始向右晃動,對方兩名隊員意識到毋大海又老調重彈,馬上要從右路突圍了,急忙啟動自己的腳步一齊向右滑動。這回他們錯了,毋大海頭和上身雖然向右晃動,但腳并沒有動,待對方兩人滑到右邊,面前頓現一空檔,只見他抓住這一稍縱即逝的戰機,噌!噌!噌!三大步躥到籃板之下,先是一個跳起,接著高揚右手,手腕一壓,籃球在一道紅光之后應聲入網。
整個球場爆發出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消防隊見來者不善,便對毋大海實行重點盯防。此時的毋大海有如神助,防不住,盯不死,攔不下,撞不倒。假動作、左右盤帶、胯下運球、單手上籃……全場觀眾看得眼花繚亂。記分牌上,縣高隊的得分“呼呼”地直往上飚,離全場比賽結束還有三十秒的時候,兩隊的比分是78:79,縣高隊落后一分。
最關鍵的時刻到來了。縣高隊后場發球,后衛將球傳給了王俊輝,他帶球還未跨出兩米,便被消防隊的一名隊員盯死在原地,兩人纏在一起,時間過去了八秒。中鋒蔡勁道剛一接到王俊輝好不容易傳過來的球,又被對方的防守隊員纏住了,待他將球傳至中場的時候,時間只剩下了十五秒。十五秒時間內,如果縣高隊不能得分,便會以一分之差惜敗。中場得球的毋大海十分清楚,如果自己再將球傳給伙伴傳帶,時間肯定來不及,只有靠他一己之力完成半場的傳送和上籃得分了。
經典,絕對經典的場面出現了,我老家人后來把這個場面傳得神乎其神。
毋大海得球后,消防隊三名隊員立刻包抄而來,將他密不透風地夾在中間,動彈不得。時間在一秒一秒地過去,正在場外觀眾焦急萬分的時候,毋大海做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動作,只見他把籃球狠狠地砸向了地面,籃球猶如一發出膛的炮彈,從四人的夾縫中沖天而起。后來知道,毋大海在摔球時用了一個斜摔的動作,籃球飛向了正前方的天空。正當消防隊三個隊員詫異瞭望之際,毋大海飛身突圍,奔向前方,籃球在空中一段拋物線軌跡飛行后,被凌空而起的他牢牢接于手中。對方的兩名前鋒醒悟了過來,猛虎般撲向毋大海。時間只剩下了最后五秒,這時的毋大海離籃板還有七八米,身邊有兩名壯漢夾擊,所有觀眾心里都清楚,縣高隊必敗無疑。
奇跡,奇跡再次發生。被兩名對方隊員貼身包抄的毋大海沒有帶球,也沒有傳球,而是掄起右臂,將籃球甩向遙遠的籃板,場上所有隊員都被這“荒唐”的舉動驚呆了,個個瞠目結舌地仰望籃球如流星般從空中劃過……球一出手,毋大海即向籃板狂奔。球最終砸在籃板下沿,“砰”的一聲反彈回來,落在籃板前三米處,毋大海一個旱地拔蔥,騰空而起,又一個空中走步(現在叫空中滑翔),猩紅的右手接住了籃球,順手、抬臂、壓腕三個動作一氣呵成,將球穩穩當當扣入了籃網。
毋大海雙腳一落地,終場的哨音吹響了。
縣高隊以一分優勢贏了比賽,這是縣高十年來第一次戰勝不可一世的消防隊。
回家后,我激動地對父親說:“毋叔跳得不但高,而且筆直,上身是白的,下身是白的,腳上也是白的,只有高舉到上面的右手是紅的,整個身子看起來就像一根洋火!”
我們那里當時把火柴稱作“洋火”,不經意的一句話,后來成為了毋大海的綽號。從此沒有人再叫毋大海,而是改稱“洋火”。
二
“洋火”一戰成名,英名響徹縣城。那時,如果縣城玩籃球的人不知道“洋火”,宛如當今不知道喬丹和姚明一樣。
縣高籃球隊取得輝煌戰績后,“洋火”接受了學校廣播站的采訪,提出了“生命在于運動”的響亮口號。他的口號像激蕩的春雷,激發了上千名學生參與體育運動的巨大熱潮。學校籃球場上每天球聲不息,哨音不斷。籃球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其他體育項目比如乒乓球、羽毛球還有廣播體操也同樣風生水起,學生們扔下書本,離開教室,活躍于操場上。
“洋火”成為了學校的風云人物。
半年后的一天,“洋火”帶領一幫酷愛體育的學生把我父親堵在了校長室。大聲齊呼——“生命在于運動”。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而身體也就是生命在于運動,運動必須從時間上得到保證,強烈要求把每周六節體育課翻倍變成十二節。父親是解放前的老大學生,鼻梁上架著1200度的眼鏡,對體育活動向來不熱不冷,沒有答應。憤怒的“洋火”在學生慫恿下,勒令父親三天之內作出答復。
父親不得已,第二天便開會討論“洋火”的“提案”。校務會剛開始,駐校工宣隊隊長、老工人魏銀山便提出異議,說生命在于運動不假,但把身體鍛煉強壯后干什么?父親不知道他葫蘆里賣什么藥,便問他有何建議,他說:“生命在于運動,目的在于學工”,所以,在提高體育課比重的同時,必須把每年二十天的“學工”時間再延長一倍。魏銀山的話音一落,駐校農宣隊隊長、頭裹白毛巾的苗狗圣接了話茬,“地里不出糧食,沒飯吃,運動個屁!”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學校只放十天秋收假和十天麥忙假遠遠不夠,必須提高“學農”比重,每學期再增加十天春播假和十天冬季“保墑”假。
當時的高中已經砍去了外語課,七八位英語教師分散到了后勤室和保衛室,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和歷史課的比例也降到了最低點,很多教師已經無課可上,校務會一番吵鬧后無果而終。魏銀山和苗狗圣最后做出妥協,只要不增加“洋火”的體育課,他們就不再鬧。
父親不得不再與“洋火”交鋒。
第三天下午,“洋火”帶領十幾名學生蜂擁而至。“洋火”帶領的這幫學生,大都是縣領導和公社干部的兒子,個個不愛坐冷板凳上課看書。他們人人手中拎著標槍、手榴彈、鉛球、鐵餅和啞鈴。嘩啦一下進門后,把我父親圍了個嚴嚴實實,口中呼喊著統一的口號:“生命在于運動!生命在于運動!生命在于運動!”
父親當了二十多年的校長,風里來雨里去見識過許多學生鬧事的場面,處事老道,用現在流行的一個詞講叫“老油條”,他坐在藤椅上沒動,任由一幫人圍著他呼喊三十多遍口號連眼皮都沒抬一下,這幫人喊累了,終于無趣地停下。
“大伙剛下體育課一定很渴,我來倒水。”父親微笑著說。話畢,沒等眾人反應過來,提起水瓶,就往幾個杯子里倒水。
“洋火”和學生的火氣減去了一大半。
“俺們不是來討水喝的,生命在于運動,請問校長提高不提高體育課的比重?”“洋火”打破了沉默。
“提高任何一門課程的比重不是小事,得說出個道道,否則其他老師有意見。”
“咋個說出道道?”“洋火”厲聲質問。
“咱們現在就一起探討探討你們的提案!”父親回答。
一聽要探討“生命在于運動”的正確性,有備而來的“洋火”和學生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地說了半個鐘頭才停下來。一番亂哄哄的陳述后,一個留分頭的學生仍意猶未盡,最后又加了一句。
“生命在于運動這個偉大的真理不要說對人,就是對動物也一樣,比如豬和馬,豬整天待在圈里好吃懶做,不愛運動,所以平均壽命只有二十年,而馬每天不是干活就是奔跑,平均壽命能達到三十到三十五年。”
“說得好!說得好!”“洋火”帶頭為這名學生鼓掌。
“剛才這名學生舉的例子很好,但我也有個例子,幾十年來都沒有弄明白,想請他指教指教。大家都見過烏龜吧,烏龜一年中至少六個月靜臥水底淤泥或有覆蓋物的松土中冬眠,恐怕是最不愛動的動物,但烏龜的壽命究竟有多長,目前尚無定論,一般講能活一百年,去年我從《參考消息》看到了個材料,說有的烏龜至少一千歲了。”不緊不慢地說完,父親把目光落在了留分頭學生的臉上。
留分頭的學生一時語塞。
“受烏龜長壽的啟發,看來生命不但在于運動,也在于靜止。”父親慢條斯理地說。
父親的話如同一根劃著的洋火扔進了火藥桶,辦公室里砰地一聲炸了起來,圍著父親的學生們都瞪大眼睛叫嚷不停。“洋火”和學生一通高聲指責后,始終沒有說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運動的目的在于身體強壯和長壽,大家知道民間經常用什么成語來祝賀老人健康嗎?”父親乘勝追擊。
“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一個學生回答。
“還有呢?”父親問。
“松鶴延年。”又一個學生回答。
“對!就是這個成語,鶴代表動,松代表靜,動和靜兩者缺一不可才能長壽。所以說,生命不但在于運動,同樣也在于靜止!”
父親的一席話說得“洋火”和學生面面相覷。父親要是說到這里就收場,說不定事情還有轉機,但那次“老油條”顯然是得意忘形了,接著又舉了個例子。
這個例子把父親推進了自己挖的坑里。
“再比如我剛才給大家倒的這幾杯水,剛開始時水在杯中一直晃蕩,也就是你們說的運動,但一會兒之后呢?你們現在再看看,水還晃蕩嗎?哪一杯水不是安安靜靜的?!所以說,運動是過程,靜止是運動的最終形式。”父親瞅著無言以對的一干人等,心中暗自竊喜。
屋子里沉默半分鐘后,想不到先前那個留分頭的學生說話了。
“不對,靜止的水一直在運動!布朗運動揭示了這一點。”
父親是學國文的,隔行如隔山,自然不知道什么是布朗運動。
“我們物理課上剛學過布朗運動,液體表面上一動不動,但構成液體的分子卻在不停地做無規則的運動。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物理學家在液體中放置了一些細小的花粉微粒,在顯微鏡下很容易觀察到懸浮在水中的花粉微粒受分子運動的沖擊也在不停運動。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沒有風的情形下觀察過空氣中的煙塵,煙塵會靜止嗎?不會,它們在空氣中慢慢擴散,不停運動……”
父親眨巴著一雙小眼睛,顯然是被這番理論打懵了。
“好,好,波浪運動!波浪運動!”“洋火”帶頭起哄。父親先前的優勢盡失,“洋火”和學生占據上風。
“老油條”畢竟是“老油條”,父親自然不肯輕易就范,一番思考后,計上心來,說:“運動不僅僅是體育課,有些活動也是運動。”
“什么活動?”“洋火”追問。
“學工應該也是運動吧!”父親回答。
“工人整天窩在機器旁,光動手不動腿不動腳也不動腦,不算運動!”一個學生回答。
“那學農呢?”父親又問。
“農民大部分時間不是曬太陽就是睡懶覺,只有農忙幾天才動動手,不算運動!”另一個學生回答。
父親一聲不吭地站了起來,出門叫來了隔壁的魏銀山和苗狗圣。
“老魏老苗,工人農民在工廠和田間干活,有人說他們這些體力勞動不算運動?”父親說。
“俺們搬運工人卸貨裝貨從早干到晚,天天工作服都被臭汗濕透,還不算運動?”搬運工出身的魏銀山高聲怒罵。
“農民兄弟就更苦了,不但犁地耙田,還要割麥揚場,哪一項不是重體力運動?”苗狗圣義憤填膺。
那個年頭工人和農民的話頂用,“洋火”和學生沒有一個人敢吭聲。
“既然生命在于運動,學工學農也是運動,就從學工學農開始吧!”父親說出了自己的主張。
魏銀山和苗狗圣一聽這話,頓時喜出望外:“不孬,不孬,既活動了身體,也學到了本事。”
無人敢站出來反對。至于先學工還是學農,魏銀山和苗狗圣爭吵不斷,最后父親說:“農業是經濟的命脈,先學農!你們這些喜歡運動的人都帶頭報名,簽個字!”
父親把一張白紙和一支蘸水筆擺在了桌面上。形勢轉得如此之快,“洋火”和學生們雖然很無奈,但還是一個接一個簽了名。
第二天,父親請來了縣治淮委員會主任梁三響。梁三響在我們縣城大名鼎鼎,因他娘生他時連放三個響屁,他爹便給他起名“梁三響”,此人說話向來說一不二。一個月前,梁三響來過學校,說治淮時間緊任務重,提出能否讓高中停課兩個月上河工。父親說:“三響主任,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一千多名學生正在為即將到來的機械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你難道想破壞上級的政策?!”梁三響思來想去,只得作罷。
對“洋火”和十幾名學生,梁三響就沒有那么客氣了,動員會上的他聲如洪鐘:“農業是經濟的命脈,而水利又是農業的命脈,你們不是想運動嗎,俺會讓你們在工地上運動個夠!到時候誰不好好干,誰就是蓄意破壞國家的命脈!”
河工是我們那里最苦的活兒,要把河床淤泥挑到十幾米高的河堰上,每副擔子重達一兩百斤,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外加一天三頓鹽水窩頭,葷素不沾,人人談“河工”色變。一個月時間不到,“洋火”和十幾名學生個個面黃肌瘦,不成人樣。
一天半夜,我家的房門忽然被敲得咣咣作響,進來的是蓬頭垢面的“洋火”。
“校長,救救學生吧,俺們實在受不了啦。”
“你們不是說生命在于運動嗎?這么好的機會,難得啊!”
“校長,還是您說得對,生命在于靜止啊!”
“布朗運動不也強調每個分子都得不停運動嗎?”
“再運動下去,俺們個個身體都零散了!”
父親最后說:“我想想辦法!”
“洋火”臨走時,低聲告訴父親:“校長,俺半夜回來的事千萬不要讓梁三響知道,那個人可是新社會的‘周扒皮’呀!”
第二天,父親來到工地找到了梁三響,說:“三響主任,下個月學校要舉行農業機械化知識考試,上級要來巡考,誰考試不及格,誰就是破壞農業機械化政策!”
梁三響無奈,只得放人,臨走時沖著“洋火”和十幾名學生喊:“剛來時天天給俺宣講‘波浪運動’,現在咋了,整天蔫了吧唧的,成了‘不浪運動’!”
三
“洋火”上河工回來后,人老實了許多,不再到處宣傳“生命在于運動”,也不再提增加體育課比重的事了。
三個月后,“洋火”把兩個兒子從農村接來,跟著他在縣城上學。后來我才知道,“洋火”老婆是個農村婦女,生了兩男兩女四個娃,為了使大毛二毛兩男娃將來有出息,一直催“洋火”把孩子接進縣城,嘟囔了大半年時間“洋火”才無奈同意。
大毛八歲,二毛六歲,可能是遺傳基因的關系,都比同齡娃高出半頭,長得虎頭虎腦。兩個孩子到來后,“洋火”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先是睡覺成了問題。當時學校的教師每人一間房,十平米大小,只能放下一張床、一個書桌、一張凳子和一個衣柜。床是一米二寬一米九長的單人床,“洋火”一人躺下,已經滿滿登登,陡然增加兩人,空間更加局促。頭兩個晚上,大毛和二毛各掉床一次,父子三人試睡兩晚后,終于找到了解決方案。“洋火”一人一頭,大毛和二毛一頭,但二毛不能獨自睡,必須夾在“洋火”兩支粗壯的大腿間睡。有生活經驗的人都清楚,運動量大的人屁多味臭,一個星期后,二毛噘著嘴對“洋火”說:“爹,放屁前吭一嗓,俺先下去會。”
解決了睡的問題,吃的問題接踵而來。那個年代,只有城市戶口才有糧票,當時的戶籍政策是孩子戶口隨母不隨父,“洋火”老婆是農村戶口,所以,大毛二毛沒有口糧,只得分“洋火”的口糧。我從父親嘴里獲悉,一般教師每月國家給三十二斤口糧,對體育教師照顧,每月多六斤。兩個孩子沒有到來前,三十八斤糧票對“洋火”來說,每頓只能達到七成飽。現在添了倆娃,每月人均只有十二斤七兩,攤到每天,人均只有四兩二錢。四兩二錢的概念“洋火”比誰都清楚,兩個小孩拳頭大的窩頭加上一碗小米稀飯而已。
“洋火”老婆一人掙工分養活倆女娃,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根本接濟不了父子仨,城里的事只能城里解決。“洋火”是個會過日子的人。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起了床,先是和面揉劑,做好六個面坯,再捅開煤爐,用大鐵鍋蒸出六個窩頭。蒸好后,再抓一把小米,熬一大鍋稀粥。做完這一切,方才搖醒大毛二毛。“洋火”從鍋中取出三個窩頭,每人一個。干糧分配完畢,便開始用大瓷碗盛粥,“洋火”先動手,舀的是上面的清湯,大毛的是半干半稀,只有二毛的是碗稠米粥。三人分罷米粥,“洋火”坐在椅子上,倆兒蹲在地上圍成一圈,中間放一盤咸菜疙瘩,稀里嘩啦吃早飯。
中午,整個縣高都是十二點左右吃飯,只有“洋火”家例外,父子三人要熬到一點半才揭鍋。一點鐘的時候,“洋火”把早上剩下的半鍋粥和三個窩頭餾熱,仍舊是每人一個,三人各捧一碗稀粥,餓狼般地一掃而光。
“洋火”父子三人從不吃晚飯。
每天晚上七八點鐘,床上三人的肚子咕咕哇哇一個比一個叫得響。一如往常,“洋火”這時便下床捅開煤爐,燒一大鍋開水,冷涼后三人一飲而下,肚子不叫了。幾泡尿撒過,時間到了晚上九點,三人的肚子重新咕咕哇哇鬧騰起來。有一次二毛終于忍不住問:“爹,為啥吃饃肚子不叫,喝水就叫呢?”
“洋火”想了好大一會兒回答:“大毛二毛,爹不是給你倆講過‘波浪運動’嗎,饃是固體,分子不運動,水是液體,每個分子都運動,運動時相互碰撞,就會發出聲音。這是物理學上的正常現象,別管他,睡覺吧!”
時光荏苒,“洋火”的一身肥膘日益減少,走起路來屁股上的兩坨肉也晃蕩不起來了。大毛二毛像現在時尚人士吃了減肥藥似的,變成了直挺挺的“麻桿”。
“洋火”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每晚九點,不再躺在床上,而是趁夜深人靜時,右手拎一支標槍,左手拎一張塑料薄膜出了門。縣高學生食堂前面有個泔水池,是學生倒飯菜殘羹的地方,夜里常有老鼠出沒。那個年代,縣里轟轟烈烈開展“抓老鼠”活動,上交五只老鼠,可以獎勵一個二兩的窩頭。到達泔水池旁,“洋火”屏住呼吸,側臥于塑料薄膜之上,右手緊握標槍,利用在抗美援越戰壕里練就的隱蔽本領,幾個小時一動不動,直到老鼠出現,才果斷出手。剛開始時,“洋火”每夜能刺殺四五只老鼠,第二天就拎著去縣“愛衛會”換窩頭。到了后來,老鼠變得越來越狡猾,兩個甚至三個晚上才能湊夠五只。領回窩頭后,“洋火”白天鎖在抽屜里,等到了晚上八點才開鎖取出,一掰為二,大毛二毛各一塊。從此之后,大毛二毛夜里的肚子不再咕咕哇哇鬧騰,“洋火”得意洋洋地說:“大毛二毛,饃是固體,分子不運動,沒有碰撞,所以肚子里也就不叫,爹說得對不對?”
大毛二毛齊聲回答:“爹說得對!”
高中每年給體育教師配兩套服裝一雙球鞋。球鞋是白色回力鞋,服裝春夏是一身白色背心和短褲,秋冬是一身藍色運動裝。到第二年開學的時候,其他體育教師都把洗得發白不成樣子的藍色運動裝扔掉了,換上了嶄新的運動裝,唯獨“洋火”不扔,他讓老婆裁裁剪剪,改成了兩件小衣服,穿在了大毛二毛的身上。因此,大毛二毛一年四季都是運動打扮。語文組有個瘦小精明的教師叫吳兆漣,找到我父親告狀說“洋火”“侵吞和轉移國家財產”。我父親把臉一橫,扔出一句話來:“如果你愿意去教體育課,也可以侵吞和轉移國家財產。”一句話把吳兆漣嗆得目瞪口呆。
“洋火”每周六節體育課上得生龍活虎。他一身白或者一身藍的身影每天都閃現在籃球場上。我和大毛是同班同學,小學放學早,放學后我倆都不回家,而是跑到操場上看“洋火”上課。“洋火”上課和其他體育老師不一樣,他們做過示范動作后,便站在球場外抽煙閑噴,我們那里把聊天叫“閑噴”。唯獨“洋火”做過示范動作后,仍然站在場內,見哪一位學生動作不規范,就跑上前再做一遍示范動作,一堂課下來大汗淋漓。大毛瞧他爹上課,一般是坐在地上一動不動,而我不一樣,站在場外有模有樣地模仿,有時“洋火”看到場外的我,也會板著臉吼上兩嗓:“錯了,錯了,先邁左腳,再跨右腿!”
過去的回力鞋不知道咋回事,遠沒有現在阿迪達斯和耐克的質量好,穿過半年之后,就會開膠,并且開了膠就再也無法粘上。但這個問題難不倒“洋火”。從每年下半年九月上體育課開始,“洋火”的回力鞋前面就綁了幾道繩子,到了十月底,回力鞋的中間和后跟又多了幾道繩子。剛開始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有一次和縣化肥廠籃球隊比賽,凌空躍起投籃的“洋火”腳底忽然飛出一個黑影,躥到前方十多米遠方才落在地上,觀眾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回力鞋的鞋底。
到了十二月份,繩子再也捆不牢兩個鞋底。“洋火”便赤腳上課。說是赤腳,實際上也不是。一次午飯后我去叫大毛一同上學,見他家門后放了半罐油漆,便問弄油漆干啥,他說他爹從學校木工組要來的,涂腳板用。我問涂腳板干什么,大毛說他爹下午有體育課,煤渣籃球場硌腳。還有一次我聽到“洋火”喊:“大毛,多涂一遍,爹下午替生病的王叔代課,四節課哩!”
“洋火”赤腳上課和比賽照樣風采依舊,彈跳高度不但絲毫未減,反而略高一二公分,“洋火”為此找出了根據:“動物中蛤蟆彈跳最好,你給蛤蟆爪子上套雙鞋試試?”赤腳大仙“洋火”成了縣城百姓津津樂道的人物,堪比現在的“網紅”。很多觀眾不認識“洋火”,但一看到球場上腳底涂油漆的,就立刻明白了其人的身份。兩年之后,“洋火”腳底板生出了一層粗繭,沒有牛蹄子的厚度,卻有牛蹄子的硬度。多年以后,酷愛籃球的我喜歡穿彈性好的牛筋底球鞋,廣告說此類球鞋是仿牛蹄粗纖維生產而成,我常常想,“洋火”的粗繭該不該算第一代仿生“牛筋底”呢?
去“洋火”家的次數多了,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洋火”只要不上體育課和給倆娃做飯,就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瞇著雙眼像個死人,但一聽到上課預備鈴響起,他便像犟牛一樣一躍而起,拎起籃球網兜就跑向操場。體育課上,“洋火”像換個人似的,不但集體教學一絲不茍,個人輔導也忙得不亦樂乎。下課鈴一響,“洋火”收拾完籃球,拎起網兜就往家里跑,跑到家,臉也不洗,便倒頭躺在床上,樣子像極了現在網上流傳極廣的“葛優躺”。
“洋火”如此,倆兒也一個俅樣。中午放學后,大毛二毛回到家撂下書包就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不到下午一點半揭鍋吃飯不起床。傍晚放學后,天還大亮,父子三人不約而同上了床。每次我和其他小朋友去他家玩,都是站著和躺著的大毛二毛說話,經常有一搭沒一搭地。后來我們都認為父子仨個個是懶蛋,躺在床上“裝死”,也就不去了。我把看到的情況給父親說了,父親聽罷半天沒吭聲,最后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看來生命在于靜止啊!”
告“洋火”狀的第二天,父親去了趟他家里,“洋火”一見是我父親,慌忙從床上爬了起來。
“‘洋火’,你不是天天宣傳‘生命在于運動’嗎,咋整天像頭懶豬躺在床上?”
“生命在于靜止啊!”“洋火”回答。
“聽好了,從明天開始,下課后或者周末拉著你的籃球隊到縣城其他單位去比賽。”父親吼道。
“校長,俺去過幾次,后來人家就不讓進門了。”“洋火”說的是實話,他過去領著縣高籃球隊去過幾次化肥廠、農機廠和消防隊比賽,球賽結束后主人都會按規矩留客吃飯。每頓飯,“洋火”一個人能吃下二十七八個花卷外加六碗大米稀飯,活生生五六名工人或消防隊員的口糧。三五次之后,“洋火”帶著隊員再去敲門打球,廠長和消防局長就不同意了,隔著門縫朝外罵:“滾,滾,滾,俺們正在忙著促生產,哪有閑工夫打毛蛋!”
當天下午,父親就給農機廠廠長崔大壯打了電話,崔大壯是父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老學生,那時的學生念舊。
“大壯,我們要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星期天讓我的人和你的人打場毛蛋!”
“老校長,不是俺不支持打毛蛋,怕的是打完毛蛋咋弄哩!食堂老王說,一個叫什么‘洋火’的,打毛蛋前一天就不吃不喝了,來到俺這一頓頂五六頓,工人們都有意見啦!”
“大壯,你每次都在全縣會議上發言講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實現機械化,而手下的工人都是大老粗,咋個實現法?!打完毛蛋后,讓‘洋火’給你的人輔導輔導,特別是物理學上的‘布朗運動’,他給我輔導過,我認為對你們一定有用!”
崔大壯礙于面子,只得接受。
每隔一周,父親就幫“洋火”聯系一個單位,還特別叮囑“洋火”,打毛蛋得有撿球的,讓大毛二毛跟著去撿球。除了農機廠、化肥廠、消防隊外,父親還聯系過鐵鍋廠、被單廠、供銷總社、郵電局、廢品收購站……半年之后,輪過幾遍又排到了農機廠,崔大壯在電話里哭喪著臉喊:“老校長,這次就換換單位吧,‘洋火’給廠里的工人講過四遍‘布朗運動’了,人人都會背了!”
兩年間,“洋火”的隊伍和縣城三十六家單位打了不知多少輪毛蛋,再這樣打下去,估計要出問題,“老油條”又生一計。
縣高中每學期期末都評積極分子,學習積極分子、學工積極分子、學農積極分子、勞動積極分子等等,父親找到已經成為體育教研室主任的“洋火”說:“‘洋火’,每個教研室都評積極分子,你們咋不評?”從此之后,體育教研室每學期開始評積極分子,由于體育活動群眾基礎好,評的人數特別多,每年都有一百多名,尤以家庭條件好的孩子居多。
“洋火”拿著獎狀到校長室加蓋大紅印章的時候,父親問:“獎狀咋發?”“洋火”回答:“開個表彰會,讓學生上臺領。”父親頓時翻了臉:“你這個當主任的就是懶,一個一個給我去送,這樣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讓學生家長在自豪的同時,也懂得生命在于運動的深刻道理。”父親話畢,抓起電話就撥給了縣糧站主任吳全收:“胖子,你兒這個學期表現不孬,評上體育積極分子啦!這個學期能評上體育積極分子,說不定下個學期就能評上學習積極分子,比你當學生時強多了!”吳主任電話里感謝不斷。父親最后說:“我派個人晚飯前到你家里送獎狀,中不中?”吳主任滿口應答。“洋火”急忙說:“校長,飯前去人家里,不妥吧!”父親擺了擺手,說:“去,去,去,讓你去你就去,啰嗦個啥!”
我老家有句俗話:“要甜不過棗子,好吃莫過餃子。”吳主任讓老婆包了一大面板餃子等待學校派來的頒獎者。我們那里的餃子比現在飯店里賣的估計要大一倍,一般飯量的人二十來個就能打住,好飯量者頂多也就三四十個。吳主任一見來者是個五大三粗的體育老師,用大海碗裝了四十來個餃子,一點湯不帶。
“洋火”嘩嘩啦啦三五分鐘吃完,抹了把嘴,連聲稱贊香香香。
“吃飽了沒?”吳主任問。
“差不多!”“洋火”扭捏地回答。
“差不多還是欠點!再下,再下!”吳主任是個實在人,讓他老婆又下了三十來個。
嘩嘩啦啦四五分鐘,一碗餃子再次入肚。“洋火”抹了把嘴,連聲稱贊香香香。
“現在吃飽了沒?”吳主任問。
“洋火”遲疑片刻,說:“差不多!”
“差不多還是欠點!再下,再下!”
吳主任老婆把面板上剩下的三十多個餃子一鍋煮了。
仍然是嘩嘩啦啦,“洋火”用了四五分鐘時間,大海碗見了底。
“現在該飽了吧?”吳主任問。
“如果沒有餃子了,上碗湯頂頂,也就飽了!”
吳主任大驚失色,遲疑了一下慌忙沖老婆喊道:“要是老校長知道俺用餃子湯當餃子待客,非罵扁俺不行!再包,再包!”吳主任說。
吳主任老婆急忙和面剁餡,累得滿頭大汗,一個鐘頭后,三十多個餃子才端上桌……
“洋火”一連頒發了七八年的獎狀,半個縣城的家戶他都蒞臨過。當時在我們縣城,不知道勾股定律,不知道牛頓定律,不知道愛因斯坦能量公式的大有人在,但不知道“布朗運動”的寥寥無幾。經我父親力薦,“洋火”還兩次獲得全縣體育運動推廣積極分子的稱號,他光著雙腳上臺領獎的時候,臺下的掌聲經久不息。還有一件事要說說,1975年我老家發大水,一個學期操場因儲存堆積救災物資沒法上體育課,也就評選不出體育積極分子,父親就讓“洋火”代發學習積極分子獎狀。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詞來形容這事,現在有了,叫“跨界”。
后記
先說兩件事。
一件是幾十年前跟著“洋火”圍攻我父親的那幫學生中,出了三位名人,兩個是省籃球隊的隊員,另外一個是用“布朗運動”降服我父親的那位留分頭的學生,他考上了大學,最后成了中科院半導體領域的院士。寫這篇小說時,我給他打過電話,問能不能用他的真名,他說:“年輕時無知,現在想想多丟人,就用‘留分頭的家伙’代表我吧!”“留分頭的家伙”后來回母校做過幾場學術報告,雖然他研究的是固體領域,但每場報告都以液體領域的布朗運動來起頭。
另一件事是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去美國留學,同時得到了耶魯、賓西法尼亞、普林斯頓和布朗四所“常青藤”大學的通知書,我征求父親的意見,對外國大學一竅不通的他毫不遲疑地回答:“你喜歡運動,就去布朗大學吧!”于是,我就去了布朗大學。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退了休,跟著我住在外省。九十年代中期,“洋火”也退休了,仍然住在縣高家屬院內,因為大毛從師范畢業后,回校做了物理老師。父親每次回縣城,“洋火”都會來瞧他,兩人只要坐在一起,就喋喋不休地爭論“生命在于運動”或是“生命在于靜止”,聽者無不捧腹大笑。
世紀之交,我老家的縣高評上了省重點中學,上級每年都按升學率對重點學校實行淘汰,當上校長的大毛為保證升學率,把沿襲了幾十年的六節體育課壓縮到了四節,后來仍嫌效果不佳,再次進行了課程改革,高中一年級保留兩節體育課,二三年級干脆取消了,四名體育老師被分配到了總務室和保衛室工作。
得知此消息的當月,父親急匆匆回老家約見“洋火”。
“‘洋火’,你口口聲聲說什么生命在于運動,咋沒說服你大兒子?”
“洋火”無話可答。
父親說:“走,叫上改行的四名體育老師,找大毛去,不能取消體育課。”
四名體育教師不敢去,我父親做了半天工作,才說動他們。六個人一起來到了校長室。
大毛客氣地給一群人各倒了一杯水。
“大毛,爹過去給你說了多少遍‘波浪運動’,雖然這杯水看起來是靜止的,但每個分子都在運動,在學校里,每個學生就是每個分子,不運動違背規律啊!”
“爹,是‘布朗運動’,不是‘波浪運動’,給你糾正幾百回了。現在的形勢和過去不一樣,不懂的事你就別瞎攪合了!”
“洋火”一下子卡了殼,我父親急忙接過話茬:“大毛,都說生命在于運動,現在學生一天到晚坐在教室里不動,時間長了吃不消啊!”
大毛笑著說:“老校長,俺說句實誠話您別往心里擱,自己當校長時倡導生命在于靜止,咋到俺當校長時,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變成生命在于運動了呢?!”
父親啞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