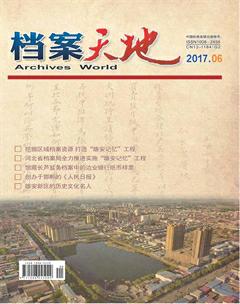試論檔案聯合編研的主體、客體及模式
蔡敏芳
檔案工作的最終目的是發揮檔案信息的價值,檔案編研作為檔案信息輸出的重要形式,力圖將“死檔案”變為“活信息”,主動向社會各界提供系統、科學的檔案服務。單一主體參與的編研工作普遍存在編研人才缺乏、投入資金不足、檔案資源貧乏、編研成果形式單一等問題。反之,檔案的聯合編研將檔案部門獨自承擔的編研工作分配一部分給公民社會(包括社會組織、志愿團體、公眾個體),形成檔案部門為核心、其他機構或組織為依托的模式,各方聯合對檔案進行多方面、深層次的開發,進而提高編研工作的效率和水平,走向檔案社會化“大編研”的道路。
一、檔案聯合編研主體的多元化
(一)多元化的編研主體
從主體構成來看,聯合編研的主體包括檔案部門、社會組織甚至是公眾個體。由檔案部門唱“獨角戲”而把社會公眾排除在外的編研是一種“閉門造車”,這種封閉式的檔案編研造成編研成果與社會需求間的巨大鴻溝,不利于檔案價值的充分發揮。由單一檔案部門轉變為多主體聯合參與,將成為新時代檔案編研工作的新趨勢,將從事不同職業、來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思維的公眾調動起來,賦予他們自由參與的權利,同時,不同組織機構(如檔案中介、信息服務中心、社會團體等)在編研工作中發揮獨特的作用,從而發出更加多樣的聲音。
從主體素質來看,來自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專業的編研主體,除檔案素養外還可能具有史學素養、傳播學素養、信息素養、創新素養,歷史學家、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等從各自專業的角度,為檔案編研工作注入新活力。
(二)各主體間的協調互補
聯合編研需要形成檔案部門、機構組織及社會公眾間協調互補的良性關系,使各參與主體都能夠發揮所長。
1.檔案部門的引導作用。檔案部門不再是編研工作的唯一主體,其在編研工作中的絕對權力遭到分割,成為聯合編研中的重要一環,起著凝聚各種力量、推動編研工作順利開展的引導作用。
2.機構組織的紐帶作用。機構組織參與編研是公眾力量與檔案部門交鋒的結果,一方面,部分機構組織承擔著檔案部門所不能完成的編研任務,在編研工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機構組織是個體利益訴求的“發言人”,力量薄弱的普通公眾可以結成團體或協會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3.社會公眾需求的釋放。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檔案意識的提高,人們要求多樣化且獨具特色的編研成果,這就需要檔案部門把更多的權力交給社會去博弈。公眾通過網絡志愿服務、檔案眾包等形式參與到編研工作中,釋放自身的利益訴求和檔案利用需求。
二、檔案聯合編研客體的豐富性和共享性
檔案聯合編研的客體即檔案編研對象,除檔案部門的館藏檔案外,還包括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團體以及保存在個人手中的檔案資源,換言之,除體制內的官方檔案,涉及人們經濟、文化、科研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檔案都將成為重要的編研素材。
(一)編研素材的廣泛多樣
檔案編研素材由單中心(館藏檔案資源)向多中心(社會信息資源)擴散:從形成領域來看,口述歷史檔案、民生檔案、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社群檔案、家庭檔案、家譜檔案、社交媒體檔案等擴大了編研素材的范圍;從載體類型來看,照片檔案、音頻檔案、視頻檔案等多媒體檔案豐富了編研素材的形式。
一方面,聯合編研可以立足于各區域、各民族的特色檔案,與當地的人文特色結合起來,傳承和發揚民族文化,如根據廣西少數民族檔案史料編纂而成的《壯族歷代史料薈萃》《明實錄廣西史料摘錄》《瑤族過山牒文匯編》,立足于貴州水書編纂而成的《水書·秘籍卷》《水書·婚嫁卷》《水書·陰陽五行卷》;另一方面,聯合編研要密切關注社會各方的利用需求,追蹤重大事件,把握社會熱點,使編研工作以“開放”的姿態緊跟社會發展的腳步。中央檔案館電視專題片《共和國的腳步》和上海市檔案館百集系列專題片《追憶》的成功,離不開編研主體對社會熱點的準確抓取。
(二)檔案資源的共享整合
最新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國家綜合檔案館館藏檔案58641.70(萬件、萬卷),僅綜合檔案館就藏有數量如此龐大的檔案資源,這還不包括大量散存在社會組織或個人手中的檔案。如何開發和利用海量的檔案資源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檔案聯合編研破除了檔案部門間、檔案部門與組織機構間、檔案部門與社會群體間的資源壁壘,力圖形成各層級館藏資源的共享、地區間檔案資源的共享、體制內外檔案資源的共享、國內外珍貴檔案資源的共享,在共享的基礎上進行整合,為充分挖掘檔案信息的價值創造條件,以便形成滿足人們需求的編研成果。例如,上海市圖書館保存的盛宣懷日記和名人手稿,上海魯迅紀念館保存的魯迅先生重要文獻,在整合基礎上采取聯合出版或舉辦專題展覽的方式,反映上海城市文化的發展軌跡,對傳承社會記憶、重塑社會性格具有重要意義。
(三)涉及更加復雜的法律問題
早在1991年,我國《各級國家檔案館開放檔案辦法》就規定:“各級國家檔案館應采取自編、與有關單位合編、委托有關單位或個人編輯等形式,積極開展檔案史料的編纂出版工作,有計劃地配合社會需要和各種紀念活動,通過各種形式公布檔案。”編纂出版檔案成果是檔案工作的重要一環,檔案聯合編研涉及編研主體的聯合和編研客體的聯合,多方的協調與合作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更加復雜的法律問題,例如著作權的歸屬問題。新的《著作權法》對編研成果的著作權規定,“匯編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構成作品的數據或者其他材料,對其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體現獨創性的作品,為匯編作品,其著作權由匯編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上述條例對編研對象、編研主體權限和編研成果形式做了規定,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侵權現象的發生,維護了著作權人的利益。但是,對分散在組織機構、社會群體和個人手中的檔案進行編研,需要更多地關注隱私權和知識產權,尤其是涉及組織形象、個人尊嚴的檔案。
三、“大編研”的檔案聯合編研模式
打破檔案部門“以我為主”的編研模式,實行橫向和縱向多方位聯合的“大編研”模式。
(一)橫向聯合模式
檔案的橫向聯合編研以信息的公開和共享為前提,是一種以檔案部門為主導,其他平行部門(包括檔案領域和其他領域)共同參與、職能互補的編研模式,可以細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與同級檔案館(室)聯合。綜合檔案館可以與各專門檔案館(室)、部門檔案館(室)聯合編研,立足特色館藏,共享檔案資源,開發出獨具特色的編研成果。中央檔案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20余卷)。上海市檔案館與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聯合舉辦了“走進西藏——來自檔案館的精品”的展覽。
2.與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事業機構聯合。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是留存人類歷史、提供信息服務和延續人類記憶的科學文化事業機構。檔案館與圖書館和博物館的館藏在資源性質上具有相關性,在資源內容上具有交叉性。這些文化事業機構間的聯合能夠減少重復工作,提高編研的效率和質量。我國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館曾共同參與國際敦煌項目,制作了絲綢之路地名規范數據庫、敦煌吐魯番學者檔案數據庫,并成功舉辦了網上專題展覽。
3.與出版社、影視欄目等傳媒機構聯合。檔案編研是系統、主動地向社會進行信息傳播的工作,檔案部門與傳媒機構強強聯合,開發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檔案成果,更貼近人們的心理和情感。2016年3月,天津市檔案館與天津出版傳媒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利用市檔案館的豐富資源和出版傳媒集團在文化推廣方面的優勢,聯合推出了《近代以來天津城市化進程實錄》《日本在津侵略罪行檔案史料選編》《辛亥革命與天津史料匯編》《“北四行”檔案史料系列選編》《船王董浩云在天津》《天津老商標》等一批檔案史料典籍和大眾文化精品,深受社會各界好評。此外,檔案部門還與影視欄目合拍了集文字、聲音、影像、圖片、動畫和音樂多種形式于一體的影片,《一號機密》《新四軍》《青島要塞》《共和國的腳步》就是其中的典范。
4.與各地高校等教育機構聯合。面對社會影響力大或研究性較強的編研課題,可以充分借助高校優質的專家人才,形成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編纂與研究相結合的編研成果,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為了深入挖掘西安市檔案館深藏金匱的珍貴歷史檔案,合理利用西安豐富的高校科研資源,優化檔案文獻編研內涵,西安市檔案館與西安文理學院開展有償聯合編研工作,聯合編撰了《西安火柴工業》一書。
(二)縱向聯合模式
檔案的縱向聯合編研包括國家檔案館和地方檔案館間的聯合,省級、市級、區(縣)級檔案館間的聯合,突破館藏檔案資源的局限,使編研工作向縱深方向發展,實現各機構間檔案資源的互通互補。由于市、縣級檔案館的編研工作在人力、資源和經費上都稍顯薄弱,縱向聯合模式能起到互幫互助的作用。河北承德市檔案館和縣級檔案館進行了聯合,將市縣檔案館所藏32萬卷檔案中的珍貴、重點檔案案卷目錄分類匯集,編輯完成《承德市縣檔案館館藏指南》,使利用者能夠便捷地查詢到全市11個檔案館的館藏情況,實現檔案信息的共建共享。
(三)國內外聯合模式
前國際檔案理事會主席王剛曾指出,“檔案事業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共同的事業需要國際間和地區間的密切合作。”檔案的聯合編研在國家間同樣適用,尤其在解決珍貴檔案散失海外的問題時。對于一些暫時難以收回原件的檔案,以聯合的方式出版編研著作或舉辦專題展覽,起到了填補歷史空白、維護歷史完整的作用,有利于凝聚民族力量,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
上海市檔案館曾與日本橫濱開港資料館聯合開展“上海——橫濱都市近代化比較研究”活動,舉辦比較圖片展,合作出版比較論文集和圖片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先后與韓國漢城大學、新加坡國家檔案館開展合作,聯合出版了《清代中朝關系檔案史料匯編》《清代中朝檔案史料續編》及《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系檔案史料匯編》;2015年12月,首部輯錄“中國養父母”群體信息的史料著作——《中國養父母歷史檔案》正式出版,該書正是在哈爾濱日本遺孤養父母聯誼會和中日雙方各界人士及有關部門的支持下聯合編寫的,以一千多個家庭的歷史情況和部分當事人口述歷史為資料,匯編了1945年日本戰敗后被拋棄的日本孤兒在中國收養的情況。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