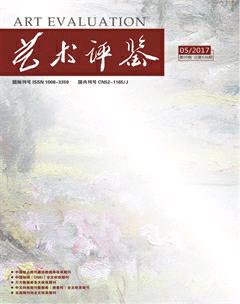隨武鳴之鄉,趕歌圩文化
張瑤
摘要:他們對唱所唱的民歌,實則是指壯族二聲部民間歌曲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生存狀態。這其中包含有專業人員剛接觸它的原生形態,也有多種因素促其稍變的次生形態。就像我們此次前去欣賞到的壯歌,有比拉柳拉、比羅嗨、比呃等。而這三種也是有所不同的,比拉柳拉的每段開始都有前呼后應;比羅嗨是臨結束時do與re碰撞,然后導入主音la終結;比呃則是兩聲部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關鍵詞:歌圩 壯鄉 對唱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09-0033-02
武鳴,壯族歌吁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在古壯語中,“圩”就是市集,“歌圩”實則是民眾因唱山歌而聚集形成的市集。在清光緒年間的《武緣縣圖經》有記載:“答歌之習,武緣仙湖、廖江二處有之,每年三月初一至十日,沿江上下,數里之內,士女如云。”足可見當時歌圩的盛況。然,“三月三”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俗話說“三月三,龍拜山”,是歌圩真正的起源。傳說駱越祖母王救下并養了一條斷尾的小蛇,還稱它為“搖尾蛇”,之后的小蛇漸漸長大,做起了珠江的守護龍神,由此駱越祖母王又被珠江流域民眾尊崇為“龍母”神,每逢農歷三月初三,搖尾龍神便會回到大明山為母親掃墓。后因為壯族先民們感念龍母的庇佑,便于每年農歷三月初三都聚集舉行祭拜儀式,并以山歌來歌頌龍母恩德,這便是最早的歌圩。作為儒教策源地的中國,音樂的主流一直是政治的附庸,宮廷雅樂、俗樂大都以儀式居上,與西方音樂體裁相比其藝術性空洞化性格明顯。宋、明以來,隨著城市文化的迅速成長也為民間藝術的發展燃熾了新的火種,在戲劇文化、器樂音樂、民間體裁等蓬勃發展的同時,我們又看到在追求藝術性、娛樂性的同時,也顯露出一種求新棄舊的發展軌跡。
在今年的“三月三”,對于歌圩文化甚是好奇的我們,便趁著國家特意為三月三放公假的時間,來到“歌圩圣地”武鳴參加2017年的歌圩暨駱越文化旅游節。到了這里,我們欣賞到了“歌王大賽”“駱越祖母王祭祀大典”“千人竹竿舞”“搶花炮”,拋繡球,舞龍舞獅,采茶戲……還吃到了五色糯米飯,感受到它的氛圍不亞于春節,還了解到三月三不單是壯族的重要節日,也是漢、瑤、苗、侗、仫佬、毛南等世居民族的重要節日,宋人著《太平寰宇記》中“男女盛服……聚會作歌”的記載,廣西駱越文化研究會會長謝壽球說“這源于古駱越時期農歷三月初三前后舉行的駱越祖母王祭祀大典。”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是稱“歌吁暨駱越文化藝術節”的原因了。
當然,在此給大家簡單介紹下我們這次去文化旅游節的安排,首先是,歌圩的開幕式。表演壯鄉人民慶豐收的《竹竿迎春舞》;緊接著,不同地兒有民間民俗體育活動,包括搶花炮、投繡球、板鞋竟速、打陀螺、滾鐵環混合接力賽、舞獅等項目,這樣既可以體現出壯族的少數民族民情風俗又可以將當地的地域性表現得淋漓盡致,更何況它的藝術性、觀賞性再一次為我們外來趕歌圩的人們創造近距離感受這種節日的氛圍,同樣也讓我們見識到了壯鄉人們這種樂觀豁達、民風樸素的精神面貌;當天晚上是壯鄉的文藝晚會,它有情景表演和壯族本地歌曲,如《三月長歌行》《壯鄉五色飯》等,反映壯族人民能歌善舞,幸福美滿的民風;第二天是,駱越文化文藝演出和展覽。文藝節目《駱越神鼓》,演繹壯族先民神物銅鼓象征權利、財富和地位的歷史文化,反映壯族先民的原始信仰,生活習俗和農耕稻作文化。另外還有反映駱越文化的書畫、攝影展、筆會等活動。還有廣西山歌的歌王賽,既可以展現壯鄉山歌本身的魅力,也可以為培養和選拔民間文藝人才提供舞臺。
當天晚上結束了所有的活動后,我們邊走邊想,是怎樣的文化底蘊造就了這樣的歌圩文化的出現?追溯到原始社會,歌圩更多地是表現為對自然的祭祀行為,用載歌載舞的形式向大自然表示敬畏,向神靈禱告,以祈求風調雨順。但隨著人們的主體地位漸漸顯現出來,最初作為祭祀的歌圩活動便演變成了一項男女青年互相結交朋友的文化活動,成為一種融合了民俗風情與地域文化的文化活動。第二天我們沒有跟隨安排去觀賞他們的歌王大賽,而是去到老年活動中心外的沿河邊,看到了武鳴還有其他鄉縣的民眾搭臺對歌,除了在臺上男女青年對唱山歌以外,在臺下小涼亭中中老年人也會聚到一起成群進行歌圩比賽,待我們進一步了解得知,這是一項娛樂性強的活動,大概將男女分成兩組來對歌,也可另作分組,對唱的山歌內容不作要求,可以是抒發個人情感、表達愛情的歌,也可以是中老年人們茶余飯后的聊天,還有你一言我一語罵人的俏皮話,當然我們還特意請教了當地的民眾,他們的歌詞和曲調都是現編現唱,當然也有直接取已經存有的壯族自己的調子來進行填詞并演唱,唱法就是運用現在所說的原生態唱法,那既然有比賽就會有輸贏,歌圩的比賽輸贏與其他聲樂比賽不同:歌圩比賽是進行到一方已經對不上歌才算勝負分明,并強調中途是不能夠停止的,假使雙方實力相當,對上幾天幾夜也毫不驚訝,所以你在三月三前后幾天聽到夜半歌聲便懂得其中的奧秘了。
當我們再細細去品味壯歌時,你將被壯族民歌本身完整而成熟的對唱聲部觀念與豐富的對唱曲目所折服。他們對唱所唱的民歌,實則是指壯族二聲部民間歌曲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生存狀態。這其中包含有專業人員剛接觸它的原生形態,也有多種因素促其稍變的次生形態。就像我們此次前去欣賞到的壯歌,有比拉柳拉、比羅嗨、比呃等。而這三種也是有所不同的,比拉柳拉的每段開始都有前呼后應;比羅嗨是臨結束時do與re碰撞,然后導入主音la終結;比呃則是兩聲部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壯族這種對唱民歌與其相應的族群性民俗活動相依相存,群聚性民俗活動更是他們發展的載體,而它們也充分彰顯出群聚性民俗文化活動的特色,進一步充實其內涵。
毫無疑問,歌圩節,既可以很好的滿足像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想要趕一趕歌圩的眼福和耳福,也可以拉動當地的經濟并對于他們本民族的情感有一定的維系作用。不僅如此,還可以很好的為挖掘后繼的唱山歌的歌王等原生態歌手提供展現的平臺,同時對挖掘和推廣民族歌舞、劇種、民族手工藝品、少數民族服飾等都有一定的推廣和宣傳的作用。從世紀初,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西學”進入國門,隨之而來的是中外(西)、古今、雅俗文化之“遇流”及其延伸出的種種振蕩、探索和轉型。傳統音樂原本占有著的天下,一躍成了“三分天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格局中,中國的一批知識分子深深感受到“音樂”在中國的近代,已然不似“禮樂之邦”的古代輝煌,而只是“不足以促進我們民眾的向上精神”的“淺陋冶蕩之音”。換句話說,從晚清到明初,中國的傳統民族音樂在民眾眼里是有著不同的解讀——山歌小調隨性、隨情,繚繞在不知名的原野。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零零碎碎”的地方性音樂,不知如何來面對現代民族音樂國家的要求。當時的知識分子則不得不提出“國樂”這樣的要求,這不僅僅占領傳統民族音樂的部分,還有著延續音樂傳統的創造及其成果。據筆者所知,武鳴縣歌舞劇團編導的原生態民族節目《古岳鏗鏘》,2009年代表自治區參加首屆全國“女媧杯”民間歌舞比賽榮獲銀獎,還有武鳴縣尼達妮合唱團的成立,對山歌的繼承和保護起到重要作用,進一步從娃娃抓起,為培養新一代的山歌手,傳承與弘揚武鳴壯族優秀山歌,打造武鳴壯族文化的品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享譽世界等具有重要的影響,實現非物質文化保護、傳承與當地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雙驅動模式,這樣一個雙贏的“三月三”必定會越走越遠,讓我們期待武鳴的時代的到來。
參考文獻:
[1]楊燕迪.音樂學新論——音樂學的學科領域與研究規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