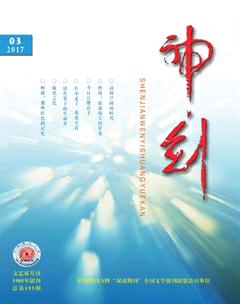語言:別把羽毛從鳥兒身上拔下來
閻連科
我們討論文學,當然不能不討論其最為重要之元素:語言。自古至今,凡被稱為文學的,都首先是其“語言”與“說話”的不同。凡被我們稱其為文學性的東西,都是首先從語言開始的。《伊利亞特》被荷馬最早吟唱出來時,并不是荷馬給古希臘人講了一個他們聞所未聞的故事,關于特洛伊,關于神居的俄林波斯山,關于萬能暴躁的宙斯和各懷心思的阿波羅和雅典娜,還有人的代表赫克托爾、阿伽門農和阿喀琉斯們,以及引發那場人與人、人與神、神與人的長達十年之久的混亂戰爭的絕美女人海倫等,他們的故事,早已流傳在古希臘人的身邊和嘴邊。但當荷馬重新把這些故事講出來的時候,這些故事就不再一樣了——不是故事不再一樣了,是傳播、傳遞故事的語言和方式不再一樣了。
荷馬是用詩的方式把那些故事吟唱出來的,不是古希臘人在狩獵場和捕魚的海上及收禾的田頭或橄欖樹下采摘時候順口說將出來的。荷馬把詩注入那些故事里邊了。或者說,荷馬從那些故事中挖掘出了詩。于是,文學產生了。文學語言也隨之應運而生了。
可以說,文學孕育了文學的語言;也可以說,是文學語言孕育了文學和文學性。
所以,當我們討論文學的語言時,最不該犯的錯誤,就是把語言和文學的整體分開來。無論一只多么美麗的鳥,它的美一定首先來之羽毛的美。鳳凰、孔雀、黃鸝等,我們之所以喜愛它,是因為它們的羽毛與眾不同,美輪美奐。我們對麻雀、烏鴉是沒有那么喜愛的。為什么?因為它們的羽毛太普通,鳥的數量又那么多,那么普及和遍布。回到我們說的文學語言上。可不可以把文學比為一只美麗的鳥,而語言則是鳥的美麗羽毛呢?然,當語言成為美麗鳥的羽毛時,我們需要謹記的,就是無論多么美麗的羽毛,離開鳥體都是無法產生的,無法獨立存在的。是鳥體產生并滋養著羽毛;也是羽毛滋養呈現著鳥的美麗的生命與存在。所以,任何討論文學語言的文章,把語言和文學的整體剝離開來,或者,把語言凌駕于文學的整體之上,顯然都是一種幼稚的錯誤。
在通常情況下,討論文學的語言,有以下幾種觀點和說法:1.語言是講述的工具。這是一種工具說;2.語言是文學之本身。即:文學就是語言,語言就是文學;3.語言是一種思維。文學之語言,即文學之思維。
現在,我們擺脫語言學、修辭學的抽象與高深,甚至擺脫關于語言的文學理論,回到寫作的實踐,回到文本之本身,完全從文本的角度,試著來分辨一下這各有其理的說法的意義和無意義。
第一,工具說。語言到底是不是敘述的工具呢?是。也不是。說語言確實是敘述的工具,是可以舉出許多例子的。大仲馬的《基度山伯爵》《三個火槍手》,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以及史蒂芬·金和丹·布朗的小說《閃靈》《肖申克的救贖》和《達·芬奇密碼》《失落的秘符》等,還有瑞典已故作家史迪格·拉桑的“女孩三部曲”,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的一系列作品,中國這樣的作家如金庸等。我們這樣把這些作家和作品排列在一起,絲毫沒有尊敬與不尊敬的道德覺悟。而只是說,有一類小說,當你閱讀它的時候,你已經忘記了語言的存在。忘記了文學的存在。你完全沉浸在小說的故事、情節、懸念、推理、恐怖和懸疑中間。你不去思考任何語言的存在和意義。你只被小說中故事、人物和事件的魚餌所吸引,想要揭開各種謎底大白于天下。
年輕的時候,我剛當兵入伍,讀了阿瑟·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和《東方快車謀殺案》,曾經徹夜不眠,念念不忘,白天到軍營外的射擊場打靶訓練,會自己在黃河故道的沙地上,有意地走出各種各樣的腳印:穿鞋的,不穿鞋的,快跑的,慢走的,用力跺腳在沙地和輕輕落下讓腳印淺些再淺一些的。甚至,會把自己的雙手套在兩只鞋子里,輕輕、輕輕讓那鞋子從黃河故道的沙灘上“飄”過去,留下兩行似有似無的痕跡,然后我就想,如果我殺過一個人,柯南·道爾和克里斯蒂這一男一女到這兒,會編出怎樣的兇殺和偵破的故事呢?甚至我還想,英國是怎樣一個國家啊?總是產生這樣的作家,是不是他們那兒每一棟的別墅里都藏有一起、幾起兇殺案?
所以,直到今天,每次到歐洲,只要住進鄉間別墅,我都緊張和不安,懷疑它們每一棟別墅里都有兇殺案。
言歸正傳。阿瑟·柯南道爾和克里斯蒂的小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沒有記住他們敘述中的一句話、一個字和一個詞。就是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沒有想到那敘述中的哪個字、哪個詞使用得奇妙而難忘,更不會因為哪一段話兒寫得好,而用筆在那話下畫出一條線兒來。與此在同一時間內,我還讀了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處女地》。尤其在讀《獵人筆記》中的《木木》和《白凈草原》那些短篇時,我幾乎沒有記住小說中的任何情節和故事,只有模糊的人物形象和清晰得要背下來的句子和段落。如《白凈草原》那個短篇,它從一開篇就放棄人物和情節,讓人對大自然的感受依附著語言準確、細膩而又層次多變地鋪展開來:
這是七月里晴明的一天,只有天氣穩定的時候才能有這樣的日子。從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像火一樣燃燒,而散布著柔和的紅暈。太陽——不像炎熱的旱天那樣火辣辣的,不像暴風雨前那樣暗紅色的,卻顯得明凈清澈,燦爛可愛——從一片狹長的云底下寧靜地浮出來,發出清爽的光輝,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霧中。舒展著的白云上面的細邊,發出像小蛇一般的閃光,這光彩好像煉過的銀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動搖不定的光線——于是愉快地、莊嚴地、飛也似的升起那雄偉的發光體來。到了正午時候,往往出現許多有柔軟的白邊的、金灰色的、圓而高的云塊。這些云塊好像許多島嶼,散布在無邊地泛濫的河流中,周圍環繞著純青色的、極其清澈的支流,它們停留在原地,差不多一動也不動;在遠處靠近天際的地方,這些云塊互相移近,緊挨在一起,它們中間的青天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它們本身也像天空一樣是蔚藍色的,因為它們都浸透了光和熱。天邊的顏色是朦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沒有發生變化,而且四周都是一樣的;沒有一個地方暗沉沉,沒有一個地方醞釀著雷雨;只是有的地方掛著淺藍色的帶子:這便是正在灑著不易看出的細雨。傍晚,這些云塊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像煙氣一樣游移不定而略帶黑色的云塊,映著落日形成了玫瑰色的團塊;在太陽像升起時一樣寧靜地落下去的地方,鮮紅色的光輝短暫地照臨著漸漸昏黑的大地,太白星像有人小心地擎著走的蠟燭一般悄悄地閃爍著出現在這上面。在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來,明凈而并不鮮艷;一切都帶著一種動人的溫柔感。在這些日子,天氣有時熱得厲害,有時田野的斜坡上甚至悶熱;但是風把郁積的熱氣吹散,趕走,旋風——是天氣穩定不變的確實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柱子,沿著道路,穿過耕地游移著。在干燥而清凈的空氣中,散布著苦艾、割了的黑麥和蕎麥的氣味;甚至在入夜以前一小時還感覺不到一點濕氣。這種天氣是農人割麥所盼望的天氣。
我第一次讀到這一長段的自然描寫時,那心中的震驚,完全不亞于柯南·道爾通過一個腳印、一串無用的鑰匙和扔在地上的一個煙頭的牌子、長短及彈掉在地上煙灰的多少和煙灰散落的形狀來判定死者或兇手的身份、地位、生活習慣乃至于他的性格。在當時,我以為那是屠格涅夫描寫的大自然的風光在吸引我。我把這段話用紅筆畫下來,并抄在我21歲的筆記本上。但是后來,當我把《獵人筆記》讀完時,發現那不能忘的不是屠格涅夫描寫的風光,而是他描寫這風光的語言。
因為,我出生在中國北方的農村,關于大自然中的森林、河流、田野、陽光、云朵、野獸、鳥雀等,這些在我的生活中一點都不少,而我少的是把這些寫出來的語言。對自然的感受,愛、恨、悲喜交加與純粹的欣賞,我樣樣不缺,可我缺的是把它寫出來的能力——語言的表達。《白凈草原》那篇小說,我至少讀過三遍以上,至今讀來,仍為屠格涅夫能用語言表達他對大自然感受的能力感佩不已。
至今我都以為,面對大自然時,屠格涅夫是那時俄羅斯文學中無二的語言大師。
現在有一個問題到來了。我們讀《尼羅河上的慘案》《東方快車謀殺案》《福爾摩斯探案集》等小說時,我們忘記的是他的語言,而吸引并讓我們的記住的,是它的故事、情節、場景以及懸疑的誘餌和謎與謎的連環。而讀另外一種小說,如《獵人筆記》和契訶夫的《草原》以及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卻常常會完全被文字(語言)所吸引。這就出現我說的第二個問題:語言并非敘述的工具,語言是語言之本身。換言之,語言不為敘述而存在,語言只為語言本身的生命而活著。而敘述,只是語言生命的載體。正如前類的小說,敘述的過程只是那些故事、驚悚、吸引力和謎串謎的載體,而語言,又只是這種敘述的工具。但后者的小說,語言本身已經成為我們欣賞、愉悅的滋養,而不僅僅是人物、情節與思想。語言在這些小說中不再是工具,而是語言之本身,是文學之本身。現在,我們可以用最簡單而略帶粗野、武斷,甚至不那么十分精確的方法來判斷兩類小說的價值:一是你在閱讀中忘記了語言的存在,雖然你還在不停地閱讀的小說。而另一類小說,它在你的閱讀中,時時提醒你語言的生命和存在,甚至你就是為了那些語言而閱讀。而且,承載著這種語言的小說,不僅在你閱讀時存在,而在閱讀后還久久存在于你的記憶和回想中,因此你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去重讀和思考。哪一種小說更有價值和偉大?語言在這兒其實成了主要元素和試金石。
當然,在這兒,語言不是敘述的工具,而成為第二個問題的語言之本身、文學之本身時,又有一種偏見出現了。長期以來,文學史和那些教文學的教授們,以及最為致力、癡迷小說語言的作家們,都有一種千古不變、攻守同盟的理論,即:小說是語言的藝術。毫無疑問,一個偉大的作家,不會僅僅把他的偉大建立在小說的語言上。盡管我們在創作一部小說時,你對小說的一切理解,都必須通過語言去展示和實現,但當語言出現在你的筆端時,語言不會無所憑依而到來。這也正如一片云的到來,它必須借助風流、氣壓和日光等才能向你展示它的來到和美麗一樣。這是偏見的,有失公允的。對一個成熟的作家而言,當你的公允力只停留在語言上時,你的幼稚就已經變得根深蒂固、偏執到無可救藥和無法校正了。
語言無法脫離敘述而存在,而敘述沒有物事與心緒,這就像人要行走而雙腳又不愿落入塵埃和大地上。所以,當把小說藝術上升為小說就是語言的藝術時,其實,就等于說一棵樹的美,就看它的葉子、花卉美不美。或看它枝葉、蓬冠美不美。看一個人的深度與厚度,而把目光停在他的衣著、皮膚、秀發和儀表上,而不用有更深的跟進與追究。我們忘了在希臘的眾神中,英雄安泰力大無比,可他一旦雙腳離開大地,就幾無縛雞之力、必死無疑那則傳說了。忘了再美的孔雀開屏,也不能離開那家雞一般的孔雀的肉體了。如此而言,除了語言,小說中那些也一樣重要的有時比語言更為重要的其他文學元素呢?最近聽說,美國第三次翻譯出版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讀者驚呼我們現在讀到“真正”的托爾斯泰了。讀到真正的(更接近的)《安娜·卡列尼娜》了。為什么?因為此前的翻譯,語言都太美、太過詩意,而這新的譯本,語言則更為粗糲和泥沙,更符合原本俄文的托爾斯泰。這是一則笑話與傳聞,聞而過之,實不可取。但它即便是真的,也并不影響托爾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偉大與價值。而這兒,不是說托爾斯泰的寫作不重視文學之語言,而是說,他并不把小說僅僅作為語言的藝術而致畢生之努力。他深明,偉大的小說,是小說一切藝術元素的平衡和均力,正如一臺跑在讀者閱讀中的蒸汽機,每一個部分出了問題,那蒸汽機或火車,都會戛然而止停下來,都會成為一堆廢鐵停在那無人問津的閱讀荒野上。
到這兒,關于語言的第三個問題出現了。——語言即思維。現在,語言為文學之思維的說法在中國作家中頗為盛行和時尚。可這種說法的鼻祖在哪兒?準確的解釋又是什么呢?尤其在詩人中間,已經把語言(詞語)上升為神的高度,似乎不視語言為神靈,這位詩人(作家)就不夠純粹和高尚。
維特根斯坦曾經說,“想象一種語言,即想象一個世界”“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這說出了語言無邊的意義,可同時它也說出了語言的有限性。即:世界有多大,語言就有多么寬廣——這句話翻過來的意思是,世界有多么寬廣,語言才可以有多么寬廣。為了語言即文學思維這個概念,我特意請教了北京大學的文學老師。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他非常鄭重地向我推薦了由中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美國語言學家本杰明·李·沃爾夫的文集《論語言、思維和現實》。我回去認真地閱讀這本書,就像一個鐵匠在仔細研究鐘表匠做表制鐘的過程一樣。這就讓我忽然明白,一個作家,就是作坊中的一個鐵匠、木匠、泥瓦匠,你的寫作就是燒打出各種各樣的鐵器,制出各種各樣的木器和建蓋出適合當地文化、風俗審美的各式各樣的房子。而那些批評家,尤其是語言學家,則是那些可以把粗制的鐵器當作手表拆解分析的人。但是,在沃爾夫的那篇《習慣性思維、行為與語言的關系》的長篇論文中,最后他對語言、思維和行為三者的關系總結道:“在語言和文化(當然包括文學)的結合中存在著各種聯系——語言分析和各種行為反應的聯系,語言分析和各種文化發展所采用的態度的聯系。因而,傳令長的重要性確實有一種聯系,不是與缺乏時態這一特征本身的聯系,而是與一個思想體系的聯系。在這個體系中,與我們的時態不同的范疇是很自然的存在。要發展這些聯系,最佳途徑不是專注于語言學、人種學或社會學的典型描寫方法,而是將文化和語言當作一個整體對待。”這段總結,非常清楚地強調了語言和一個“思想體系”的聯系,應該將語言和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當作一個整體去對待,而不能把語言從整體中抽離出來。文學語言,也亦是如此。無論你把語言上升到多么高的位置,語言的存在,都必須有對象的存在。在這兒,“言之有物”,已經不再是文學敘述中空泛、空洞與實在的意義,而是關于語言與文學整體的聯系。“實際上,思維是非常神秘的,而目前對我們理解思維幫助最大的,是對語言的研究。語言研究顯示,一個人思維的形式受制于他沒有意識到的固定的模式規律。”
凡此種種,都在說著語言的有限性,而不是語言的漫無邊界的高度和萬能;不是說,語言就是思維之本身與本質。不是說,在文學中,因為有了語言,就有了文學的一切。
總之,在我們有限的閱讀范圍,無法從文本中找到一部(一篇)“語言為文學的萬物之源”的小說。也無法從文本上弄明白“語言即思維”這種觀念在寫作中的實踐(哪怕是失敗)之作。但是由此,它讓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寫作的過程中,人物、故事、情節和敘述方法等,對天下的作家而言,都有可能形成共識和彼此交叉的重復,容易在甲和乙,乙和丙的寫作中重疊和相似,唯有語言,是最可以獨有并更為個性的,一如天下人的行為與思想,多都與他人不可分開來,唯有他的聲音——他最細微的言說,則最為也最易與人不同、與眾不同。所以,我們發現了一種存在——世界觀決定一個作家的陣營立場,文學觀決定一個作家的藝術陣營,俗言之就是風格與追求。而人性觀,則決定一個作家的情感立場與愛恨的糾結度,而語言,則最可能分辨和決定一堆作家中的“這一個”或那一個。就是說,世界觀、文學觀、人性觀在決定了作家中的一群或一個后,語言更為細致地分出了“這一個”中的你、我、他。于是,在寫作中,關于語言就有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語言即我。
一切都從文本出發,我們不可被寫作理論的空穴來風吹得迷三而倒四。
在本文開頭,我首先講了一句話:一樁無奈的事情到來了。意思是說,我們講的是十九世紀文學。而我們在這兒要談論的語言,也自然應該以十九世紀的文學為藍本。然而,無論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凡來到中國的,都是經過翻譯的。以俄羅斯文學為例,我們談論托爾斯泰的語言,其實談論的是經過草嬰先生翻譯的語言。談論屠格涅夫《父與子》與他的中短篇小說之語言,是在談論巴金翻譯的語言。談論《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這兩部偉大小說那種刻骨的揪心之描述,又是在談論耿濟之和岳麟們的翻譯之語言。基于此,如果我們把同一部小說換為另外一個翻譯家,立刻就會發現,小說的故事、情節也許還是那樣兒,但語言——語言的腔調、節奏、詞語都發生了不能接受的變化。如果是詩歌,還有可能出現南轅北轍、黑白混淆之亂象。
這就是我說的一樁無奈而尷尬的事。談論語言,必須以母語為本。而在母語寫作中,十九世紀文學達到高峰時,我們的中文小說還在文言文的跋涉中。白話小說,還遠未開始。這樣兒,我們討論十九世紀的文學,也就只能以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為例了。
為什么說在語言這個問題上,是“語言即我”呢?因為一個寫作者的文學觀、世界觀、人性觀大多只能把作家分成“我們”和“你們”,“他們”和別的“一群人”。文學觀和世界觀,其實是文學的“黨派性”和“宗教性”,是群體的基礎性,是流派形成的最基本的土壤。而不是作家中“這一個”的細微之別,只有語言,才可能是這一個與那一個作家寫作安檢中的指紋。作家中真正有價值的是“這一個”的寫作人,不是“這一群”或“那一群”,如人物中的“這一個”,是十九世紀寫作中作家的立根之本,而寫作中的“這一個”和“那一個”的寫作人,也恰恰是一個作家在一個時代和一群作家中的立根之本。這個立根之本,在一群中分出“你”“我”“他”的標志與區別,不在共性的“我們”與“你們”中,而往往是在他“最個性”的語言中。是那種只有真正的讀者可以看到的語言中的“語言紋”。請注意,在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群星燦爛的作家中,經常在語言上被我們反復稱道的幾個作家是:魯迅、老舍、沈從文、張愛玲和蕭紅等。如果沿用狹隘、民族、私利的方法把張愛玲從“我們”的群體中排除出去,或從“他們”那一群中摘開來單說另論,那么,魯迅、老舍、沈從文、蕭紅等,應該都是“我們”這一國群的。這一群,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文學觀、世界觀、人性觀,應該都是“我們”的,趨近趨同的。是什么把他們分成了“我們”中間的“這一個”和“那一個”?當然不是他們的名字。而是他們的作品。更為具體地說,是他們作品中諸多藝術元素最小而最不易趨同的——語言。
我家的后面有一個很大的園……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里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云霄里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墻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里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會啪的一聲,從后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著,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墻,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遠。
這是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人所皆知的一段。
祖父雖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細看,也不過馬馬虎虎承認下來就是了。一抬頭看見了一個黃瓜長大了,跑過去摘下來,我又去吃黃瓜去了。
黃瓜也許沒有吃完,又看見了一個大蜻蜓從旁飛過,于是丟了黃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飛得多么快,哪里會追得上。好在一開初也沒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來,跟了蜻蜓跑了幾步就又去做別的去了。
采一個矮瓜花心,捉一個大綠豆青螞蚱,把螞蚱腿用線綁上,綁了一會,也許把螞蚱腿就綁掉,線頭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見螞蚱了。
玩膩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亂鬧一陣,祖父澆菜,我也搶過來澆,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澆,而是拿著水瓢,拼盡了力氣,把水往天空里一揚,大喊著:
“下雨了,下雨了。”
……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矮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愿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他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
只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可是白云一來了的時候,那大團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銀似的,從祖父的頭上經過,好像要壓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個陰涼的地方睡著了。不用枕頭,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臉上就睡了。
這是蕭紅的著名小說《呼蘭河傳》中蕭紅兒時在她家花園里最開心的童年和那永遠留給我們的花園與文字。這與魯迅的童年與他童年的那個花園相比較,他們的心境、歡樂、情趣幾乎一模一樣,所不同的是,他們使用其表達的文字——言說的語言和語言中的語言紋。再看他們面對死亡、麻木和國民性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現實,魯迅的短篇《藥》,幾乎就是蕭紅的中篇《生死場》的某種魂靈的早生,而《生死場》的寫作,則是讓那魂靈由南方的鄉村飄至東北鄉村的舞語。
西關外靠著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冢。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里祝壽時的饅頭。
……
微風早已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里,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
這是魯迅的《藥》中華老栓為了給兒子小栓醫治癆病去買人血饅頭和兒子死后,那被賣了腦血的瑜兒的母親去給兒子上墳,又在墳地相遇那吃了自己兒子腦血的也一樣死去的小栓的母親華大媽的場景和敘述。
下面,我們再來看《生死場》中月英從病到死,這期間她的丈夫和王婆及五姑姑們的行為:
月英坐在炕的當心。那幽黑的屋子好像佛龕,月英好像佛龕中坐著的女佛。用枕頭四面圍住她,就這樣過了一年。一年月英沒能倒下睡過。她患著癱病,起初她的丈夫替她請神,燒香,也跑到土地廟前索藥。后來就連城里的廟也去燒香;但是奇怪的是月英的病并不為這些香煙和神鬼所治好。以后做丈夫的覺得責任盡到了,并且月英一個月比一個月加病,做丈夫的感著傷心!
三天以后,月英的棺材抬著橫過荒山而奔著去埋葬,葬在荒山下。
死人死了!活人計算著怎樣活下去。冬天女人們預備夏季的衣裳;男人們計慮著怎樣開始明年的耕種。
實在說,在蕭紅的《生死場》中,充滿著魯迅的《藥》《祥林嫂》和《故鄉》的物事、場景和氣息。《生死場》就是這些小說精神的合體。其中病中的月英和華老栓、小栓及祥林嫂,他們血液的脈管,幾乎是相通相連,同源同根。而愚昧至極的月英的丈夫,又多有華老栓的魂靈。王婆與王姑姑,又多么和在兒子墳地相遇的華大媽和瑜兒的母親相似。就連這些小說中的氛圍、基調,也都是“死亡和墳場”的孤寂、冷寒與麻木的日常。那么,又是什么把這些小說真正區別開來呢?當然,是魯迅的名字與蕭紅的名字,是魯迅小說的故事與蕭紅小說的故事。這樣說,是完全正確而毫無差池的,但又總還不免讓人想到他們的相似性:來自世界觀的立場,來自文學觀和人生觀的對現實和人的認識。然而,他們又是截然不同的。不同如楊樹與榆樹都為北方的樹種卻完全不一樣。木棉花與鳳凰花,同為南方的花朵,又完全不一樣。松樹與柏樹,都為冬綠樹,又常被種在一塊兒,可他們又有哪兒相似可比呢?那么,在魯迅和蕭紅的寫作中,他們真正的差別在哪兒?最早是從哪兒開始不同起來呢——
語言。
魯迅的小說語言簡潔、冷硬,講究珠璣之力,針針見血。因為這樣的語言,也使得他小說的情節與細節,都如石塊、鐵塊樣結實、寒涼并帶著處處傷人的棱角和邊沿。而蕭紅的語言,則綿柔、細潤,多有枝蔓的生長。如果說蕭紅的語言是植物之藤,而魯迅的小說語言,則是剪除藤蔓后孤立或成串的帶刺的干果。如果說蕭紅的語言文風,多如秋冬之間細流纏繞的緩慢的河水,那么,魯迅的語言文風,則完全是酷冬中因冰凍斷流而鋪滿冰結與掛著冰凌的鵝卵石的河道。他們真正的區分,正是從這兒開始:因我的語言與你的語言的不同,從而變化、蔓延出了完全不同氣韻、氛圍的小說。就是那些小說彼此間有多少“我們”的趨同和相似,而最終,也因“語言即我”,而彼此分開成你的寫作是“我們”中的“這一個”,而我,是“我們”中的“那一個”。
關于語言,我們還可以繼續從各種不同的文本開始,進行各樣的討論和紛爭。但在這一課要結束時,我不得不說,無論魯迅多么偉大,蕭紅多么個性和綿柔,張愛玲多么才華如語言的女巫與神靈,老舍又多么地域和創造,而在語言與人物、與故事、與現實、與世相等等諸多的平衡和結合上,尤其從短篇小說說開去,魯迅的小說,讀來未免有語言的尖利和突兀,老舍未免帶有京腔京調那種“皇味兒”,張愛玲,那種才華的冷漠盡在語言中表露和凸顯,可蕭紅,寫得最好時,是她自己不知自己多好時,一旦知了也就失去了語言的純和真。反倒是我們一直未顧及談到的沈從文,在語言上的自覺與平衡,達到了至高的境界與完美——我說的是他在語言與文本整體的文學性的平衡上,既不讓語言成為離開鳥體飛起來的美麗無根的羽毛,也不讓語言成為龐大鳥體、物體上的裝飾和附庸,既不讓語言成為工具含有過多的物質性,也不讓它成為藝術的精神貴族在敘述的路上走著走著飄起來。這方面,他的短篇《丈夫》,可謂范例中的范例,經典中經典,是寫作中語言與文學整體性最完美結合的金鑲玉與和氏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