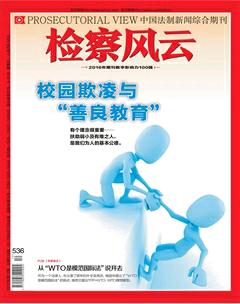做官的滋味
于永軍
滋味者,感覺也。做官乃啥滋味?這恐怕也是一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話題。
《尚書》中有則官訓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由此解讀這官滋味,庶幾可用一個字概括:“苦”。為百姓作“磨刀石”,苦;為百姓作“舟船”,苦。急百姓所急作“及時雨”,同樣苦。
這般鑒讀,絕不是筆者的管窺臆猜,而是歷朝各代清官廉吏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共同感受。據史料,這里聊舉幾例: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歷任州判官、戶部主事、兵部主事、兩京左右通政等職,73歲在南京任上病逝時,由于沒有兒子,僉都御史王用汲為他主持喪事。看到這個朝廷三品大員的住處,清貧寒酸的是用葛布制成的帷帳和破爛的竹器,家中沒有分文積蓄,禁不住哭了起來。《明史》評價海瑞:“苦節自厲,誠為人所難能。”借一個“苦”字刻畫“海青天”,可謂惟妙惟肖。
清代廉吏于成龍,官至兩江總督兼兵部尚書,卻一直過著簡樸清苦的生活。在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于同仆共食”;在江南,他“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天南地北為官20余年,他一直只身天涯,不帶家屬,只一個結發妻子闊別20多年后才得以一見,其清操苦節享譽當時,被康熙稱為“天下第一廉吏”。他68歲去世時,寢室只有一個放衣物的舊竹笥,里面裝著官服和簡單的靴、冠帶,后堂只有幾斗米、幾罐咸豆豉,別無余物。做官之“苦”,映照著“于青菜”,熠熠生輝。
做官的苦滋味,表述最清楚的當推“揚州八怪”之首鄭燮。他在“七品縣官”任上有首《青玉案》,將自己的感受描寫得淋漓盡致:“十年蓋破黃綢被,盡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當開釀,正是文書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妝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燈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因而他曾修家書感嘆:“人皆以做官為樂,我今反以做官為苦,既不敢貪贓枉法,積造孽錢以害子孫,則每年廉俸收入,甚屬寥寥。”從現有史料來看,鄭燮為官確實很苦:不僅收入少,而且因上書請求賑災,得罪了一些權貴,最后被罷免了官職,在揚州過著“宦海歸來兩袖空,逢人賣竹畫清風”的貧苦日子,直至離世。
清官廉吏何苦?原因很明了:一則廉潔自律,不貪錢財,經濟上苦;二則勤政為民,排憂解難,工作上苦。去了這個“苦”字,就喪失了官的本意。而蒲松齡老先生筆下諷刺的那種做官:“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階下百喏。見者側目視,側足立。”乃是“官念”的異化,是變餿了的官滋味。
“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史料載,海瑞死訊傳出,南京百姓罷市相哭,其靈柩運往故鄉時,穿著白衣戴著白帽的人站滿兩岸,祭奠哭拜的人群百里不絕。于成龍逝世后,出殯當日,“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心之心,江寧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
在“墨海沉浮”的封建時代,像海瑞、于成龍、鄭燮這等甘嘗苦滋味卻“窮且益堅”的清官廉吏雖如鳳毛麟角,但卻以做官的“苦”和“累”播撒了流芳百世的為官價值:做官苦,方能換來百姓甜;做官累,才有百姓安、社稷安。“古來不肖之人,皇靈不能使忌,天譴不使霅,而獨畏匹夫匹婦之口,何也?皇靈、天譴皆不必,而匹夫匹婦之口必也。”(明·馮夢龍《口碑部第三十一》)相對于百姓對“古來不肖之人”的口口相傳,“做官苦”卻千秋萬代美名播揚,或許這正是歷朝各代清官雖苦卻總不絕于世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