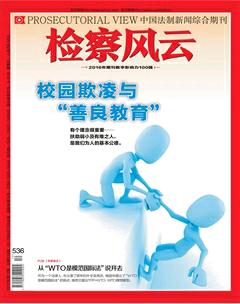數(shù)字追兇:犯罪地理畫像
顧建梅
數(shù)字與你同在
從出生那一刻獲得自己的生日開始,我們的人生就處處被記號(hào)筆標(biāo)注著數(shù)字。數(shù)字告訴我們時(shí)間,數(shù)字告訴我們天氣,數(shù)字告訴我們行程,數(shù)字告訴我們輸贏、成敗……甚至,數(shù)字還能自動(dòng)生成一份個(gè)人簡(jiǎn)介。當(dāng)身高151cm、體重75kg、月薪2K、年齡43,家庭成員人數(shù)為1時(shí),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了:你是個(gè)又矮又胖又窮又老的單身狗。
數(shù)字保證了你是個(gè)有“身份證”的人,然后你才可能是個(gè)有身份的人,只是這身份也許是犯罪嫌疑人的案卷編碼和監(jiān)室號(hào)碼——是的,數(shù)字居然還可以用來(lái)破案。
《數(shù)字追兇》是一部美國(guó)電視劇,該劇主要通過(guò)真實(shí)的事例,反映數(shù)學(xué)理論是如何被應(yīng)用到警方的調(diào)查之中,從而破解一件件匪夷所思的罪案。它以真實(shí)案例為藍(lán)本,將一種被稱為“犯罪地理畫像”的方法運(yùn)用在刑偵中。
地理畫像
在犯罪畫像中,有一分支是通過(guò)利用罪犯的犯罪地點(diǎn),而不是相貌和行為特征來(lái)預(yù)測(cè)他的行為模式。這種方法被稱為地理畫像。警方對(duì)案件進(jìn)行調(diào)查的一個(gè)焦點(diǎn)就是犯罪現(xiàn)場(chǎng)及其證據(jù)內(nèi)容。而導(dǎo)致犯罪現(xiàn)場(chǎng)的犯罪和空間行為的地理知覺卻常常被忽視。因?yàn)槿魏蔚姆缸锒际窃谝欢ǖ臅r(shí)空、一定的受害人及犯罪人之間完成的。
我們?nèi)匀挥脛≈兄鹘遣槔怼ぐ账沟慕忉寔?lái)了解地理畫像的特點(diǎn):當(dāng)查理看到家中草坪上的噴灑頭正四處噴灑時(shí),突然心有靈犀,他叫來(lái)哥哥:看到噴灑頭和水滴了?即便使用數(shù)學(xué)理論我也無(wú)法推測(cè)下一個(gè)水滴落在何處,這變數(shù)太多了。但假如我看不到這個(gè)噴灑頭,從水滴下落的軌跡,我能精確推算出噴灑頭的位置。這不是預(yù)測(cè)下一落地點(diǎn),而是通過(guò)推算所有落地點(diǎn)的共性,從而找到水滴的原出發(fā)點(diǎn)(噴灑頭)。
哥哥唐·艾普斯明白了,他們之前一直無(wú)法抓住那個(gè)連環(huán)強(qiáng)奸殺人犯是因?yàn)樗麄円恢痹谡蚁右扇撕皖A(yù)測(cè)下一個(gè)作案地點(diǎn),而地理側(cè)寫則把關(guān)鍵點(diǎn)放在:由案發(fā)地和受害人信息推算出犯罪嫌疑人的基地,再在鎖定的基地內(nèi)篩選和緝捕嫌犯。
所以,地理畫像是指將系列案件的各個(gè)作案點(diǎn)標(biāo)在地圖上,并對(duì)各個(gè)犯罪地點(diǎn)的空間分布圖形進(jìn)行分析,從而確定犯罪嫌疑人藏身匿跡的地域范圍的偵查方法。運(yùn)用地理側(cè)寫分析系列案件犯罪分子每次作案的地點(diǎn)在空間上所形成的點(diǎn)、線、面關(guān)系,可以比較準(zhǔn)確地推斷出犯罪分子最有可能所在的位置。換句話說(shuō),如果查明犯罪分子每次作案的地點(diǎn),就有可能據(jù)以找出犯罪分子作案活動(dòng)的“中心點(diǎn)”。這個(gè)“中心點(diǎn)”,在很多情況下就是犯罪分子的家或居住地。
真實(shí)案例:約克郡屠夫
1981年1月,英國(guó)警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緝兇行動(dòng)畫下句點(diǎn),警方逮捕了34歲的彼得·薩特克里夫——被稱為約克郡屠夫的連環(huán)殺手。
5年中,薩特克里夫殘忍殺害了13名女性,而無(wú)論警察的偵緝行動(dòng)多么迅速、嚴(yán)密,他每次都能搶得先機(jī),早一步從法網(wǎng)中脫逃。
是兇案留下的線索太少了嗎?不!
警方有諸多線索:幸存者對(duì)嫌犯描述:“他的頭發(fā)是深色的大卷發(fā),滿臉深色的大胡子,膚色偏白,眼珠顏色很深,幾乎是黑色的眼珠”;鞋印:鞋紋路屬于7號(hào)的工人靴,右鞋鞋底有個(gè)區(qū)域磨損嚴(yán)重,顯示此人可能是長(zhǎng)程駕駛員;現(xiàn)場(chǎng)的5英鎊鈔票:警方取得35家公司的名單,他們可能在薪水中發(fā)放過(guò)這批5英鎊鈔票,其中一家便是貨車司機(jī)彼得·薩特克里夫工作的搬運(yùn)公司。
是沒有篩選出嫌疑人嗎?恰恰相反!
5年間,薩特克里夫先后被辦案警察詢問(wèn)了10次。可即便發(fā)現(xiàn)他符合所有的嫌犯資料,也只有一名警察鎖定了他,而他的報(bào)告還被否決了。
那么,真的只是警察無(wú)能,辦案不力嗎?似乎也不是:此前西約克郡謀殺案的破案率之高在英國(guó)數(shù)一數(shù)二,他們已有好幾年沒有未破的兇案了。
是案件沒有得到重視嗎?更不是!
約克郡屠夫案警方收集了26.8萬(wàn)嫌疑人姓名,發(fā)動(dòng)了11.5萬(wàn)次行動(dòng),追查了5.3萬(wàn)名車主,共消耗了警方500萬(wàn)小時(shí)。
但,兇手仍然逍遙法外并繼續(xù)作案。
最后,英國(guó)警界的六大名探接管此案,他們被稱為“超級(jí)小組”。小組中有位特別的成員——鑒識(shí)學(xué)家史都華·坎德教授,坎德運(yùn)用自己在英國(guó)皇家空軍擔(dān)任導(dǎo)航員時(shí)掌握的技術(shù),創(chuàng)造出全新的技巧用來(lái)追緝約克郡屠夫。通過(guò)交叉對(duì)比每次攻擊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坎德鎖定坐標(biāo),指出兇手最有可能住在布拉福地區(qū)。坎德的地理側(cè)寫終結(jié)了警方大海撈針式的搜索,而更接近薩特克里夫。未幾,兩名警察在例行檢查中遭遇薩特克里夫,查實(shí)種種疑點(diǎn),令薩特克里夫罪行敗露。
地理畫像——應(yīng)運(yùn)而生
隨著社會(huì)的高速發(fā)展,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已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社會(huì)人員流動(dòng)的頻率與范圍都超出了傳統(tǒng)社會(huì),使得警方的工作常常陷入以下困局:
信息缺乏。在破案過(guò)程當(dāng)中,通常會(huì)面臨信息的嚴(yán)重缺乏,警方必須投入大量警力展開地毯式排查,有限的警力面對(duì)日益嚴(yán)峻的治安形勢(shì)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信息超載。信息超載導(dǎo)致大規(guī)模、長(zhǎng)時(shí)間及高成本的偵查。如美國(guó)雅圖綠河殺人案,歷時(shí)18年,專案組人員曾高達(dá)40人。調(diào)查過(guò)程中涉及1.8萬(wàn)嫌疑人,近萬(wàn)件現(xiàn)場(chǎng)物品。在約克郡屠夫一案中,連兇犯薩特克里夫都說(shuō):“警察已累到你說(shuō)什么他都信”的程度。
司法管轄限制及部門溝通不力。在甘肅省白銀市連環(huán)殺手案中,兇手高承勇常居的青城鎮(zhèn)隸屬于蘭州市,與白銀區(qū)只有一河之隔卻分屬兩個(gè)不同的地級(jí)市,每次作案,高承勇都是坐40分鐘的車去白銀區(qū),案后立即回到青城鎮(zhèn)。高承勇1997年在包頭犯下的兩樁命案,及至2004年才與白銀案并案處理。及至高承勇落網(wǎng),距其首樁兇案已有28年。
現(xiàn)實(shí)的難題驅(qū)動(dòng)警方去尋找有效的方法優(yōu)化警力部署、提高破案率及破案效能。地理畫像作為高效能的情報(bào)研判手段及方法,能夠輔助警方一線實(shí)戰(zhàn),優(yōu)先排查熱點(diǎn)區(qū)域及熱點(diǎn)嫌疑人,從而實(shí)現(xiàn)精確打擊犯罪,提高警務(wù)效能——
*地理畫像的理論基礎(chǔ)
國(guó)外對(duì)地理畫像的研究和應(yīng)用已經(jīng)有幾十年,并廣泛應(yīng)用于歐美頂級(jí)警察機(jī)構(gòu)及各級(jí)警察機(jī)構(gòu),且在應(yīng)用過(guò)程中不斷驗(yàn)證提升,其理論依據(jù)是犯罪心理學(xué)、環(huán)境犯罪學(xué)、犯罪地理目標(biāo)模型(CGT)、坎特理論和犯罪的地理慣技及犯罪模式等。地理側(cè)寫系統(tǒng)通過(guò)海量犯罪數(shù)據(jù)的驗(yàn)證,已成為科學(xué)高效的執(zhí)法利器。
*日常活動(dòng)空間理論
日常活動(dòng)空間是指?jìng)€(gè)人每天、每周定期活動(dòng)去的地方以及他們外出的路線。同其他社會(huì)人一樣,犯罪分子也要吃飯、睡覺、交通、消費(fèi)等,其日常生活也要受到工作、家庭的限制。這些居住、工作、購(gòu)物或娛樂(lè)的場(chǎng)所就是歸屬點(diǎn);行走在歸屬點(diǎn)之間的路線為路徑。犯罪分子根據(jù)日常活動(dòng)環(huán)境在頭腦中形成自己的心理地圖。研究表明,犯罪分子往往在購(gòu)物、拜訪朋友或上下班路上實(shí)施犯罪活動(dòng)。
*犯罪地理慣技
犯罪人對(duì)犯罪地的選擇是地理畫像中的焦點(diǎn),犯罪人都會(huì)選擇一種熟悉的方式作案,在非常強(qiáng)的相似性中,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犯罪人的地理慣技。
犯罪心理學(xué)認(rèn)為,系列犯罪往往是有預(yù)謀的犯罪,一般犯罪人在選擇犯罪地點(diǎn)時(shí)都會(huì)遵守“三不”原則。即:“不近、不遠(yuǎn)、不重復(fù)”。“不近”是指犯罪人在選擇犯罪地點(diǎn)時(shí)要盡量考慮避開熟人環(huán)境。他們不僅害怕作案時(shí)被熟人認(rèn)出或發(fā)現(xiàn),而且也擔(dān)心案發(fā)后自己被警察納入調(diào)查的范圍;“不遠(yuǎn)”是指犯罪地點(diǎn)不會(huì)離犯罪人活動(dòng)基點(diǎn)太遠(yuǎn),太遠(yuǎn)則犯罪人對(duì)犯罪地點(diǎn)環(huán)境的熟悉程度降低,從而大大增加了其犯罪行為被暴露和被抓捕的危險(xiǎn);“不重復(fù)”是指同類型的刑事案件不會(huì)發(fā)生在同一地點(diǎn)。一方面是因?yàn)榉缸锶撕ε卤恢槿税l(fā)現(xiàn),另一方面被害人也會(huì)提高警惕,這兩方面都會(huì)增加作案風(fēng)險(xiǎn)。英國(guó)著名心理學(xué)家戴維·坎特也認(rèn)為:“犯罪人選擇自己熟悉的、對(duì)自己方便的地方實(shí)施犯罪,至少在最初是這樣選擇犯罪地點(diǎn)。”
*地理畫像的模式
自20世紀(jì)90年代初由警官羅斯莫博士開始系統(tǒng)研究,至今已有三種地理畫像模式:1.羅斯莫模式,他的軟件是參宿七(Rigel);2.坎特模式,他的軟件是搜索網(wǎng)(Dragnet);3.萊寧模式,他的軟件是犯罪統(tǒng)計(jì)(CrimeStat)。
2005年以來(lái),犯罪地理畫像理論及國(guó)外應(yīng)用案例被陸續(xù)引入國(guó)內(nèi),同時(shí)伴隨著我國(guó)PGIS系統(tǒng)的全面建設(shè)和犯罪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的逐步完善,使其在我國(guó)的應(yīng)用研究成為可能。目前我國(guó)引進(jìn)并使用的地理畫像模式為參宿七(Rigel)。參宿七能繪出狀似山脈的立體圖,其中紫色是犯罪人最不可能的居住地,黃色和橙色為犯罪人可能居住地,而紅色頂點(diǎn)則是歹徒最可能的居住地。
參宿七比較挑食,它接的案件須符合這樣的條件:1.已發(fā)生的一系列犯罪, 有充分的證據(jù)顯示為是同一個(gè)犯罪人所為;2.在一系列犯罪中,至少有五個(gè)犯罪地點(diǎn)( 雖然在一定的環(huán)境中,只有很少的一些地點(diǎn)的評(píng)估成為可能);3. 能證明產(chǎn)生畫像所需的時(shí)間和努力是正確的。雖然挑剔,但參宿七真的可以快成閃電:一般地理畫像需要超過(guò)百萬(wàn)次的計(jì)算,參宿七能在約4秒內(nèi)完成計(jì)算。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