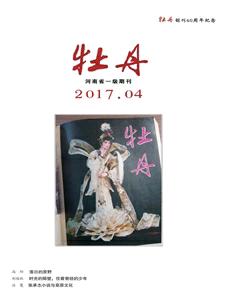《赫索格》
《赫索格》(Herzog,1964)是索爾·貝婁中期的代表作。其采用了意識流手法,描述了美國猶太裔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赫索格的困惑。從赫索格身上,人們不僅能看到猶太人流浪的經驗,還能夠看到赫索格所代表的現代人懸掛(dangling)的生存狀態。深厚的猶太文化背景在索爾·貝婁的作品中成為一座橋梁。貝婁將古老的猶太歷史同現代人生存連接在一起,從而使單一的猶太流浪歷史經驗上升到整個人類的生存經驗。
猶太知識分子摩西·埃爾凱納·赫索格是一位大學教授,他雖然學識淵博,但與現實格格不入。他結過兩次婚,有一兒一女。小說從第二次離婚后寫起。他的第二位妻子馬德琳與他的好友瓦倫丁私通,把他趕出家門。他內心異常痛苦,不停地給各種人寫信,在信中同死者、生者討論問題,盡管這些信件不曾寄出。他回到芝加哥童年的故居,拿走了父親遺留的手槍,想殺死馬德琳與瓦倫丁。但是,看到瓦倫丁耐心地為他的小女兒洗澡后,他打消了殺人的念頭。最后,他回到了馬薩諸塞州路德村的鄉村古屋中。
初看《赫索格》比較雜亂無章,涉及了多種視角、主觀與客觀的變化。小說現實的時間只有五天左右,但是信件內容和頭腦中的意識占據了大量篇幅。時空順序即紐約——芝加哥——路德村,過往經歷和情感軌跡主要通過書信和頭腦中的意識流來展現。小說圍繞著與馬德琳的糾紛牽扯出了他以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存。除了現實的時空軌跡,情感線索也是其中比較明顯的一條線。其中涉及了他歷任情人和妻子,以第一任妻子戴西、第二任妻子馬德琳、情人園子、情人雷蒙娜為主。
關于《赫索格》有很多的分析角度,如女性主義、存在主義或者身份認同等。本文主要從《赫索格》所顯露的猶太流浪歷史同當代人的生存入手。
貝婁明確表示他不愿意被稱作美國猶太作家,他從來沒有為猶太人寫作,但是他深厚的猶太文化淵源的確深刻影響了他的創作。他的小說中的主人公仍有明顯的猶太背景特征。而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的猶太人,和同是猶太作家的辛格等比起來,貝婁在適應美國社會方面比較迅速。他選擇了用英語寫作以及不再固守在猶太生活的創作范圍中。他通過塑造的掛起來的人的形象(Dangling man)而達到對猶太傳統的超越。
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談到了人們執意把作家拉回到小民族的背景中會曲解作家的美學意圖。因為對于一個作家來講,“在一個小民族的大家庭中,藝術家被多種多樣的方式,被多種多樣的細線束縛住了手腳。”
昆德拉認為正是因為這種做法才妨礙了小民族的藝術得到承認。一個作者的作品可能置于一個現代性的大背景中才能夠被理解,冒昧地拉回民族性的背景只會造成對作者的誤讀。索爾·貝婁拒絕將自己稱為美國猶太作家,并表示從來沒有為猶太人寫作。也許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對于索爾·貝婁來說,人們不僅要看到他作品中的猶太性,更要看到他作品中體現的現代性因素。
在《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論述:“由于猶太移民對居住地主體文化的適應及對異質文化的某種融合,非族語猶太文學在以種種方式呈現了猶太屬性的同時,也呈現了超越猶太的屬性……猶太人的遭遇濃縮了人類的共同命運,猶太作家往往把猶太人作為人類的代表或象征,在猶太因素與非猶太因素的結合中表現形而上的世界性問題。羅斯、貝婁等拒絕承認自己僅僅是猶太作家,并不意味著是對自己猶太屬性的否認,而主要意味著他們不僅是猶太的,更是超越猶太的。”
貝婁小說主人公擁有猶太背景及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利用這種背景作為一種線索同現代人類生活建立內在的聯系,從而顯示出更為深刻和普遍的文化內涵。主人公赫索格成為了一個中介:猶太流浪歷史和現代人生存命運的中介。《赫索格》是一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流浪史,在主人公赫索格身上既可以窺探到猶太人的流浪,也能看到現代人生存的懸掛。它塑造了一個掛起來的人,探究了現代人懸掛的生存狀態。
一、流浪的赫索格
主人公赫索格的流浪實際上是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流浪。本文從小說中體現的空間流浪、情感流浪、意識流浪乃至小說敘述手法上體現“流浪”等角度來對其進行分析。
(一)空間流浪
在書里赫索格經歷了從紐約到芝加哥,最終回到了鄉村路德村的空間移動順序。如果加上他的回憶,人們能夠看到這樣一條空間移動軌跡:路德村(馬德林辭去了體面的工作,買了馬薩諸塞州路德村的房子)——芝加哥(馬德林需要在芝加哥學習,同時要求赫索格給瓦倫丁找一份工作)——紐約(被趕出家門)——芝加哥(回去探望女兒瓊妮;拿手槍想殺死瓦倫丁)——路德村。赫索格在路德村鄉村自然本真中暫時得到寧靜。在這里他感到把馬德琳從他的肉里拔出了,并且決定一個字都不再寫了。《赫索格》中有這樣的描寫“他覺得這很好,比較安靜,樹林里的寧靜照拂著他,還有那美好的氣候。”“既聽不到繁雜的世事,也見不到遙遠的未來。每日的光華,行走在這里,在上帝的虛空之中。”他打掃干凈屋子等待著雷蒙娜到來。
(二)情感流浪
猶太人十分重視家庭生活,家庭不僅給孩子一個好的成長環境,同樣也給予了他們歸屬感。每個猶太人都要組建家庭,摩西十誡中也強調了婚姻關系的重要性。他們不鼓勵離婚,認為夫妻雙方應該互相關懷、體貼。赫索格的父母遵循了猶太人重視家庭的傳統,母親莎拉沒有因為父親的失敗而責備他,而是一心照顧家庭,幫助丈夫渡過難關。相對于第一代移民來說,第二代猶太人顯然不大遵循猶太傳統。赫索格作為一個在美國社會成長的猶太人,傳統的猶太價值取向不再是他的歸宿,這一點可以從他選擇的女性來窺探一二。在小說中出現的四個主要女性角色個性特征都大不相同,女性成為他內心欲望的象征符號,他的情感在一個個不同的女性當中游蕩。
第一任妻子戴西是相當傳統的猶太女子,赫索格也說“她是個比較冷靜、比較規矩的舊式猶太女子。”對任何事情都可以安排得井井有條。“我把全副精力都投進思想史里去了,雖然也是雜亂無章的。赫索格說他忙得不可開交,沒有空,她也就信了他的話,當然既為人妻,就有責任竭力支持自己的丈夫。”盡管她處處以丈夫為中心,但是婚姻以赫索格出軌結束。
第二任妻子馬德琳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新式現代女性。馬德琳的家庭是傳統的猶太家庭,但是她十分厭惡父親的大男子主義,以及母親為了丈夫和家庭失去自我的行為。母親丹妮受盡了父親的欺凌,但是離婚后還為了前夫的藝術事業而犧牲自己,并且始終保持著對丈夫的忠貞。馬德琳不想成為一個傳統猶太女人,不想整日圍繞在家庭事務中,不想過傳統猶太生活。在書中,她對赫索格說:“你要的那種環境,你一輩子也別想有,那種環境十二世紀有過,你一天到晚嚷著要你的那種老家,說什么廚房的桌子上蓋著油布,還放著你的拉丁文書。”所以,她有一段時間改信了天主教,她不甘于平庸,所以想學習課程拿到博士學位。她關心物質享受,購買孕婦服就花掉了500美金,但是赫索格對她的行為十分不滿,并且諷刺她:“你要生個路易十四出來嗎?”赫索格不能夠理解馬德琳的需求和痛苦,他扎進書堆里,對馬德琳的情感不聞不問,并且處處限制她的生活。隨著自我意識的高漲,馬德琳毅然決然地同赫索格離了婚。赫索格對馬德琳的心態又愛又憎。一方面對于馬德琳的能力大加贊賞,另一方面,書中利用馬德琳情感表達的空缺,赫索格將馬德琳妖魔化,塑造成一個貪婪虛榮、一無是處的女人。
情人園子是一個日本女人,她如同神秘、縹緲的東方。她為赫索格準備明蝦、生魚片、為赫索格沐浴更衣。她處處為赫索格著想,不求回報,不需要赫索格為她提供金錢,只是想赫索格能夠經常陪伴她,甚至赫索格拋棄園子,選擇馬德琳之后,她雖然難過,但仍提醒赫索格小心馬德琳。赫索格一直對園子戀戀不舍。雖然最后分手了,但是赫索格始終回憶著她。
雷蒙娜同上述三個女性不同的是,她不再是單一的猶太、美國或者東方的。正如書中描寫的,蕾蒙娜的“身世經歷具有國際性:西班牙、法國、俄國、波蘭和猶太”。雷蒙娜在紐約有一家花店,經濟上并不依附于赫索格,同時體貼又有趣。赫索格不滿足于完全歸順于他的猶太妻子,對于馬德琳這樣的新式女性又無法掌控。最后,雷蒙娜似乎是他情感的歸宿,赫索格在路德村等待著雷蒙娜的到來。
(三)意識流浪
小說中,意識流的創作手法展現了赫索格心理上的流浪。赫索格不停地給生者、死者寫信。在信中,他討論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沒有固定的主題和內容,思想意識雜亂無章地袒露在信件中。同時,貝婁頻繁地使用回憶的手法,在現在同過去的時間軸上滑動,通過追憶的手法而期望在過往歲月中重新找到真與美。
在坐出租車的時候,赫索格聯想到小時候去度假的場景。“不管怎樣,度假應該以坐火車開始。他小時候在蒙特利爾就是這樣。他們一家大小乘有軌電車先到大樹桿火車站。隨身帶去一只用木片編成的籃子,籃子里裝著父親喬納·赫索格從雷切爾市場買來的廉價梨子,上面滿是黃蜂咬過的斑點,熟透得快爛了,但奇香撲鼻。赫索格的父親坐在火車車廂陳舊的綠色粗毛墊上,用他那把俄國制的珍珠鑲柄小刀削著梨子。他削得薄,旋得快,切得勻,真是歐洲人的手藝。”
在中央火車站擁擠的人群里,赫索格又想起母親,想起當時她怎樣用唾液沾濕手帕給他擦臉。那年夏天,在加拿大那個空蕩蕩的火車站里,母親手帕上唾液的味道充滿了他的腦海。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說:“小說探索時間:馬塞爾·普魯斯特探索無法抓住的過去的瞬間;詹姆斯·喬伊斯探索無法抓住的現在的瞬間。”現實時間稍縱即逝,從不停留,想象力也無法重新構建被遺忘的瞬間。回望過去的時間,記憶也無法準確地抓住它,只能夠描摹出大致輪廓。面對令人崩潰的現實,回憶是一種暫時的跳脫,是一種暫時的安慰。而過去的種種已經成為過去,無法再次占有。回憶變成了模糊的輪廓,現在的生活則無法控制,赫索格在心理上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四)小說的敘述
小說敘述采用了復合視角。例如:“我非做赫索格不可。除我之外,再沒有人可做赫索格。哭過之后,他還是得回復‘故我,把‘故我應做的事做完。你竟有這么一個妙主意——第三位赫索格夫人!”
這里使用了三種視角。“我”是主要人物赫索格第一人稱顯身敘述,“你”是第二人稱顯身敘述,“他”是第三人稱隱身敘述。視角之間跳躍轉換,形成了一種網狀的復合視角。這種視角的跳動同赫索格的流浪狀態形成一種有趣的對應關系。
二、流浪的猶太人
赫索格全名是摩西·埃爾凱納·赫索格。關于赫索格名字的來歷,學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說起摩西,大部分人想到的仍是圣經中帶領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英雄。圣經中摩西經歷了許多磨難。他在蘆葦中被法老的女兒救起,之后應耶和華的要求帶以色列人出走埃及。出走埃及的路上,由于曠日持久的艱辛,以色列人對上帝缺乏信心,在西奈曠野流浪了四十年,才到達應許之地。
兩個摩西有很多異同。圣經中的摩西是一個拯救者,而赫索格是無法應付現實的人。相似之處有兩個人都受了女性的幫助以及兩個人都經歷了漫長艱苦的流浪。小說中有很多細節也提示了兩個人之間隱隱約約的聯系。例如,和雷蒙娜共進晚餐時,赫索格聽著埃及音樂,這使他想到“我過去的歲月,年湮日秒,真像比埃及的歷史還要久遠”。吹奏雙簧管:“小客廳里很悶熱,空氣壞透了,由于赫索格和他吹奏的雙簧管(reed),那圣歌中吸入了一股猶太人的哀傷。”這種情景讓人聯想起藏于蘆葦(reed)中的嬰兒摩西。
摩西作為猶太人的英雄,他的流浪就是猶太人的流浪。歷史上猶太人有多種稱謂:希伯來人、以色列人、猶大人、猶太人。由于歷史上猶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固有無根的猶太人之稱。整理猶太人歷史上的大事件,人們會發現猶太人一直在尋找他們的應許之地。公元前約1700年:猶太民族的祖先亞伯拉罕在迦南地定居。后因饑荒古以色列人遷徙到埃及;公元前約1350年,摩西帶領古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在西奈山接受“摩西十戒”,猶太教誕生。公元前1300-公元前1250年,古以色列人返回迦南地,并在此地定居;后來,猶太人雖然建國,但是后被別國消滅;132年古代猶太歷史終結,進入流散時期。
猶太人離開迦南地區以后,其足跡幾乎遍及歐洲各國。伴隨著猶太人的到來,歐洲各國的排猶運動產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猶太人遭到納粹的大屠殺。《圣經·創世紀》中,上帝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這里本指的是希伯來人越過幼發拉底河到迦南地去,但是這一歷史經驗成為希伯來人恒定的生存經驗。不停尋找適宜棲身之所成為猶太人的終身事業。
諾貝爾獎對貝婁的獲獎陳述是:“他的作品中融合了對人性的理解和對當代文化的精湛分析。”猶太人、非猶太人都可以在赫索格中找到共鳴。通過赫索格這個人物,猶太人歷史經驗同現代相遇了,轉世再生的古老神話轉化成為一種小說技巧。其流浪史升華為一種現代全人類的生存狀態。貝婁的第一部小說的名字Dangling Man很好地描述了現代人的狀態,即一種晃來晃去、沒有支點的懸掛狀態。
三、懸掛的現代人
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說:“世界是價值(源于中世紀的價值)貶值的進程,這一進程綿延現代的四個世紀是現代的本質。”當上帝死了,價值需要重估,人還能以什么為依靠。
在許多現代作家那里,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現代人面對價值貶值的狀態。在卡夫卡那里,人們看到強大的外界對人的壓迫(《審判》),看到人對外部世界的無能為力以及人被拋來拋去的命運(《美國》),普魯斯特那里是無法抓住的過去(《追憶似水年華》),在喬伊斯那里是無法抓住的現在(《尤利西斯》)。對于現代人與其所處世界的可能性,猶太作家似乎更為敏感。猶太民族經歷了上千年的流浪,從一開始就是被命令到另一個地方去,這種歷史經驗伴隨了猶太人兩千年。例如,卡夫卡作為一個猶太作家,其作品猶太因素已經比較少了,但是他本人及其作品也呈現了一種生存的可能性,一種無歸宿的懸掛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僅適用于猶太人,同樣幾乎永恒地伴隨著人類。其小說主人公也面臨著和卡夫卡一樣的困惑:《城堡》主人公K是想方設法進入城堡而不得的土地丈量員;《美國》卡爾·羅斯曼迷失在陌生的陸地上,無法到達心中的目的地。W.H.奧登說過: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貝婁的小說《晃來晃去的人》(Dangling Man),這個名稱很好地概括了以卡夫卡為代表的現代人類命運,即像一個被懸掛的小球一樣,晃來晃去,沒有支點,沒有歸宿。
猶太人深厚的文化背景在索爾·貝婁的作品中起著連接的作用。赫索格成為了一個橋梁,從他身上,人們不僅可以窺探到往昔猶太歷史,同時也能看到現代人的生存。索爾·貝婁將古老的猶太歷史同現代人生存連接在一起,從而使單一的猶太流浪歷史經驗上升到整個人類的生存經驗。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作者簡介:李京(1992-),女,河北保定人,文學碩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方向:比較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