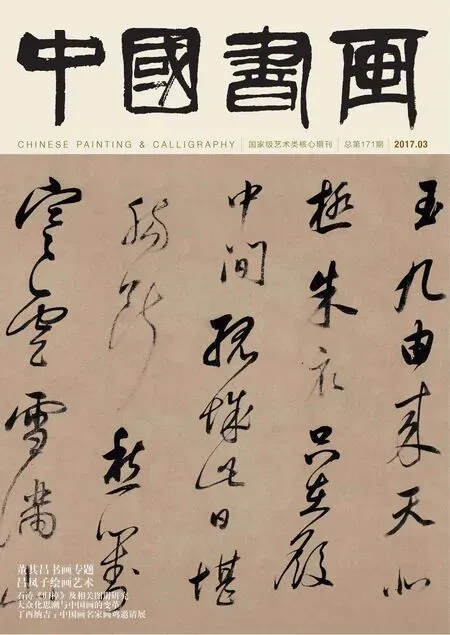寫意人物畫的線條語言及其表現力
◇ 孫棋
寫意人物畫的線條語言及其表現力
◇ 孫棋

[明]張路 騎驢圖卷 29.8cm×52cm 紙本設色 故宮博物院藏
“線條”在中國畫里是一種極為重要的藝術語言。中國畫崇尚“以線造型”,從遠古時期開始,線條就是人類進行空間想象的重要手段。線條通過筆墨的干、濕、粗、細等方式給予物象以內涵,并深化了畫家的情感。線條語言貫穿于中國繪畫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原始的樸拙線條,發展到元代的書寫性和“似是非是”的線條,寫意人物畫中線條的運用體現了厚重而蒼茫的歷史,蘊含著深刻的人文精神。可以說,在寫意人物畫中,線條語言是繪畫中藝術表現語言的主導。
《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在繪畫中的陰陽說體現為線條的干濕、疏密、畫面布局的“計白當黑”。線條的疏密濃淡形成了動與靜、剛與柔的辯證統一,也是傳統哲學中陰陽關系最普遍的表現,也形成了繪畫中形式的美。一幅畫若只有陰柔的線條,則就會讓所表達的意象失去力量的美,而若只有陽剛的線條則會讓線條缺乏形式的美感。因此,只有剛柔結合,才能讓畫面更豐富,更具有表現力。
1.線條與畫面骨架
中國畫對畫面骨架的構造尤其注重,對于骨架結構常運用線條或者線性墨塊進行組合。線條構造骨架要充分利用和最大限度地發揮“以線造型”的能力,把握描繪物象形象的特征。在畫面結構內部,運用不同長短、虛實和寬窄的線條來表現。從線條本身來看,不同線條的用途有著明顯差別:實線、長線及單線主要用來勾勒框架,用于主干線和外部輪廓的展現;虛線和短線則主要填充內容,用于分支線和內部輪廓的描繪。兩種線條在畫面中可以看作是從屬關系,通過疏密聚散、穿插隱現等結構方式,發揮各自的優勢。畫面骨架由線條經過組合形成墨塊建造而來,是通過線型語言構建的畫面輪廓,這就要求線條在畫面中以筆墨團塊的形式存在。
此外,為了使欣賞者獲得立體厚重的視覺感受,畫面中出現光影的效果,從本質上而言也是線條的靈活運用。不同的線條在排列組合后,形成新的單元基本形,這些基本形在二次組合后構成墨塊,由墨塊間的明暗對比產生視覺引導,使之成為骨架結構之外的光影或其他效果。在完整的畫面中,兩種表現形式通常同時存在,或是獨立出現,或是相伴而生,不同的組合方式提高了畫面本身的藝術性和觀賞性,使畫面成為可供觀賞,同時也能激發想象的藝術品。
2.線條對人物形體的刻畫
對于人物形體的勾勒還需仰仗線型語言,在人物寫生中,線型元素的作用就極其重要。首先要運用線條來塑造人物的外部輪廓,以此來完成人物造型骨架搭建的第一步。外部輪廓是所形體描繪的基礎,它既是連接的橋梁,又是區分的標志。所謂連接的橋梁是其勾畫了整個形體結構,區分的標志指的是外部輪廓是區分形體的各個部位和塊面內部結構的重要元素。輪廓線在畫面中有著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筆墨必須空靈善變,在不同場景下,通過線條骨力的凸顯或隱匿區分各個區位。同質同體輪廓線的構造可以借鑒西洋繪畫中的光影表現法,將線條通過分段的形式實現各個部位和內容的區分。例如,在毛皮帽子的外輪廓構建中,為了強調帽子在光線下的光影效果,將帽子分為三部分表現:其一是頂部,頂部屬于受光部位,應用細線或稍粗的線條表現光線效果;其二是底部,底部屬于背光部位,應用稍粗或稍細的線條表現;其三是側面,側面能夠反射光線,應用不連續的短線表現質感。三個部分對線條的使用將光線效果和光影效果直觀地表現出來。在人物形體的構建中,頭部所包含的元素較多,要注意根據不同情況表現五官或毛發。
水墨人物畫更加關注運用線性墨塊來表現人物形象。線性墨塊也稱筆墨團塊,是通過筆墨表現出線的流向、形態、明暗等特點,從而反應人體各局部部位間的輕重、粗細、明暗等內在關系。借助線性墨塊表現變化強調的是墨塊間的排列組合關系,經由墨塊的虛實、明暗甚至留白等不同方式,使得人物形體自然具有生命力,從而完成人物形體的構建。
此外,主干線與支干線的搭配以及團塊與團塊間的組合也是展現畫面立體、明暗、形狀及肌理等特性的重要方式。通過搭配與組合,并與畫面的整體布局相結合,使得畫面更富于藝術表現力。當力透紙背的墨線與墨色內外合一,藝術家們所要刻畫的形體就會由內而外,在厚重的筆墨之中透出一種秀氣、靈氣和骨氣。
3.寫意人物畫線條的書寫性
中國畫具有的重要特征是“以書入畫,以線造型”。因此它強調書法精神,強調與書法用筆的關系。“書畫同源”就是強調書法精神的重要性。書寫性也是中國民族精神中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
筆墨造型是中國人物畫的突出特點,也是中國人物畫線條語言的主要表現形式,它體現了造型與用筆合一的美學原則。中國書畫均以“線”為基本造型手段,而線條藝術中“骨力”來源于書法,這種筆法使得中國畫線條有了鮮明的節奏感、韻律感和廣闊的表現空間。歷史早期繪畫中線條的粗細變化較小,如楚墓帛畫與篆書的形式是統一的。隸書的出現使得畫中也講究頓挫和轉折。顧愷之的線條被稱作“高古游絲”描,這與魏晉時出現的草書密不可分。吳道子的蘭葉描體現了盛唐書法的突破,畫中的線條也有了粗細變化。到寫意人物畫的產生及繁榮,“元四家”“明四家”等直至晚晴時期的吳昌碩、任伯年等更是將書寫性發揮到了極致。尤其是任頤的寫意人物畫更是達到了“形隨線生”“線”“形”兩忘的統一和融合境界。
4.寫意人物畫線條的意向性
中國傳統人物畫中,象征和寫意是其基本特征,用主觀想象代替真實視覺是其區別于西方繪畫寫實性的主要因素,它也體現了中國畫的詩情畫意。中國特有的筆墨等繪畫基本工具材料,也為線條造型的抒情達意提供了空間。“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國畫的表現手法。它并非照搬自然世界的客觀,而是加入了創作者的主觀想象,即在客觀事物進行還原的基礎上寄予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使得線型語言具有精神性和意向性。
寫意人物畫開拓者梁楷的《李白行吟圖》是線條語言意象化的范本,也是水墨人物畫的經典之作。畫家通過對線條流暢的書寫及墨色暈染的巧妙運用,使這位“新詩成后自長吟”的詩人在筆墨的搭配和揚灑中生動形象地呈現。尤其是對“李白行吟”這一動態的描繪,作者采用了墨色的變化及筆法技藝。在詩人的鞋子處,作者的用墨通過濃淡的變化展現了詩人前行的動態,加上用筆方向的變化及對服裝中長袍的垂拂曳引形象運用線條的勾勒,使得畫面靜中有動,栩栩如生地展現了人物的神態,傳神地體現了詩人的氣韻。在另一幅傳世之作《潑墨仙人圖》中,線型語言展現了作者自由奔放、超凡脫俗的境界。寬松的粗麻僧衣運用禿筆并無造作涂畫出澀硬的線條,而五官和手臂的線條則用圓潤飽滿的濕筆平緩勾勒,而劈刀的線條剛勁細長,竹竿則用沒骨線條淡墨掃出。身體部位不同,線型語言的速度和力度感也不徑相同。梁楷對于線條語言精準的運用不僅是對客觀意象的再現,更是畫家對于禪宗思想的頓悟。不同時期繪畫藝術有著其鮮明的個體特征,線條語言在筆墨的演變過程中傳達了作者思想及畫作中的豐富內涵,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文人對社會的思考。
責任編輯:歐陽逸川

[唐]伏羲女媧圖軸 220cm×80.9cm 絹本設色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 中國書畫的其它文章
- 楊中良
- 以意運法 寫心為尚
——陳良敏的繪畫藝術 - 專業的意義
- 筆墨當隨時代
- 丁酉納吉
——中國畫名家畫雞作品邀請展 - ——從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仿黃公望山水》卷說起">"愉庭"與過云樓顧氏
——從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仿黃公望山水》卷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