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上的創(chuàng)造和思考
劉金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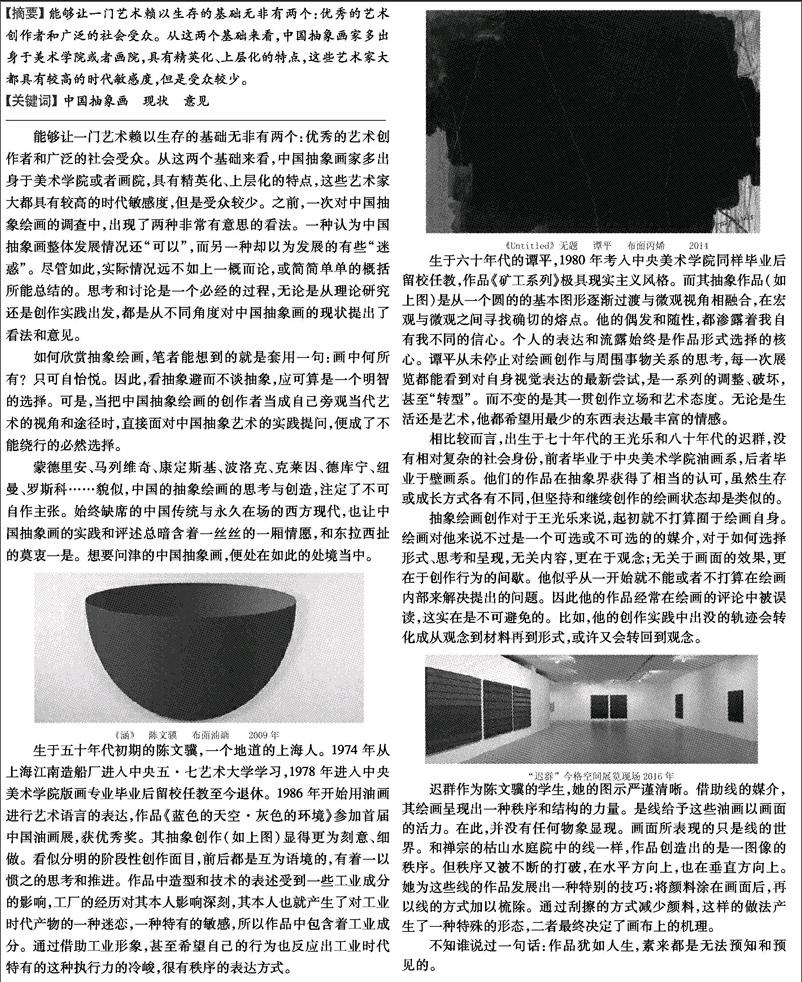
能夠讓一門藝術(shù)賴以生存的基礎(chǔ)無非有兩個:優(yōu)秀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和廣泛的社會受眾。從這兩個基礎(chǔ)來看,中國抽象畫家多出身于美術(shù)學院或者畫院,具有精英化、上層化的特點,這些藝術(shù)家大都具有較高的時代敏感度,但是受眾較少。
中國抽象畫現(xiàn)狀意見
能夠讓一門藝術(shù)賴以生存的基礎(chǔ)無非有兩個:優(yōu)秀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和廣泛的社會受眾。從這兩個基礎(chǔ)來看,中國抽象畫家多出身于美術(shù)學院或者畫院,具有精英化、上層化的特點,這些藝術(shù)家大都具有較高的時代敏感度,但是受眾較少。之前,一次對中國抽象繪畫的調(diào)查中,出現(xiàn)了兩種非常有意思的看法。一種認為中國抽象畫整體發(fā)展情況還“可以”,而另一種卻以為發(fā)展的有些“迷惑”。盡管如此,實際情況遠不如上一概而論,或簡簡單單的概括所能總結(jié)的。思考和討論是一個必經(jīng)的過程,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創(chuàng)作實踐出發(fā),都是從不同角度對中國抽象畫的現(xiàn)狀提出了看法和意見。
如何欣賞抽象繪畫,筆者能想到的就是套用一句:畫中何所有?只可自怡悅。因此,看抽象避而不談抽象,應可算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可是,當把中國抽象繪畫的創(chuàng)作者當成自己旁觀當代藝術(shù)的視角和途徑時,直接面對中國抽象藝術(shù)的實踐提問,便成了不能繞行的必然選擇。
蒙德里安、馬列維奇、康定斯基、波洛克、克萊因、德庫寧、紐曼、羅斯科……貌似,中國的抽象繪畫的思考與創(chuàng)造,注定了不可自作主張。始終缺席的中國傳統(tǒng)與永久在場的西方現(xiàn)代,也讓中國抽象畫的實踐和評述總暗含著一絲絲的一廂情愿,和東拉西扯的莫衷一是。想要問津的中國抽象畫,便處在如此的處境當中。
生于五十年代初期的陳文驥,一個地道的上海人。1974年從上海江南造船廠進入中央五·七藝術(shù)大學學習,1978年進入中央美術(shù)學院版畫專業(yè)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今退休。1986年開始用油畫進行藝術(shù)語言的表達,作品《藍色的天空·灰色的環(huán)境》參加首屆中國油畫展,獲優(yōu)秀獎。其抽象創(chuàng)作(如上圖)顯得更為刻意、細做。看似分明的階段性創(chuàng)作面目,前后都是互為語境的,有著一以慣之的思考和推進。作品中造型和技術(shù)的表述受到一些工業(yè)成分的影響,工廠的經(jīng)歷對其本人影響深刻,其本人也就產(chǎn)生了對工業(yè)時代產(chǎn)物的一種迷戀,一種特有的敏感,所以作品中包含著工業(yè)成分。通過借助工業(yè)形象,甚至希望自己的行為也反應出工業(yè)時代特有的這種執(zhí)行力的冷峻,很有秩序的表達方式。生于六十年代的譚平,1980年考入中央美術(shù)學院同樣畢業(yè)后留校任教,作品《礦工系列》極具現(xiàn)實主義風格。而其抽象作品(如上圖)是從一個圓的的基本圖形逐漸過渡與微觀視角相融合,在宏觀與微觀之間尋找確切的熔點。他的偶發(fā)和隨性,都滲露著我自有我不同的信心。個人的表達和流露始終是作品形式選擇的核心。譚平從未停止對繪畫創(chuàng)作與周圍事物關(guān)系的思考,每一次展覽都能看到對自身視覺表達的最新嘗試,是一系列的調(diào)整、破壞,甚至“轉(zhuǎn)型”。而不變的是其一貫創(chuàng)作立場和藝術(shù)態(tài)度。無論是生活還是藝術(shù),他都希望用最少的東西表達最豐富的情感。
相比較而言,出生于七十年代的王光樂和八十年代的遲群,沒有相對復雜的社會身份,前者畢業(yè)于中央美術(shù)學院油畫系,后者畢業(yè)于壁畫系。他們的作品在抽象界獲得了相當?shù)恼J可,雖然生存或成長方式各有不同,但堅持和繼續(xù)創(chuàng)作的繪畫狀態(tài)卻是類似的。
抽象繪畫創(chuàng)作對于王光樂來說,起初就不打算囿于繪畫自身。繪畫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可選或不可選的的媒介,對于如何選擇形式、思考和呈現(xiàn),無關(guān)內(nèi)容,更在于觀念;無關(guān)于畫面的效果,更在于創(chuàng)作行為的間歇。他似乎從一開始就不能或者不打算在繪畫內(nèi)部來解決提出的問題。因此他的作品經(jīng)常在繪畫的評論中被誤讀,這實在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出沒的軌跡會轉(zhuǎn)化成從觀念到材料再到形式,或許又會轉(zhuǎn)回到觀念。
遲群作為陳文驥的學生,她的圖示嚴謹清晰。借助線的媒介,其繪畫呈現(xiàn)出一種秩序和結(jié)構(gòu)的力量。是線給予這些油畫以畫面的活力。在此,并沒有任何物象顯現(xiàn)。畫面所表現(xiàn)的只是線的世界。和禪宗的枯山水庭院中的線一樣,作品創(chuàng)造出的是一圖像的秩序。但秩序又被不斷的打破,在水平方向上,也在垂直方向上。她為這些線的作品發(fā)展出一種特別的技巧:將顏料涂在畫面后,再以線的方式加以梳除。通過刮擦的方式減少顏料,這樣的做法產(chǎn)生了一種特殊的形態(tài),二者最終決定了畫布上的機理。
不知誰說過一句話:作品猶如人生,素來都是無法預知和預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