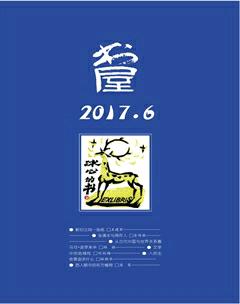書屋絮語
有緣得見法國學者師覺月1944年出版的《中印文化關系千年史》,此書為非賣品。開首一段就頗讓人動容:“古代人生活的世界通常不像我們所想的那么大,自從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后,東方與西方的分野便逐漸淡化。海上、陸上交通也開始日益興盛、固定,商業和貿易的交流為東方和西方帶來了繁榮,文化的交流也促進了東方和西方文明的進步。”“在這種大交流的背景下,印度所發揮的作用其實并不低微。……因此,從某種特定的角度來看,印度的歷史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須臾不可分。”古代希臘—印度文明是與中華文明相互交流、共同推進的重要力量,不僅僅是佛教的傳輸,還有古希臘文化、建筑等的共生共榮。反之,在遠古時期,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都在不同的層面影響著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塑造,所謂東學西漸,在歷史上肇其始。十八、十九世紀,又是一次,歐洲的啟蒙運動受其益,可以說改變西方的歷史方向。及至近代,印度哲學家維韋卡南達等思想再次喚醒了西方人的靈魂,它與中國古典哲學相呼應,直指世界和平共處,天下一家。
盛唐時期,是中國和印度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最為密切的時期:“在中國的大城市里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印度人,其中有很多都是商人或是普通的觀光者,也有相當多的人是佛教僧人和學者。”宋朝時期,隨著佛教的衰落,“曾經使印度與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建立緊密聯系的力量也不再發揮任何作用”。盡管如此,中印文化的交流從未斷線,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再度興盛起來,當前印度各著名大學的中國學院或漢語系就是明證。
收到岱峻贈送的新著《弦誦復驪歌——教會大學學人往事》,“展示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教會大學的幾度轉折經歷,尤其是一代學人的精神氣質和人世遭際”。同樣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中印文化交流如出一轍。從歷史上來看,這個時間點無疑是文化的關鍵點,意義與價值尤為突出。
當編輯最大的好處,莫過于可以收到作者贈送的著作,與作者共享喜悅,也將閱讀視野及物又及人。韓秀《翻動書頁的聲音》和王曄《看得見的湖聲》二本書,一本是新著,一本是舊著,都與聲音息息相關。一個是聽得見,一個是看得見,實際上都是生活的狀態中的具體體現;一個是在臺北敦化圓環誠品書店,凌晨二點,一位年輕讀者翻動書頁的聲音;一個在瑞典奧斯南湖邊上的聲音。無論是聽得見,還是看得見,那個聲音一直在那兒,需要我們屏息以待。
而唐玄奘騎著的那匹白馬的嘶鳴,我們還能聽得見或者看得見嗎?或者恒河邊泰戈爾的朗誦聲?或者馬可·波羅來華的足屐聲?抑或容閎在耶魯的讀書聲?我們當用心聆聽歷史的聲音,那些悠長而回蕩在浩瀚的天空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