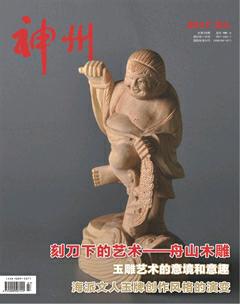黃賓虹筆墨精神中的不可學性
摘要:筆墨不是以模仿物象為創作目的,而是作為藝術形式表演語言,表達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中獨有的幽遠意境。能將“筆墨”發揮到如此高超境界的,當中國繪畫史上黃賓虹莫屬,在藝術上堅守本土文化立場,堅持從山水畫中尋找超越的動力,發掘筆墨語言的超長滲透力。筆墨對于心理情感因素的依賴,使他的藝術風格執著走上一條表現道路。筆墨點線勾擦、情感交織,形成高低起伏音樂性。他以獨有筆墨節奏和韻律,充分表現對客觀社會生活的主觀能動反映,營造出崇高、渾厚又不失細膩的山水境界。黃賓虹在晚年的山水畫中,筆墨已經是無跡可尋,所表現的物象也是超乎于自然,這就決定了他的可學性與不可學性、可取性與不可取性。
關鍵詞:筆墨精神;滲透力;氣韻;意;法;不可學性
一、黃賓虹“五筆七墨”在中國傳統繪畫中的革新
筆墨表達出的藝術效果所牽引出優雅、纖細、崇高、偉大等種種感受,是藝術家的基本功力,也是綜合素質、氣質修養的一種反映。歷代畫家極其重視“筆墨”二字,五代荊浩在其著作中論述道:“隨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墨暈章,興我唐代。”[1]南朝蕭繹[2]也曾提出“筆精墨妙”的原則。筆墨不是以模仿物象為創作目的,而是作為藝術形式表演語言,表達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中獨有的幽遠意境。作為中國畫審美標準之一的筆墨,它的價值、意義和地位隨時間發展爭議日趨激烈。那么能將“筆墨”發揮到如此高超境界的,當中國繪畫史上黃賓虹莫屬。 “國畫民族性,非筆墨無以見”這是他對筆墨的精神態度,即在藝術上堅守本土文化立場,堅持從山水畫中尋找超越的動力,發掘筆墨語言的超長滲透力。
(一)黃賓虹山水畫中用墨七法
“畫重蒼潤,蒼是筆力,潤是墨彩,筆墨功深,氣韻生動。”[3]確是如此,在他晚期山水作品中“山不山,水不水,樹不樹,屋不屋”,即“以不似之似為真似”,創作中對客體更多發揮想象力,更廣泛重視筆墨對心靈的直接造就作用。黃賓虹從龔賢[4]畫中的“點”領悟到“點墨積法”,以此總結成“七墨法”,較出眾和具研究價值的有破墨法、積墨法和宿墨法三種。
破墨法有濃淡、水墨、墨色、橫直要素間互破,效果豐富而章法嚴謹規整。淡破濃是先濃墨后破以淡墨,濃破淡則反之,其余破法亦如此。橫直互破說明除濃淡變化外,用筆方式方向也會影響筆墨效果。
從淡墨遞增到濃墨,墨中有墨,墨不礙墨,是他山水畫中常用的積墨法,這是對超自然事物的反思,在象征與聯想中找到潛意識中事物本質。《雨霽云深》、《摩崖看古篆》那渾厚、滋潤、華麗畫風,通過極濃稠筆墨使整個畫面充滿敦厚的視覺效果,以增強層次感和立體感。這種表現手法不僅能嫻熟駕馭繪畫工具性能,還能突破傳統程式束縛,使情感釋放得到一種新的載體形式。
宿墨法是他晚期畫作中及其大膽的墨法。宿墨即隔夜墨,滲透在紙上稍黑、干得快,筆筆分明且難控制。山水畫《山居曉望圖》是宿墨最具代表性作品。黃賓虹曾說:“畫用宿墨,其胸次必先有寂靜高潔之觀,而后以幽淡天真出之。”這說明藝術家真情的自然流露,與他審美經驗、筆法技巧緊密相連,這些潛意識無法預判的水墨痕跡,伴隨生命在時空中一起流動,是生命力無限延展的象征。
(二)黃賓虹山水畫中用筆五法
在黃賓虹作品中,可以探索出他對含蓄內斂而不外露的用筆執著追求,遵循“渾厚”、“剛勁”的用筆原則,以至提出新用筆方式和評判標準,稱之為“五筆”:平、留、重、圓、變。
平,追求用筆力道均勻穩健且筆筆送到,切記忽提忽壓,或一味地提、一味地壓,《西橋煙雨》大筆橫掃描繪雨中朦朧景色,筆法力度躍然紙上;留,線條沉著而含蓄,能主觀控制偶發性產生,隨時收筆、隨心所欲,使自我生命的感性直覺與理性安排達到簡單透明境界;重,用筆有力量,勾勒出線條挺拔、敦實、厚重,切記線條軟弱無力飄于紙上;圓,保持中鋒用筆,表現出線條圓潤、挺拔、飽滿、富有彈性;變,用筆豐富因勢而變,黃賓虹山水畫作品《深山夜話》、《九華山》可領悟他用筆靈巧生動,根據不同表現對象或肌理質感,用筆快慢、方圓、濃淡、橫直,產生出悠遠的浪漫意境和豐富的思想情感。
二、黃賓虹筆墨中的意與法
筆墨對于心理情感因素的依賴,使他的藝術執著走上一條表現道路。筆墨點線勾擦、情感交織,形成高低起伏音樂性。他以獨有筆墨節奏和韻律,充分表現對客觀社會生活的主觀能動反映,營造出崇高、渾厚又不失細膩的山水境界,更是對傳統和當代精神完美融合,進而對社會屬性審美價值深度挖掘。
黃賓虹深刻發展中國山水畫筆墨的“意”與“法”理論。“意”、“法”與筆墨的關系應是章法之外又在章法之中,以精妙筆墨技巧去“達意”而“合法”。黃賓虹認為自然就是法,即山水畫是寫自然之法、自然之性,進一步延伸為心靈之法。這里營造了“非真實”狀態,達到更貼近生活的“真實”,把現實化自然轉變為情感化自然,將內與外、天與人、心與物融為一體,不拘泥于畫面的“形似”和“筆到”,達到至真至美的心齋與坐忘之境。
“氣韻”最初在中國傳統繪畫中作為筆墨精神最高層次,但謝赫提出“六法”中“氣韻生動”,才正式確立筆墨精神中的氣韻。黃賓虹就筆墨與氣韻的關系在《六法感言》作出精辟論述,他認為“韻由氣生”,“氣”至關重要,所以畫面理應追求虛與實、疏與密。虛實作為表現的重要手段,實在筆墨章法間,虛不全然。
三、總結
黃賓虹山水畫作品在體驗后加工、取舍和再創造,采取的表現手法和描繪對象是精神上、心性上屬靈事物,即他作品的生動主要來自筆墨上豐富而靈巧變化。黃賓虹晚年山水畫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筆墨已無跡可尋,所表現的物象超乎于自然,這就決定了他的可學性與不可學性、可取性與不可取性。
注釋:
①引用五代荊浩著作《筆法記》,為古代山水畫理論的經典之作
②梁元帝蕭繹,字世誠,小字七符,自號金樓子,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
③引用黃賓虹先生《自題山水》
④龔賢(1618-1689)明末清初著名畫家,金陵八家之一
參考文獻:
[1]《黃賓虹畫論》,云雪梅編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 《黃賓虹的繪畫美學思想》,郭因, 晉中師范高等專科學校,2002.
[3] 《黃賓虹全集》,黃賓虹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4] 《黃賓虹自述》,黃賓虹著,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胡晨,學校:湖北美術學院美術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設計藝術理論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