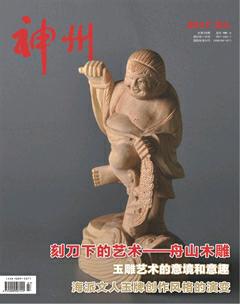《給WP》余光中李敖譯本對(duì)比分析
董婷?侯寶花
摘要:《給WP》為美國(guó)自然主義文學(xué)家與美學(xué)家喬治·桑塔耶納為悼念亡友所作的十四行詩,余光中和李敖先后都對(duì)組詩中的第二首進(jìn)行翻譯,但是譯本給人的感覺卻頗有差異。本文試圖從意象、美學(xué)及韻律三方面淺析兩個(gè)譯本各自的特色。
關(guān)鍵詞:意象;美學(xué);韻律
桑塔耶納曾是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的教授。他是一個(gè)向往自由,行為隨性之人。這首詩是其為悼念亡友所作,那種清凈與無奈的心情就更需細(xì)心揣測(cè)。李敖曾說,他當(dāng)初改譯這首詩的目的就是要挑戰(zhàn)余光中,并自覺無論是語言還是意境上自己都要稍占上風(fēng)。然而,讀者們的意見卻并未如此涇渭分明。兩個(gè)譯本究竟孰優(yōu)孰劣,不妨從意象、美學(xué)及韻律三方面探討一下。
1.意象
意象指對(duì)事物的感知在大腦中形成的表征。后來這一術(shù)語被引用到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語義描寫中,用來表示形成一個(gè)概念或概念結(jié)構(gòu)的具體方式。同一情景由于觀察方式和角度不同會(huì)在說話者的大腦中形成不同的意象,從而產(chǎn)生不同的表達(dá)方式。同樣,不同的句法結(jié)構(gòu)可以在受話者大腦中形成不同的意象,象征著不同的語義,并造成不同的理解。
在原文本中,作者寫到:“in the peopled forest of my mind, A tree made leafless by this wintry wind, Shall never don again its green array.”作者將生命中出現(xiàn)的人比喻成一片樹林,而這位友人的離去,就如同在寒風(fēng)中凋零的樹木,友人離世,恰如樹木再不回春。余李二人的譯本:“在我心里那人物的林中,一棵樹飄零于冬日的寒風(fēng),再不能披上它嫩綠的春裝。”(余譯)。“冬風(fēng)掃葉時(shí)節(jié),一樹蕭條如洗,綠裝已卸,卸在我心里。”(李譯)。很明顯余譯更尊重作者要表達(dá)的意境,但是若單純欣賞漢語,很難體味樹木和人之間究竟有何關(guān)系。而李譯則完全打破了原詩的意象和句法,將“冬風(fēng)”、“樹木”、“綠裝”、“凋零”這幾個(gè)關(guān)鍵詞語重新整合,雖然用詞講究也更符合漢語的表達(dá),但從中卻無處尋覓到原詩的影子。李敖曾說自己的這篇譯文乃是“運(yùn)用之妙存乎一心”,更是放言道:“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nèi),中國(guó)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只是漢語的使用即使再精妙,如不能很好地傳達(dá)原文,又怎能稱之為好的譯文呢?
2.美學(xué)
美學(xué)是研究主體與客體、藝術(shù)與現(xiàn)實(shí)的審美關(guān)系,同時(shí)也研究審美物件的內(nèi)容與形式以及形式間各部分的審美關(guān)系。翻譯美學(xué),從美學(xué)的角度研究翻譯,是運(yùn)用美學(xué)、語言學(xué)和文化學(xué)的基本原理來探討翻譯中語際轉(zhuǎn)換的美學(xué)問題。翻譯是審美主體通過審美中介,將審美客體轉(zhuǎn)換為另一審美客體的一種審美活動(dòng)。林語堂曾表述為“譯文須忠實(shí)于原文之神氣與言外之意。……語言之用處實(shí)不只所以表示意象,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之明達(dá),亦必求使讀者有動(dòng)于衷。”歸結(jié)起來,即是內(nèi)容美、形式美、簡(jiǎn)潔美和音樂美四方面。
原詩中第二節(jié)寫到“Chapel and fireside, country road and bay, Have something of their friendliness resigned;”承接上文,朋友的離去,使得教堂、爐邊、郊路和港灣也失去了友誼,將這些事物擬人化,說明懷念逝者的并非只有作者一人。余譯“都喪失些許往日的溫情”,李譯“情味都今非昔比”,余譯雖然語言沒有李譯生動(dòng),但是更為貼切,傳達(dá)出擬人之感,“往日的溫情”一詞更是給予讀者以回味和想象的空間。下一行“Another, if I would, I could not find,”作者要表達(dá)的是想要追尋除教堂、爐邊、郊路和港灣之外,曾和逝者有過記憶的場(chǎng)所,卻無處指認(rèn);又似乎是要找尋另一份如此真摯的感情,卻無果而終。余譯“另一個(gè),就如我愿意,也無法追尋,”雖有些晦澀,但是以尊重原文為主,而李譯“雖有余情”則似乎離題太遠(yuǎn)。“And I am grown much older in a day.”說明了失去這樣一位友人所帶來的巨大悲痛。這一句,兩個(gè)譯本各有特色。余譯“白發(fā)加長(zhǎng)”可以理解為,失去友人已是青絲變白發(fā),而無處可尋,使得悲痛更甚,白發(fā)加長(zhǎng)。李譯“不知老了幾許”,將那種無奈和悲涼表達(dá)的淋漓盡致,也更符合漢語的表達(dá)。
第三節(jié)是對(duì)逝者品質(zhì)的評(píng)價(jià),用語客觀而平淡。兩個(gè)譯本差異不大。最后兩句的翻譯,李譯要更為出色一些,“你帶走的我,還是我留下的你”,更為浪漫,也帶來更多想象的空間。
3.韻律美
韻律美是詩歌區(qū)別于其他文學(xué)體裁的特質(zhì)。詩歌正是以富有音樂性的節(jié)奏和韻律,來對(duì)粗硬的、強(qiáng)烈的內(nèi)在情感實(shí)施有效的美學(xué)控制,使情感的傳遞更加溫和完美。
這首詩是傳統(tǒng)的十四行詩,講究的是格律形式中吟念出來的韻味與美感。由于語言體系的不同,如果譯者想要將這種韻味通過另一種語言傳達(dá)出來,完全保留原詩的音韻,必然處處受限。
本詩的韻腳為abba-cddc-effe-gg。余譯遵從原詩,依然譯為十四句,前三節(jié)尾字為:“亡,中,風(fēng),裝”“港,情,尋,長(zhǎng)”“藏,心,祥,命”,還是有意以英詩的格律為先,在無法追尋到每一個(gè)韻腳的情況下,退而代之以中國(guó)古詩的押韻規(guī)則aaba。而李敖則完全打破韻律的限制,長(zhǎng)短句隨心意搭配,以至于將十四行改成十三行,讀起來已不復(fù)商籟體詩歌的特色,順暢到似乎是在欣賞一首現(xiàn)代詩。
詩歌是表達(dá)個(gè)人感情的一種方式,表達(dá)的內(nèi)容較為隨意,悼亡詩的那份柔情就更加千回百轉(zhuǎn)。想要完全理解詩人的每個(gè)詞句,已是不易,再將其那種愁思用另一種語言淋漓表達(dá),更是難上加難。“信”、“達(dá)”、“雅”難全,成為一種必然。余光中先生,作為中國(guó)文學(xué)界的北斗和大師級(jí)人物,給后輩們開辟了道路,也幸好有李敖先生這類敢于挑戰(zhàn)的有才狂人,使得生活與文字交相輝映,相映成趣。
參考文獻(xiàn):
[1]劉宓慶.翻譯的美學(xué)觀[J].外國(guó)語, 1996, (5).
[2]林語堂.論翻譯[M]//林語堂名著全集:語言學(xué)論叢.長(zhǎng)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1995.
[3]熊麗君, 禹麗芳.認(rèn)知語法下的意象與意象意義[J].四川外語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06, (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