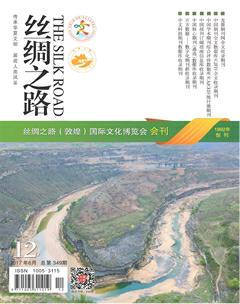唐代僧人泓師考述
劉慧婷

[摘要]唐代僧人泓師以占相堪輿之術游走于王宮貴胄之間,反映了利用俗世技藝推動佛教傳播與發展的特殊方式。僧人習學相面、堪輿等世間技藝,正是大乘佛教習學世間諸法觀念影響下的寫照。武周及中朝、睿朝二朝佛教的極盛發展為泓師的活動提供了客觀條件。正史與雜史、小說、僧傳等對其故事的不同記載反映了編撰者各自對佛教的認知態度,前者偏于經世致用,注重說教;后者的創作則以期通過神化和虛構使得人物更為鮮活和豐富。而泓師的相宅理論也確為中國古代堪輿之術的展現積累了寶貴資料,藉此我們得以從新的角度了解唐代民間的金玉文化、堪輿信仰。
[關鍵詞]泓師;相宅理論;堪輿信仰;民間信仰;符號文化
泓師是唐代武周、中宗、睿宗朝的僧人,目前學界尚缺少對之的專門研究。周勛初《唐人筆記小說考索》考證盧言和《明皇十七事》時對其人有所涉及,1閆淳純《唐代風水活動考》、關長龍《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王雪艷《唐人小說中的僧人活動》也提及了泓師相地的相關材料,2然均非專論。故而對泓師相關文獻的梳理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從正史、雜傳、小說、僧傳、類書等文獻出發,對泓師的生平及與他人交往情況進行考索,思考其占相堪輿之術背后的民間信仰與符號意義,進而探究其在歷史上的活動及對當時上層社會的影響。
一、泓師之生平
泓師,生平見于《舊唐書》卷191《方技·一行傳附》和《新唐書》卷254《方技·杜生傳附》。兩《唐書》記載較為簡略,僅言僧名(泓)、占籍(黃州,今湖北黃岡)。且《舊唐書》記載極簡,竟未具體言及交游之事。《新唐書》略述為張敬之預言、張說相宅二事,但未作評價(《舊》書尚言其“善葬法”)。
檢釋家史書,惟《佛祖歷代通載》于禪師一行后談及泓師,云:“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郎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兇亡不明驗。”3釋家對泓師生平詳細記載最早出自《宋高僧傳》卷29《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一》,相較正史,贊寧所記人物形象更為豐富:除言姓名、占籍,又對其性格(簡傲自持,而罕言語,語則瑰怪)、堪輿之術(頗善地理之學,占擇塋兆,郭景淳、一行之亞焉)、與官宦權貴(韋安石、張說、源乾曜等)之交往以及當時君主對其態度(中、睿朝皆崇重泓,號國師)等方面猶增筆墨。
國師為古代帝王給予學德兼備之高僧的尊稱。檢兩《唐書》武后至睿宗《本紀》《資治通鑒·唐紀》,未有名泓、號國師之僧人。然縱觀歷史,武后確對神秀、慧安等禪師待以師禮,使唐代佛教達于極盛。中宗時,“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瑰麗”;睿宗時,詔以“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道集”,釋、道并重。武后至睿宗時期,佛教獲得極大發展,統治者即便沒有像前朝那樣流露出過度的熱情,仍能夠深刻地意識到通過興建佛寺、舉辦法事等途徑,可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佛教維護封建統治的積極作用。
二、正史與雜傳之間
通過史書、筆記小說等文獻,筆者發現泓師與當時權貴重臣多有交往,并有諸多反映其占相、堪輿之術神奇靈驗的軼事。
材料分目 大致情節【錄文引最早記載】 最早記載【引自類書者以其所引之書著述時間最早者為參照】 其他記載
一、預言張敬之官三品、弟訥之病愈事 張敬之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于天官。僧泓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弟訥之,為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師指訥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間,必不墜矣。”皆如其言。 《大唐新語》卷5 《新唐書》卷254《杜生傳附浮屠泓傳》
二、預言李林甫居相十九年事 弘(泓)師過李林甫宅,謂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開元初,林甫官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于弘(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制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制,將毀其檐。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宣室志》卷10 《太平廣記》卷457〈李林甫〉、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3同引自《宣室志》
三、占王鍔、馬燧宅事 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永寧為王太傅鍔地,安邑為馬北平燧地。后王、馬皆進入宮,王宅累賜韓令弘、及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也;馬燧為奉誠園,所謂玉破而不完也。 《大唐傳載》 《太平廣記》卷497《王鍔》引《盧氏雜說》
四、占李吉甫、牛僧孺宅事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為玉杯,一破無復可全;金椀或傷,庶可再制。牛宅本將作大匠康?宅,?自辨岡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必引頸望之,宅竟為僧孺所得。李后為梁新所有。 《太平廣記》卷497《王鍔》引《盧氏雜說》 《地理新書校理》卷9、《長安志》卷8、《唐語林》卷7、《唐兩京城坊考》卷3同引自《盧氏雜說》
五、為張說相宅事 泓復與張燕公說置買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燕公:“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處三數坑,皆深丈余。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總填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燕公子均、垍皆為祿山委任,授賊大官。……(后)張垍長流遠惡處,竟終于嶺表;張均棄市。皆如其言。 《太平廣記》卷《泓師》條引《戎幕閑談》 《舊唐書》卷191《一行傳附泓師》《新唐書》卷240《杜生傳附泓師》
六、與韋安石相地事 泓師嘗語安石曰:“貧道近于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余畝,有龍起伏形勢。葬于此地者,必累世為臺座。”……安石妻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旦潛游郊野,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遂止。……(安石)曰:“舍弟韜,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韜竟買其地,葬中殤男,韜后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 《太平廣記》卷389《韋安石》條引《戎幕閑談》 《宋高僧傳》卷29《唐京兆泓師傳》
七、源乾曜偶得泓師所相之地得富貴事 (泓師)言于張說:“缺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于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為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缺門,先人尚未啟袝,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后泓復經缺門,見其地已為源氏墓矣,回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洼處本高,今則洼矣。合高處本洼,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中近二十年。 《太平廣記》卷389《源乾曜》條引《戎幕閑談》
綜上七事,泓師在唐代武后至睿宗朝上層社會的地位不言而喻。其軼事既部分見于正史,又有出自《大唐傳載》《大唐新語》《宣室志》《盧氏雜說》《戎幕閑談》等雜傳小說的部分,是唐代占相堪輿文化的側面展現。
雜傳之于正史、方志,確有虛構與事實的成分區別。就材料一而言,《新唐書》記張敬之為天官侍郎,而《新語》作春卿侍郎。按,唐睿宗光宅至武周神龍年間改吏部為“天官”,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屬正四品上。禮部在光宅至神龍間亦改稱春官、司禮。春官,或稱春卿,屬正四品下。雖均屬正四品,確有屬吏部還是禮部的分別。
再考《長安志》卷9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材料三王鍔宅確位于永寧坊,但屬西北隅而非東南隅,后李載義宅亦位于此;韓令弘即“韓弘”,宅在南永崇坊;史憲誠宅在南靖恭坊;惟李載義宅在永寧坊。又經《隋唐兩京坊里譜》考,“據1983年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永寧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魯家村北。”4
關于材料四,傅璇琮認為,《盧氏雜說》作者盧言,正處于牛、李黨爭之際,屬牛黨之人,泓師既存于中、睿朝,至憲宗時已過百年,當亡。故疑“泓師號李宅為玉杯,一破無復可全;金椀或傷,庶可再制”之言或為盧氏假托泓師之名而言他事,或為依“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之言杜撰而作,意在抨擊李黨。從這個角度來看,術士泓師在中晚唐仍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公信力。
至于材料七,依兩《唐書》《資治通鑒》等,源乾曜并未任監察御史,然于神龍中官殿中侍御史一職。監察御史隸屬察院,殿中侍御史隸屬殿院;言其于開元四年始為相,至開元十九年僅16年,故《戎幕閑談》所敘不盡為實。
三、占相堪輿的符號意義
從泓師與眾多權臣的交往中,我們得以知曉關于這位術士的更多軼事,藉此關注唐代僧人習學世間技藝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就占擇對象而論,材料一、七言及相術,二至七關涉堪輿。
(一)相面術
相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傳統的占卜形式,所相之人的面部氣色、人體姿態等即是相師占相理論中的符號組成,藉此近期的吉兇福禍、命運遠景等得以預測。敦煌文書中即有許負《相書》、面色圖等多個符號系統,它們的產生正是相師依據人體氣色形神等所書。泓師為張敬之、張訥之占相時蓋依據類似相書,然而《新語》《新書》均未提及具體的占相過程與理論。材料七中,泓師于簾間占視諸臣面相,僅以對言的形式言“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為禍”,“此人(源乾曜)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亦未及相面理論,這為泓師的占術更添神秘色彩,實際依據不得而知。
(二)金玉之說
泓師堪輿之法相比相術則有較多的理論闡述。除材料二李林甫居相十九年事未提及“居此貴不可言”的緣由外,三、四、五均涵蓋部分堪輿理論。材料三、四涉及泓師對地形吉兇的判斷。在其看來,宅居之地形為金盞,則吉;形為玉盞,則兇。“金盞破而成”,“玉(盞)破而不完”,此說以中國傳統意義上象征富貴吉祥的金玉二物為中心,顯示了“金”與“玉”在世間的符號意義。唐時,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榮,絲綢之路的便利促使杯盞裝飾亦吸收中亞及阿拉伯世界制作工藝,杯面雕琢人物紋、花鳥紋、云紋等,自然素雅而不失富麗堂皇。今未見有對唐代金盞(或言金杯)形制的具體描述,現代考古學中對杯的分類也很復雜,有些碗形的器物也稱為杯,這正涵蓋了材料三、四提及的“盞(淺而小的杯子)”“杯”“椀(碗)”三種形態。泓師認為,金、玉二盞對吉兇的影響與各自的特質直接相關。現有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團花紋金帶把杯、蓮瓣紋弧腹金碗、八瓣花形玉杯、忍冬紋八曲玉杯等供參考。
此外,《錄異記》卷8曾引泓師之語敘曹王皋墓事: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馬、磚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后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
埋葬于曹王皋墓中的石人、羊、馬、磚石、金器、玉器等物,表明唐代使用石、金、玉材質的器物作為隨葬品。敦煌文書S.2263記載有以石鎮墓的方法,“石碑去門十步,石羊去碑七步,石柱去石羊七步,石人去柱七步”;《舊唐書》卷14在記述甄官署時,亦言及所負責之喪葬器物,“典事十八人,甄官令掌琢石陶土之事。凡石磬、碑碣、石人獸馬、碾硙、磚瓦、瓶缶之器,喪葬明器皆供之。”
今所見最早記載有關泓師墓中貯藏金、玉吉兇之說出《大唐新語》卷13: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于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參之。仆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鑄鐵為牛豕之狀像,可以御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5
此段是最為重要的一則有關泓師堪輿理論的材料。其一,關于入地深淺,泓師認為選擇深處幽靜的狹窄牢固之地為宜;其二,地下一丈二尺屬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自有土龍和水龍把守。土龍六年一發作,水龍十二年一發作,如果在二丈四尺以上之地,逝者無法獲得安寧,故而需要深至二丈四尺以下;其三,墓的四周應下寬上聚,頂部俯視呈聚集之勢,旁側收攏;其四,墓中裝飾以泥粉而非石灰粉為當;其五,隨葬品禁忌——不得放置磚瓦、黃金、朱丹、雄黃、礬石、羽毛,而宜置鐵牛、鐵豕之物抵御二龍,玉溫潤潔凈,與百神和,亦佳。“貯金多則草木焦枯”之說或為“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之訛變。
綜上,三事皆為言金玉與宅墓兇吉之事,就泓師之理論而言,宅第之形與金杯構成橫向組合系統,所指為吉;墓地與宅第構成縱向聚合系統,墓地貯金,所指為兇。同理,宅第之形與玉杯構成橫向組合系統,所指為兇;金與玉亦構成縱向聚合系統,墓地貯玉,所指為吉。在縱橫交織的關系網中,堪輿的符號意義得以呈現。這種組聚關系所構成的堪輿之法或可為中國古代民間信仰之另一側面。
吉
宅第 金
兇
兇
墓地 玉
吉
(三)地勢——宅、葬二法的關鍵
材料五泓師言“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點出張宅之吉的緣由——西北隅為高地,首先,這與中國地理大勢“西北高東南低”一致;其次,敦煌文書伯2615A對姓氏分別對應的五姓有具體記載,張姓在宮商角徵羽五姓中屬商姓人,得西高、北高之地則吉,故此亦與五姓宅經暗合;6此外,《地理新書校理》參定官書言“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流出辰巳間,吉”與此相近,王氏此書實為北宋早期全面總結以往地理堪輿術的著作,據此不得不說前代的堪輿著述及筆記史料為之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而當此處之土被取,本應為高地而洼陷,宅氣蕭索,即便從他處取土,與原本之土相比與此處的地脈并不相通,失去了聚攏之靈氣,填之亦無法補救。郭璞《葬書》云,“夫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氣本無體,假土為體,因土而知有此氣也”,一旦動土,氣必散開,此亦符合中國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材料六言鳳棲原之地有龍起伏形勢,據《類編長安志》載:“(鳳棲原)在少陵原北,接洪固原。柳宗元為伯妣志曰:‘葬于萬年之鳳棲原。”:7此常為古人袝葬之地。泓師所言鳳棲原之地有龍起伏之氣勢,風水學一般以連綿的山巒視之,然為何此地為韋安石家墓地則可世代為宰相,若作韋韜家墓地則僅做能到卿一級的官職,或與古代禮制信仰有關,大概墓地的選擇應與逝者的身份地位、德行操守等相符為佳。材料七中泓師對源乾曜所買墓地之分析亦屬地勢上的,雖為一村夫憑下俚斗書所造,然“洼處本高,今則洼矣。合高處本洼,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作者”,對地勢高低的調整以及安墳位置的恰到好處使得源氏子孫大貴。
正如敦煌寫本《黃帝宅經》所言:“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若不吉即門族衰微。墳墓川崗,并同茲說。”8通過泓師之口,我們得以了解唐代選宅擇葬所考慮的地勢問題,三則材料顯現了堪輿在唐代民眾信仰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這套符號系統能夠滿足中國古代民眾的文化性格,因而得以長期使用。
四、結 語
從唐代僧人泓師與眾多大臣的交往中,我們得以知曉這位術士的更多故事,從而關注到唐代僧人習學世間占相技藝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
首先,唐代以僧人泓師為代表的僧人習學相宅、占卜等世間技藝正是大乘佛教習學世間諸法觀念影響下的主觀映射。《宋高僧傳》將泓師列入“雜科聲德篇”,并指明此科的性質,“統攝諸科,同歸高尚。唱導之匠,光顯佛乘。”就經眼文獻而言,多記載泓師占相堪輿之事。僧人習學世俗技藝事實上由來已久。正如湯用彤先生指出:“占卜之術,易于動聽……佛教之傳播民間,報應而外,必亦藉方術以推進。”9這種觀念繼而影響到此后僧人的修行方式,他們中的一部分走出山林,來到俗世,以教化、利導眾生的方式傳播佛教。此類迎合大眾信仰的“神通”之術對傳播佛教所起的作用并不亞于求法、譯經。
其次,武則天及中、睿二朝佛教的極盛發展為泓師的活動提供了客觀條件。唐時眾多雜傳對泓師不同程度的描寫證明了這一人物存在的真實性和豐富性。他生活于武后至睿宗朝,善于堪輿、卜事、相面,常游走于王宮貴胄之間,晚唐時仍具一定影響。唐代社會的開放繁榮促使眾多宗教并行,佛教力圖尋求一種更為穩定的發展態勢。統治者對佛教的支持促進了上層社會對僧人的崇奉和青睞,富于奇幻色彩的相面、堪輿之術既取自民間,吸引了更多受眾的目光,又在宗教實踐上推動了佛教的傳播。許多僧人轉換身份,通過堪輿、相術等多種方式增強影響力和公信力。如清人趙翼所說:“蓋一教之興,能聳動天下后世者,其始亦必有異人異術,神奇靈驗……能使人主信之,士大夫亦趨之,是以震耀遍天下。”10泓師正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部分僧人企盼獲得上層統治階層名望上支持的強烈愿望,民間儒、釋、道三教合流,佛教趨向世俗化。
此外,史書與小說、僧傳對其故事的不同記載分別表明了各自的看法和立場。兩《唐書》的相關史料雖來自于唐小說,但又有所取舍,反映了編纂者對佛教的認知態度,即多從經世致用角度選取佛教文獻,歷史借鑒與批判色彩更多。而雜傳、小說既建立在歷史人物的基礎上,又對之加以神化和虛構,故雖有眾多與歷史不盡切合之處,但其豐富性確為我們提供了更多關于佛教在唐代發展的寶貴文獻。而泓師相宅理論也確為古代相宅堪輿之術的展現積累了珍貴資料,藉此我們得以從新的角度了解唐代民間的金玉文化、堪輿信仰。蘭興認為,四柱祿命的頻繁使用增強了符號意義上的理據性。11相面堪輿之術亦是如此,其符號系統是中華民族在廣泛運用中推演、發展而來,絕非能以虛假一言以蔽之。只有在不斷發現與研讀諸種文物文獻的過程中,這個符號系統內部的意義正確與否才能不斷被揭開。
[注釋]
1周勛初:《唐人筆記小說考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頁、第185頁、第186頁。
2閆淳純:《唐代風水活動考》,浙江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第 頁。關長龍:《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中華書局2013年版;王雪艷《唐人小說中的僧人活動》,西北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第 頁。
3[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版,第592頁上。
4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頁。
5[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13,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5頁。
68關長龍:《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84頁、第286頁。
7[元]駱天驤撰,黃永年點校:《類編長安志》卷7,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08頁。
9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頁。
10[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15,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43頁。
11蘭興《從天地到人倫——四柱祿命中的符號及其理據性上升》,《符號與傳媒》2012年第2期,第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