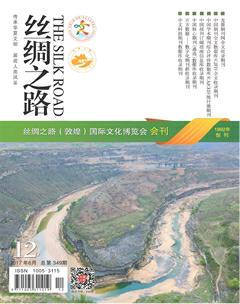試析陜西回族發展歷史上的三個時期
馬健君
[摘要]陜西回族的發展歷史和絲綢之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歷史上的陜西曾經是中國回族形成較早、分布最集中、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關中地區的渭、涇、洛三河中下游地帶,也即西安、同州兩府是陜西回族人口分布最為集中的區域。鼎盛時期人口峰值接近或超過200萬人。陜西回族的發展歷史經歷了早期孕育、發展壯大、鼎盛成熟三個時期。
[關鍵詞]陜西回族 歷史 發展 時期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陜西回族與伊斯蘭教早期歷史問題研究”(項目批準號15YJA850003)。
陜西在中國回族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與影響。陜西關中自古形勝物阜,地處中國東西南北交通要沖,省城西安曾是我國歷史上13個王朝建都之地,又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起點,因此陜西回族的發展和絲綢之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歷史上,陜西曾是中國回族形成較早、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同時也是我國回族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到清代中后期也即清同治元年之前,陜西回族人口峰值接近或超過200萬人。尤其是關中地區自西到東,沿渭河兩岸回族人口分布居住最為集中。本文綜合已有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不揣谫陋,將陜西回族的發展歷史大致劃分為早期孕育、發展壯大、鼎盛成熟三個時期。
一、早期來源與孕育時期
中國回族形成于元代,定型于明代,這是就中國回族整體而言的。回族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從全國范圍看,回族形成的歷史與時間是不均衡的,有些地區或者省份的回族形成時間較早,有些則形成時間較晚。我國的西北、東南地區是回族形成時間與歷史較早的地區,這些地區回族形成較早與回族先民大食、波斯人最先涉足進入并且落居有著直接的歷史淵源關系。
據新舊《唐書》等史籍記載,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國(阿拉伯)派遣朝貢使節來到長安,與唐通好,這一年成為中國與阿拉伯正式締交之年,亦被學界視為伊斯蘭教進入中國的開始。從唐高宗永徽二年到德宗貞元十四年(651~798年)的147年中,大食國使節派遣于唐者達37次之多。1有的是連年通好,有的是一年之中出入長安者竟有二三次。有些往來于中國與大食國的使節多兼有商人身份。7世紀中期以后,大食國的勢力范圍向東擴張,波斯及中亞講波斯語的民族遂改宗伊斯蘭教。作為唐朝國都的長安是當時國際上最繁華的貿易中心,吸引著大食、波斯與中亞商人長途跋涉、絡繹不絕來到唐長安經商貿易。唐時把這些商人稱為“胡商”“賈胡”“胡客”等。其時長安城里的“西市”外來“胡商”最為集中,“波斯邸”鱗次櫛比。唐德宗貞元三年(787),唐朝清查久居長安的“胡客”,數量竟有4000人,居住久者達40年。當唐朝欲將這些人遣返回國時,遭到一致反對,他們全都自愿留居長安。這些人中應有一定數量的穆斯林。
另據史載,唐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唐朝借助回紇、大食等外部力量平定叛亂,收復了長安以后,唐朝允許助唐平亂有功的大食與回紇兵士留居長安。有關這一歷史,阿拉伯學者也撰文寫道,安史之亂時,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組成的軍隊在突厥人葉阿福爾的率領下前往中國,幫助中國軍隊平定了叛亂。 “中國皇帝向支援了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們愿意,他們可以留住京城,允許他們同中國女子結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2比照中外兩種文字,除清真寺外其他情節基本一致。
北宋定都汴京(開封),開封又成為大食、波斯、西域諸國的穆斯林朝貢使節、商人集中的地方。關中地區處在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是前去開封的必經之路。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一度曾被西夏黨項人扼控。這些往返于絲路上的穆斯林商人與使節,常常因道路受阻滯留在陜西關中地區。有些長期滯留的穆斯林很可能和唐代留居的穆斯林后裔在唐代長安的舊址上匯合聚居,成為陜西回族的早期先民族群。
由上可知,唐代來到長安的眾多西亞、中亞的穆斯林主要是使節、商人與軍士等,以后留居唐長安的也主要是這些人。由于他們的入華并落居,促進了西域各國與唐朝的經貿關系和文化交流,而且因為他們與中國婦女通婚,更是促進了外來文化、習俗、信仰的擴大與傳播,從而為文化交往和民族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總之,唐宋時期留居的穆斯林族群是陜西回族早期的主要來源,該時期也是陜西回族早期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
二、快速發展壯大時期
蒙元時期,受蒙古人驅使,大量中亞穆斯林隨軍遷徙中國,他們與蒙古軍一起展開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中亞的回族士兵被蒙古人簽發到陜西關中屯田,同時征調蒙古軍隊入陜戍屯。陜西關中地區是元代重點經營的地區。憲宗三年(1253)忽必烈受封京兆,開始在鳳翔屯田,十年后又屯田京兆。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詔以“陜西京兆、延安、鳳翔三路諸色人戶,約六萬戶內,簽軍六千”。3在陜西京兆、鳳翔、延安三路有約6萬戶的諸色人中可“簽軍六千”,可見當時陜西回族軍士之眾。元代陜西屯田系軍民合屯,地方主要在關中的櫟陽(臨潼)、涇陽、終南(長安)和渭南等地。隨著戰事結束和元朝統治的穩固,軍隊奉命“隨地入社,與編民等”,軍士解職為農,由軍戶變成農戶,廣泛分布在關中一帶,其中有大量的回族軍士和蒙古族穆斯林。這些人集中在關中渭河兩岸以及西安周邊開墾荒地,從事農業,成為種地務農的陜西關中人。此外,元代有不少回族人來到陜西做官并攜眷入陜。最著名者是至元元年(1264)回族人瞻思丁·賽典赤出任陜西四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在任三年中,曾率大批西域軍民,在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進行屯墾,使陜西地區人口與田糧驟增,為陜西的農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元代伊始在陜西設安西路,忽必烈封他的第三子忙哥剌為安西王。由于五代時期長安城縮建之后城郭狹小,忙哥剌另在長安城東北、浐河西邊修建了宏偉壯麗的安西王府,俗稱“斡兒朵”(蒙古語“宮殿”“行宮”之意)。忙哥剌死后,其子阿難答承襲安西王。據史料記載,阿難答自幼曾被一穆斯林撫養長大,所以從小信仰伊斯蘭教。受封安西王后,他在軍隊中大力推行伊斯蘭教,使他所率15萬軍人中的大部分人成為穆斯林。受此影響,以后的安西王周邊即西安城東北郊成為西安回族聚居集中的地方之一。西北大學王宗維先生曾對該地區進行過實地調研,他撰文談道:“安西王府所在地斡兒朵附近,東至米家崖、牛而寺,西至北關、東、西菜園,北至新莊、光大門、浮沱寨、上、下水腰直至馮家灘,有很多回民村莊。”
4元代特別是安西王阿難答統治時期,三秦大地尤其是關中地區回族人口急劇增加,出現了眾多回族人聚居的地方。關中一帶此后遍布回族村莊,有八百寺坊出現,與此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因此,元代是陜西回族形成以后發展壯大、趨于成熟的關鍵而重要的歷史節點。
三、成熟與鼎盛時期
明代,以前安置在甘肅的入附西域回民,有一部分先后被明朝遷徙到陜西等腹里地區。據中央民族大學和研究,“自明太祖洪武中至明世宗嘉靖初的百余年間,入附西域回回安置在肅州、甘州、涼州、平涼一帶的至少在五六萬之眾,陜西關中一帶者也在四五萬之間”。同文中還說:“迨明中期,陜西關中、河南等地都已形成許多回回聚居區。”5還有,“靖難之役”后有不少江南回民來到陜西;明英宗初年,遷徙新疆東部與河西一部分回民于江浙的同時,從銀川疏散一批人入陜”。6這些入口促使陜西回族人數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增加。與此同時,以農為主、農商結合的回族經濟在陜西也得到長足發展與增長。
明代后期,中國伊斯蘭教的經堂教育由陜西咸陽人胡登洲(1522~1597年)倡導和實踐,首先在陜西關中地區興盛起來,隨后擴及到河南、山東、甘肅、寧夏、北京、南京、云南等全國各地的回族聚居地區。明清時期,經堂教育在全國范圍內陸續出現了陜西、云南、東南、蘭州、河州等多個不同的學派。但都是由陜西學派發展、演變而來。自經堂教育出現之后,陜西關中及西安成為中國內地回族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中心,形成“同治以前秦川有大、小八百多座清真寺,不分教派”7的局面,陜西回族與伊斯蘭教步入發展歷史上的輝煌鼎盛時期。
西安作為千年歷史古都和關中地區的中心,伊斯蘭教文化源遠流長。乾隆四十六年(1781),陜西巡撫畢沅給乾隆的奏折中這樣說:“西安省城內回民不下數千家,俱在臣衙門前后左右居住。城中禮拜寺共有七座,其中最大者系唐時建立。”8畢沅奏折中說到“城中禮拜寺共有七座”。這七座古老清真寺至今依然保存完整。它們是化覺巷清真大寺、大學習巷清真寺、大皮院清真寺、小皮院清真寺、北廣濟街清真寺、營里清真寺、灑金橋清真古寺。七座寺中歷史最悠久的是化覺巷清真寺和大學習巷清真寺,一直流傳西安回族坊間的說法兩寺是“唐寺”。其余的幾座清真寺皆建造于明代或更早,歷史最晚的是北廣濟街清真寺,也建于明末清初。七座寺再加上當時西安城內回族分別居住的街巷坊里,形成了“七寺十三坊”傳統居住格局。如化覺巷、西羊市分屬“京兆坊”,大皮院、小皮院分屬“前所坊”,北廣濟街屬“廣濟一坊”,大、小學習巷屬“新興坊”等。西安回族當時居住之處大致被這幾大坊里所涵蓋。此外,在當時西安城外附近,也即東、西、南、北四鄉,還有大小回族聚居村莊70余個、回族寺坊64個。明清時期西安府之城內與城外四鄉分屬西安府之長安、咸寧兩縣管轄,因此城內城外同屬西安回族。
明清時期,陜西回族遍布于全省七府五州,但分布空間卻極不均衡。分布的主要范圍是沿渭河流域上游的鳳翔、涇河流域上游的邠州、自西向東流經至洛河下游的同州,直抵黃河的整個關中地區。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路偉東通過多年對清代陜甘人口專題研究,將清代同治元年(1862)陜西回民起義以前陜西回民人口分布劃分為三個區域,即中心區、次中心區和邊緣區。中心區主要是長安、咸寧、咸陽、涇陽、臨潼、高陵、渭南、華州、華陰、大荔、蒲城、朝邑等18個州縣,分屬西安、同州兩府。由此看來,分布最集中的地區是涇、渭、洛三河中下游的狹長地帶,尤其在西安、同州兩府的交界地帶是陜西回族人口分布最為集中的區域。這一區域屬于關中的中東部地區。次中心區除西安、同州兩府之外,包括關中西部的鳳翔府、邠、乾二州與陜南地區的漢中府。這二府二州都有一定數量的回民集聚點,但回民人口顯然沒有西同兩府多。9
至于同治元年以前陜西回族人口數量,以及回族人口占當時陜西總人口的比例是多少,清代文獻資料所顯示的數據非常零散,即便有這方面的數據信息,也過于簡略籠統。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余澍疇在其《秦隴回務紀略》著述中開篇就言明:“舊傳,陜甘回民系唐郭汾陽借大食兵克復兩京后留居中土者,迄今千余年。陜則民七回三,甘則民三回七。”陜西“民七回三”,就是說陜西回民的人口占當時陜西總人口的30%。這種說法雖然簡略籠統,但流傳甚廣。民國《續修陜西省通志稿》中也記載:“原在陜西省西安、同州、鳳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二十多州縣里住有回民七、八十萬到一百萬,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這里所言回民人數占陜西全省人口的1/3,可實際上指的僅是關中地區。
同治元年以前陜西回族聚居最為集中的縣州府絕大多數在關中地區,尤其在西安與同州兩府所屬的州縣中,回族人口分布聚居最為集中,也即陜西回族分布的中心區域。據最新研究數據表明,同治以前“西安、同州2府的16個回民聚居的州縣中,回民人數約有121.3萬,約占兩府人口總數的22.2%。如果加上兩府其他州縣中的回民,估計戰前陜西回民分布最為集中的西安、同州兩府中,回民人口的比例可能接近30%。”10再有,研究數據還顯示當時陜西回族人口總數及所占全省人口總數的比例和峰值人口:“保守的估計,1862年以前,全陜回民人口的峰值數很可能接近或超過200萬,這一人數大約占同時期陜西全省人口總數的一成五左右。”11這是目前所見到有關陜西回族鼎盛時期人口以及分布情況的具體數據。
四、結語
陜西自然地貌呈狹長形,自北向南分為三個自然板塊,一馬平川的關中地區北邊為陜北黃土高原,南邊是處在秦巴山地間的陜南。自然地理的巨大差異和歷史原因造成三地回族在來源與發展形成方面不盡一致。比如陜北地區和關中地區的回族之間,除了關中北緣的個別地區有一些聯系外,其他地區聯系很少。以至于到了明代末期,陜北農民大起義期間,陜北回民與環縣、慶陽一帶回民一同起義征戰多年,卻對關中地區回民基本沒有發生什么影響。12以馬守應為首的參加明末農民起義的陜北回民以后轉戰甘肅、山西、湖北等地,再沒返回故地,陜北地區的回族因此幾乎絕跡。
在陜西回族形成發展的漫長歷史中,因戰爭、屯田、經商等各種原因,致使關中回族人口遷徙全國各地形成空間流動的事情屢現于史料之中。比如中國伊斯蘭教虎夫耶門宦中幾大支系的創建人像比家場的馬宗生、花寺的馬來遲、穆夫提的馬守貞其祖上都來自陜西長安。13云南回族眾多,但最早的一支是元代咸陽王賽典赤從陜西關中帶過去的。云南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因此才快速發展起來。又如云南昭通有馬姓、劉姓、鎖姓等回族家譜資料記載其祖籍均是陜西長安人,系明初隨回族大將沐英、藍玉入滇平亂后落戶當地的。14“清雍正年間,自陜西長安、大荔等地遷居內蒙古呼和浩特的經商回民很多,至清末,呼和浩特有回民三千人之多”。15特別是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之后,陜西關中地區的回族遭受史無前例的滅頂之災。除西安城內約萬余眾回族僥幸存活下來之外,關中大地自東到西各個州縣的回族蹤跡全無,或被屠殺,或兵敗受降被清政府分別安插到甘肅、寧夏等貧瘠荒漠之地。此外,還有部分人分別流落到四川、河南、內蒙、新疆等地避難,最后就是誓死不降被迫逃亡到境外哈薩克、吉爾吉斯等國的一部分人,他們便是當今的國外回族——東干人。
[注釋]
1楊懷中:《回族史論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頁。
2[敘利亞]卡米勒爾·雅德:《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研究》,1958年第11期。
3《元史》卷98,兵志一。
4王宗維:《清代中葉前西安地區回民的分布和經濟生活》,載《西北歷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頁。
5林松、和:《回回歷史與伊斯蘭文化》,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頁、第202頁。
6馮增烈:《陜西回族今昔觀》,《寧夏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
7馬長壽主編:《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頁。
8[清]劉智:《天方至圣實錄》(附錄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刊印本,1984年,第399頁。
9 路偉東:《清代陜甘人口專題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326頁。
10路偉東:《清代陜西回族的人口變動》,《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
11 路偉東:《清代陜甘回民峰值人口數分析》,《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
12馬士年:《伊斯蘭教在陜西的傳播發展與演變》,載《清代中國伊斯蘭教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頁。
13馬 通:《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頁、第223頁、第251頁。
14魏德新:《中國回族姓氏溯源》,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頁、第156頁。
15邱樹森:《中國回族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