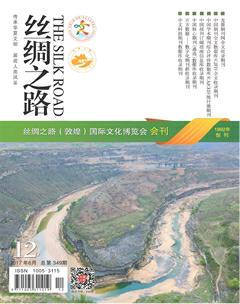張掖大佛寺藏經相關歷史人物初考
繆麗霞
[摘 要]張掖大佛寺歷史悠久,不僅保存有目前國內最大的木胎泥塑臥佛,而且還藏有數量相對豐富且保存完整的佛經多部。歷史上,許多重要人物與張掖大佛寺藏經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既為豐富張掖大佛寺佛經收藏、弘揚佛教文化做出了貢獻,同時也給張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關鍵詞]張掖大佛寺;藏經;歷史人物
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的張掖大佛寺,至今保存著我國最大的佛教殿堂、最大的木胎泥塑室內臥佛和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北藏》佛經。尤其是所藏經書,不僅是佛典至寶,更是不可多得的書法、繪畫藝術珍品。下文試就與張掖大佛寺藏經相關的歷史人物及其事跡作一簡單梳理和介紹。
一、曇無讖
張掖大佛寺現所藏《涅槃經》有《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本《大般涅槃經》、明萬歷姑蘇版《大般涅槃經》、萬歷二十五年弘仁寺金書《大般涅槃經》、順治十年弘仁寺住持定坤募補墨書《大般涅槃經》等,均為北涼曇無讖譯《涅槃經》的傳承。
據《魏書·釋老志》載,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三次下詔歷數佛教之弊,并頒布禁令:“自今以后,敢有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并讓有司宣告征鎮駐軍、刺史,“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拓跋燾此舉只是表明了一個明確的立場和態度,詔令卻遲遲未發,有意讓遠近僧界提前知道,各自為計,所以“四方山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迷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這些史料說明,張掖大佛寺古代所佛像可能就是在這次事件中藏下的。北涼時期,涅槃宗創始人曇無讖來張掖時,曾在迦葉如來寺住過。由此可以推斷,古臥佛像是為紀念曇無讖并弘揚大乘涅槃學而制作的。
曇無讖(385~433),北印度人,6歲喪父,隨母親織毛席為生。母親見僧人生活比較富裕,就讓他出家為僧。曇無讖天資聰穎,10歲時,一天能背誦三百多頌經文。最初他學習小乘佛學,后來遇見白頭禪師,就跟著專攻大成涅槃學。20歲時, 已經熟悉大小乘經6萬多頌,并擅長方術。曇無讖的哥哥喜歡調象,無意中把國王的乘騎白耳大象弄死,被國王殺死,并不準親屬去看。只有曇無讖前去痛哭,并埋葬了哥哥。國王大怒,要殺他,曇無讖說:“國王因我哥哥觸犯了國法而殺他,我是他的弟弟,埋葬他,并沒有違背大義,為什么要殺我呢?”國王佩服他的勇氣,就把他留在了宮廷。剛開始,國王很喜歡他,后來漸漸疏遠了。411年,曇無讖攜《大般涅槃經》和《菩薩戒經》,奔至龜茲,因這里僧眾多信小乘,他又向東來到北涼弘揚佛法。當時北涼國都設在張掖,曇無讖深得北涼王沮渠蒙遜厚遇,與張掖僧人法進合譯《戎本》1卷。北涼長期向北魏稱臣納貢,而北魏太武帝一心想把“博學多識、秘咒神驗”的曇無讖為己所用,并禮兵相加,要求北涼王沮渠蒙遜速遣曇無讖去北魏。沮渠蒙遜妒心發作,“既吝讖不遣,又迫魏之強”,進退惶惑。北魏延和二年(433)三月,曇無讖以尋《涅槃后分》為由,“固請西行”,?沮渠蒙遜遣刺客與途中殺了曇無讖。曇無讖被殺,舉國哀痛,張掖名僧法進等作為他的親傳弟子格外悲痛。為了紀念曇無讖,張掖大佛寺為其造涅槃像供奉,弘揚涅槃思想,使大佛寺成為涅槃宗的重要發祥地。
拓跋氏毀佛滅法,張掖迦葉如來寺的涅槃古佛埋藏于地下660余年,之后又是拓跋氏的后代——黨項族皇族嵬咩國師發現了古臥佛,并重建了寺廟。
二、太監王貴
張掖大佛寺所藏金銀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現存558卷、287本),以名貴紺青紙為本,用金泥書寫、繪畫,材質極其昂貴,經書封皮用名貴綾錦包裝,繡有精美龍紋圖案,盡顯華貴,書法工整秀麗,精美絕倫。卷首曼茶羅畫金線細密,人物云集,場面宏大,充滿了熠熠生輝的皇宮金粉之氣,不僅是佛典至寶,更是不可多得的書法、繪畫藝術珍品,歷來被視張掖大佛寺的鎮寺法寶之一。為明代太監王貴倡造。
王貴,明正統時期宮廷佛學法師,法名朵爾只省巴,御馬監太監兼尚寶監太監。出生年月不詳, 1442年卒于張掖。正統元年(1436),英宗皇帝遣王貴做鎮守甘肅的欽差大臣,坐鎮甘州。
王貴在張掖期間為張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山丹縣城西鑿山建成山丹大佛寺;二是張掖大佛寺(當時稱弘仁寺)內黃金古臺舊址上建成金塔殿,殿內塑造了三世銅佛像,并添地宮舍利寶物;三是召集書畫名士用泥金書造600卷《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明永樂八年,《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在北京開始雕刻,至正統五年(1440)刻成,主要用于頒賜全國各名山大剎。大約在正統六年初,《北藏》首部佛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首先到達甘州,余部陸續自北京運至甘州。直至正統十年(1445)將全部三藏寶典運至甘州弘仁寺,并舉行了承旨儀式。
《北藏》首部《大般若經》到達甘州之際,正值王貴駐守甘州,王貴對弘仁寺產生了濃厚興趣。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臥佛寺規模龐大,置身于此,就會產生回到天子身邊的環境氛圍和感覺。更令王貴驚喜的是,那年春天,弘仁寺金塔古臺下掘出了舍利,于是他決定在這里新修寶殿。工程很快動工,王貴在現場視察、指導,閑暇時,便捧讀《大般若經》,經卷內容深深打動了他,王貴決定用泥金書寫、制成《大般若經》一部,永奉弘仁寺,“上以圖報列圣寵賜之洪恩,下以孝資宗祖栽培之厚德”,更希望以此超度父母亡靈,“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為自己增福增壽。王貴利用在甘肅至高無上的權利和雄厚的財力,很快組織了一批書畫高手,選用名貴紺青紙,用泥金開始書寫600卷《大般若經》。由金書題記中可知,大約正統七年初,王貴去世,金書的書寫制作由太監李繼承完成。此后,有眾多佛門僧侶為修功德,不辭千里,競相來到張掖誦讀金書《大般若經》,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題記。
王貴為張掖人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至今張掖大佛寺珍藏的金書《大般若經》558卷,保存完好,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三、明英宗朱祁鎮
在張掖大佛寺的發展史上,明代是一個非常關鍵和重要的時期。明朝收復張掖之后,面對的是一個被西北少數民族相繼統治了500余年的地區,民族結構非常復雜。但張掖自然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列為“九邊重鎮”之一,所以仍然將甘肅省的首府設置在張掖。曾經作為西夏和元代皇家寺院的甘州臥佛寺,長期流行藏傳佛教,與中原的漢地佛教有著較大的差異。大明帝國為了順利統治西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從而保證了張掖的穩定和繁榮,也使得張掖大佛寺進入了一個更加輝煌的時期。
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出生后次年被立為太子,9歲登基,14歲(1441年)親政,當了22年皇帝,7年太上皇,度過了37歲人生歲月,歷經“土木之變” “南宮復辟”“曹石之變”,一生大起大落,在歷史上不算是一位成功的皇帝,但在位期間,卻做了幾件善事,如廢除殉葬制度,為弘揚佛教向天下名山大寺頒賜佛經等。
為了加強對甘肅的軍事防范,明英宗派兵部尚書親臨河西經理甘肅邊務,并派御馬監太監兼尚寶太監為欽差大臣,總理兵政。正統十年(1445),英宗親詔頒賜給當時作為全國名寺之一的張掖大佛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經》一部。王貴借此東風,在統兵之余大建佛寺,積極主導興建弘仁寺萬壽金塔殿,同時召集書畫名家書造金銀粉《大般若經》,永遠供奉于弘仁寺。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經》共收經1621部,計6361卷,分作636函,千字文編次,分裝于10個大木經櫥內,經五百多年的滄桑巨變,保存仍然較完整,今天已成為稀世珍品。
四、詩僧卜舟
在張掖大佛寺館藏《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經》里,每函經卷都有一塊50厘米見方的包袱布。這是清順治時期由甘肅著名詩僧、臨濟宗第三十四世嗣祖同法發起募化的,為保護《北藏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同法,字卜舟,俗姓麻,甘肅平番(今甘肅永登縣)人,約出生于清順治初年。據張掖大佛寺藏經包袱題記可知,順治十八年(1661),他已在甘州普門寺任檢藏僧,為了保護弘仁寺(大佛寺)藏經,卜舟發起了募捐藏經包袱活動。本次募捐一直延續到康熙三年(1664),為大佛寺輪藏殿藏經募集了許多經袱,并留下了許多寶貴題記。隨后駐錫于安徽報恩寺(今壽縣導公寺),后承傳本寺高僧南耕衣缽,任臨濟宗第三十四世嗣祖。卜舟于康熙末年告老還鄉,卓錫于張掖大佛寺,修寺弘法,老有所為。卜舟工于格律,在張掖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約在雍正十二年(1734)圓寂于甘州。
五、姚尼姑
在張掖大佛寺土塔東南側,有一尊漢白玉石雕像,她結跏趺坐,慈眉善目,靜靜地端坐于佛塔之下,這便是大佛寺的最后一位尼僧——姚尼姑。
姚尼姑俗名心印,法名本覺,1901年生于張掖,18歲持名念佛,45歲受具足戒,受恩師道心法師之托,赴甘肅永昌縣千佛寺參禪,4年后回張掖普門寺修行。1953年3月,到張掖大佛寺看護寺院。當時的張掖縣文化館為她修建了簡易僧舍,屋內一張舊琴桌、一盤土炕,幾件生活用具,設施極為簡樸。當時藏經殿正門已全部封堵,大佛寺遺存的所有經卷等珍貴文物都封存在東邊內柱與墻柱之間的夾墻密室內,夾墻長40米,高20米,厚4米。12個經櫥整齊地排列在那里,每個經櫥中都裝滿了佛經。要想進入藏經殿內,必須通過本覺的居室,外人很少知道藏經殿內的秘密。
本覺在大佛寺里度過了20多個春秋,年事漸高,貧病交加。1975年初,因破炕起火而被燒死在屋里,享年74歲,其遺骨葬于馬蹄寺。人們在拆毀燒殘的房子時,才在墻壁后面發現了完整的12櫥佛經。這批文獻主要包括四部分: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1424)北京官版刻印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匯集了我國佛教各宗派經、律、論1261部、6647卷;明正統六年至嘉靖三十七年(1441~1558),用金、銀粉手寫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光明最勝王經》《涅槃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大方便佛報恩經》等622卷;明代官版雕印佛曲15冊、佛畫20多幅,手寫《大唐西域記》1冊,御賜北藏經版822塊,明英宗圣旨,1卷;清代寫經200卷。這是繼1900年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之后,我國發現的數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獻。由她保護的這批佛經,震驚了佛教界,成為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